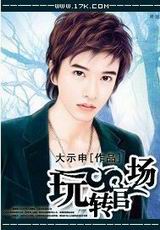官场春秋-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关隐达知道,下一次就是下个季度。地委一个季度研究一次干部。想着心里就有气。什么规矩,什么程序?上次突然任命自己去当教委副主任,规矩和程序到哪里去了?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还对向书记表示了感谢。
可是只过了一个月,地纪委召他到地区桃园宾馆谈话。先找他的是纪委一把手吴书记。吴书记说,有群众反映你有生活作风问题,组织上找你来,是想让你协助组织把事情弄清楚。
关隐达一听气懵了。他尽量克制自己,但话语中还是带了情绪。作风问题?组织上就凭一封检举信,或者一个检举电话,就把一位县长找来谈话,我看只怕有欠慎重吧。
吴书记并不生气,只是很沉着地压压手,说,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刚才说了,只是请你配合组织搞清情况。这是对你负责啊。你先考虑考虑,把你想到的写出来。
吴书记说完就客客气气同他握了手走了。关隐达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半天不知怎么回事。写什么?这就是要我写反省了?我一不嫖妓宿娟,二不养小蜜,反省什么?只怕是有人硬要整倒他了。现在整人,先看你有没有经济问题,再就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又想纪委是不会随便找一位县长谈话的,一定要事先报告地委主要领导。这么说来书记他们是知道这事了。他便扯过电话,想找一下宋书记。却发现电话早切断了。
要隔离我了?你隔离吧,老子正好累了,睡觉!他便舒舒服服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来的是纪委杨副书记,还随了一位科长。杨副书记是个严酷的人,脸上一般不带笑,下面有人背后叫他杨屠夫。
杨副书记同关隐达握一下手,脸上的皮往两边拉了一下,就算是笑了。怎么?写得怎么样了?
关隐达说,一个字没写。
杨副书记脸色一下就青了,说,你一个字都……老关,你这个态度就不对哩。
你们要我写什么呢?这又不是命题作文,只要你们出个题目我就可以写。我什么事都没有,写什么呢?
杨副书记脸上的皮轻轻地跳了一下。关隐达把这个细微动作理解为冷笑。果然,杨副书记接下来的语气同这样表情就很相匹配了。是吗?你还是要组织上给你提个醒是不是?我问你,你在北京有要好的女朋友?
原来如此!
关隐达气得站了起来,把烟蒂愤然摔在地上,任它烧着地毯也不去管。杨副书记看看他,又看看烟蒂,僵了好一会儿,过去踩灭了它。像是有捡起来放进烟灰缸的意思,却又忍住了,固守着纪委副书记的尊严。关隐达在房间来回走动。他要平息一下自己,要不然他会骂娘的。自己印象中,他从高中以后就再也没同人骂过娘。当了快二十年的干部,现在却想骂娘了!毕竟是跟领导当秘书出身的,关隐达在如此气恼的时候,竟然想到这位科长太不活泛,不知捡起那个烟蒂。
心情平静一些了,关隐达就坐在了沙发上,慢慢悠悠地点上烟,说,我在北京有个女同学,叫肖荃。还不是你说的一般要好,我们关系很不错,一直相互关心。但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就这些。你们还掌握更多的情况吗?
杨副书记脸上的皮又跳了一下,说,如果就是这些情况,我们就不会找你来了。据群众反映,你俩的关系,不是一般同学关系,也不是一般朋友关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是一般朋友之间的感情吗?
天哪!关隐达感到眼睛都发黑了。他马上想到了县委办主任陈兴业。真是识人识面难识心!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会对他怎么样。但他只是脑蛋胀热了一阵,就冷静下来了。反而觉得好笑。自己心中没有鬼,脸皮也早拉破了,他就不怕刺伤谁了,说,杨副书记,你知道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吗?
这话有损杨副书记的自尊心,他生气了,说,我就是再不读书,这卿卿我我的诗还是看得懂呀?
()好看的txt电子书
关隐达笑了。他见那位科长也在笑。他说,杨书记,这我就要向你提意见了。你要办案子,还是事先要认真研究案卷。李白和王昌龄可都是男人啊。想必他们不是同性恋吧。
隐达同志,你要认真对待。杨副书记可能也感觉出自己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便不再追问那两句诗说明了什么,只是保持着严肃。
关隐达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这事就有点邪了,还真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人们总说文化大革命太荒唐,在人类历史上再也不可能发生第二次。他从来就不信。他说中国一万年以后都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
过了好一会儿,杨副书记又问,你们真的就是一般要好同学?
我早说了,不是一般要好,是特别要好。这有问题吗?关隐达逼视着杨副书记。
那么,你说说,你给了这女人八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关隐达一听就知道是指什么钱了,但他装糊涂,问,八万?我关隐达哪有那么多钱?有钱的话,送给自己朋友一点,好像也不违法吧。
我想你是在装蒜。你当然没那么多钱,那是财政的钱。你以拨课题费的名义,送给肖荃丈夫八万。这不会错吧。
关隐达没有精力发火了。他感到十分痛苦,长长叹了一声,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么说吧,这八万块钱,还是人家看着朋友面子,按最低标准收取的。谁有本事把国际一流专家请到我们黎南去替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就是用掉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也是划得来的。
别这么夸张吧,老关!
关隐达什么也不说了,起来收拾行李。说,杨副书记,原谅我刚才的冲动。我知道你也是例行公事。不过我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陪在这里。我要说的都说了,你们再去调查吧。不过一定要给我一个答复。我走了。
杨副书记劝道,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要对自己负责。
关隐达不理会,伸出手同杨副书记握了一下,走了。
关隐达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一进屋,就见小顾在家里等他。他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不然小顾不会这么晚还在这里。他从桃园宾馆出发时跟家里打过电话。
关隐达洗了把脸,饭也不吃,就坐下来问小顾,有什么事吗?
小顾看了看陶陶。陶陶马上说,你俩说吧,我到里屋去。小顾这才说,你不在家这两天,县里谣言四起。我想是有人一手策划的,想先从舆论上把你形象搞坏。
都有哪些谣言?关隐达问。
说你去年去深圳时嫖娼被抓了,当时出钱私了啦。最近广东搞严打,你的事就暴露了。地委就找你谈话去了。还说你从财政拨款一百万给北京的情妇。说你的罪行轻者二十年,重者就难说了。我分析,这些事情,领导层都知道是假的,是谣言。可是群众不明真相,你在这里就不好工作了。这是有人故意在搅浑水。
关隐达拼命地吸烟。他看上去显得很镇静,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当领导,时常有些谣言,这本不奇怪。俗话说,谤随名高。但这回分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对小顾表示感谢,让他放心,他不是那么容易叫人弄倒的。
小顾走了,他就很高兴的样子,说,陶陶,你不给我饭吃了?
陶陶就忙去给他做饭。问,小顾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有人搞小动作。才不管哩。
吃了饭,关隐达叫陶陶先睡了,他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群众举报负责城北大桥工程的枣园建筑公司总经理陈天王偷税和行贿的检举信。从中选了一封内容最翔实的检举信,再认真看了一遍。只要搞掉陈天王,就会牵出一批人,正像有的群众说的,黎南要“改朝换代”!他原来本想再等一段来弄这事。现在他不顾那么多了,他必须马上反击!
也怪,他当初被选为县长也并不怎么觉得有成就感,今天却似乎有些激动,像要干一件大事。
关隐达提笔飞快地签道,建议立即逮捕陈大友!
《跋》
刘茁松
身居湖南的王跃文在文坛一跃而起,使我想起鲁迅“文坛无须悲观”的预言。多年前我也曾在刊物做当代文学编辑,编着编着,就有点像鲁迅看当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似的,渐渐地有点“颓唐起来”了。近年来有缘埋头一项等身的古籍整理,与当代文学可说是分道扬镳啦。因此,当我在书店发现与我工作地仅一湘之隔的王跃文在长江黄河两河之隔的北京出了长篇小说《国画》,并且已在全国各地形成洛阳纸贵之势,我是惊讶惊叹又惊喜的。
《湖南文学》的黄斌告诉我,王跃文此前早有不少中篇已引起广泛关注,《国画》之成功,实乃渠成而水到也。于是索来王跃文的一些中篇,后睹亦快,竟有些恋恋不舍。我喜欢他那从容不迫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描绘。他对政府机关人情世故的刻画令我感到冷眼旁观的清醒,他对古典文化艺术精华的化用让我觉得亲如一家的沉醉。他的“拒绝游戏”的创作态度中有着我偏爱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他的许多中篇与官场亦即亦离,将这些中篇编成一个集子,就成了难以磨灭的冲动。
()
现在集子出来了,我与我的朋友、同事们为此书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我们力图把此书编得精致与精巧。效果如何,要让读者诸君评说了。
《王跃文印象》
黄斌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溆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