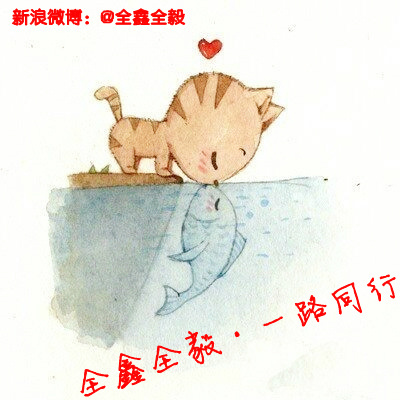军人大院-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夏冰就很满足的笑着,“也许是吧。”停顿了片刻,她又说:“我现在正式向各位宣布,我和常克(她总是这样叫)准备八月份结婚。”
“真的?”戴天娇和王萍平都吃了一惊。
“当然是真的,研究生是可以结婚的。”夏冰说。
“那你要是有孩子了呢?”王萍平问。
夏冰看了她一眼,觉得难为情,说:“为什么一结婚就有孩子?”
戴天娇说:“你自己还是妇产科的呢,当然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了。”
夏冰说:“那我就自己带着。人家于海还不是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也是。”王萍平说。
应该说,总医院护士长的讲话对王萍平冲击最大,她觉得是为她冲开了一个看到外面的口子,也就是一个希望之口。她所想象的自救已经像一艘造好的小船,时刻在等待着她的开启。
王萍平找出了在军医学校用过的教科书,并且又找了一些有关数理化的书籍,她想她一定要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有这一天的存在,她决定不在为个人问题分心。比起护理学士来,恋爱已经不能再让她投入生命。
这一年的清明节前夕,戴天娇收到了一封黄强写来的信,信不长,但是戴天娇看了似乎又把她带到了一个曾经有过的场景里。
天娇:你好!
给你写信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今天我是鼓足勇气才拿起笔的,但是想给你写封信的念头总是存放在我的脑子里的,就像我脑子里的一块瘤子,长了根。
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我们见面还是在少伟的葬礼上,在一五八医院的后山上。那时,我几乎没有和你说话,我怎么和你说呢?在你面前,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男子汉,真的,我不是一个男子汉。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我说,如果张少伟少了一根皮毛,你就拿我问罪。然而,事实上是我的话成了屁话,就好像小孩说的毫无信誉可讲的屁话。我觉得我无颜见你,我既然说了,就要做到,那才是一个男子汉,可是……
天娇,我现在给你写信,主要是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已经申请调到165师,并且已经得到了批准,我将近期到达大荒田报到;第二件事是我准备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看望少伟,请你同意。
有好多话,我们见面再谈。
黄强
3月20日
戴天娇看完了信,靠在了自己的床头上,眼泪像一股小溪一样,蜿蜒在她的脸上。这时,屋外的天空晚霞点点,一切都那么平静。戴天娇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她心里像塞满了刺喉的羊毛一样,似乎在拼命地喊叫,少伟啊,少伟……一种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可奈何,在撕扯着她的心。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天空的朝霞和晚霞依然灿烂,这个地球离开了哪一个人依然转动,可是,可是对于一个曾经的亲人,一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的思念,却依然帽子般切割在亲人的心上。戴天娇想,死亡绝不是一些理论就能说清的,对于已经走了的人或依然活着的人,死亡是一片羽毛,也一座大山,死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死亡像死亡一样毫无踪影地潜伏在活着的人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或细胞里,时刻吞噬着心灵的情线和神经的纤维。
于是,说不清的泪水,总是会在毫不设防的时候,漫布你所有的人生。
可是,活着的人还要带着死亡的阴影继续活下去,要像模像样地活下去,让活着的其他人看到。
戴天娇曾经不想活过,当然,没有人知道。在别人看来对于完美的她来说,就连战胜痛苦,她也应该是有着超人的承受力的。她知道,她知道别人是这样看她的,为此,她只有在心里哭泣,在心里哀嚎。她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她每天都在期待着一种意外灾难的降临,她渴望爆发战争,那种更惨烈的战争,或者翻车,或者被大火吞噬,总之,她不会在任何一次突如奇来的灾难中逃命的,她在期待。
黄强的来信,又像一只带刺的手抹过了她已经脆弱的心脏。她看完信后,用手使劲地揉自己的胸前区,她摸到的是饱满坚挺的乳房,那是她作为一个年轻女人的标志。她真恨啊,她恨她没有把最美好的呈献给活着的张少伟,是的,一切都没有呈献给自己心爱的人,可是,心爱的人已经长眠,已经永远不会回头,而爱他的女人只能带着无尽的无奈和永远的遗憾在呼喊他……
清明节的时候,黄强真的来了,在墓地他们相见了。戴天娇是先到了,她带着一束开得正艳的马樱花,那是一束火一样红的马樱花,她把马樱花放到了张少伟的墓碑前,说:“少伟,我带着花来了,你最喜欢的马樱花。你不是说,医院院子里那些所有的花也没有这马樱花漂亮吗?我承认马樱花很美,尤其是今年,它的花瓣就好像被擦亮了一样,鲜艳得让人觉得不真。现在就放在你的面前,你好好看看吧。今天,黄强要来看你,你们一定有好多话要说吧。”
黄强是举着一束松枝来的,他把松枝放到了马樱花的旁边,在墓碑前蹲了下来,他看着少伟的照片,照片上一尘不染,还是那样笑着,很年轻很单纯地笑着,就是这样的笑,使黄强一下子觉得无法承受,他哽咽着说:“老兄,我来看你了。”说完就急忙站起身来,赶紧扭转身子,不露声色地擦去泪水。
片刻,他转过身来,看着戴天娇,戴天娇也看着他,笑着,没有说话。黄强浑身颤栗了一下,为眼前的女人,毫无疑问,她太美了,太美好了,可是,又太不幸了。再看一看眼前的还有些新的墓碑,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老兄,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俩的那一句玩笑就要成真吗?”
他简直不敢想下去,想下去让他有一种犯罪感。
戴天娇说:“挺好的。”好像在说她自己,又是在说张少伟。
黄强忽然感到。眼前的女人不仅仅是美好,更有一种力量,一种看不见的勇气。想到这更是一颤,心疼得要命。
戴天娇看了看黄强,就转身走到了一边,她知道黄强一定有许多话要对少伟说。她走到墓地的边缘,远远地看着黄强,黄强的嘴在动,戴天娇就想,少伟是需要朋友的,一想到以后黄强能经常来看少伟了,她心里似乎多了一些安慰。
因为时间晚了,黄强准备在张少伟家住一夜,第二天返回大荒田,晚饭在张少伟家吃的,沙老太高高兴兴的做了几个好菜。吃过饭以后,沙老太对戴天娇说:“天娇,坐在家里怪闷的,你和黄强出去走走。”
还没等戴天娇说话,黄强就说:“天娇你带我去看看黄大妈,好吗?”
戴天娇就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有一个黄大妈?”
黄强不好意思地说:“还不是少伟告诉我的。”
戴天娇就说:“他怎么什么都告诉你?”说着就答应了。
沙老太一听要到西边村看黄大妈,就进厨房拿了两把面条,一瓶酱油和一瓶莱油,说:“天娇,把这带上,上次带去的可能已经吃完了。”
戴天娇点点头,接了过来,说:“妈,我们走了。”又大声对着里屋说:“爸爸,我和黄强出去了。”
路上,戴天娇说:“少伟经常给你讲我吗?”
黄强点点头说:“嗯,我知道他那种心情,因为高兴而不得不找个人说说。不过,我和少伟谁对谁呀,可以说是一个人。你们女人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谊,真的,男人与男人,有一种真友谊。”
戴天娇点点头,说:“其实;少伟也经常说起你来,也说过你这样的话。不过,我们女人也有真友谊的。”
黄强说:“可能吧,不过,很少。”
到西边村的路有一个地方不好走,因为常年积水,总是稀泥巴,黄强先跨了过去,就伸过手来拉戴天娇,戴天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给了他。黄强说:“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石林,爬莲花峰?”
忽然,那一天的事情,就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戴天娇的脑子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又要来了,戴天娇使劲咽了一口口水,说:“当然记得。”就没有再说下去。
黄强进入黄大妈家的感觉,和张少伟一样,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就听得戴天娇在和一个老太太说话。黄强就站在门口,努力睁大眼睛,过了一会儿,屋内的一切才在他的眼睛里渐渐地清楚了。眼前站着一个到他腰这么高的老人,浑浊的目光几乎让你觉得她没有视力。她看了一眼黄强,像嚼东西一样嘴在蠕动,自己先坐了下来,其实没有凳子,就是一张用土基垒起的床,上面铺着一层草,在草的上面有一床部队用的床褥,有一床已经发黑的被子。老人就坐在床沿,床低得就好像是蹲在地上。
戴天娇向里走了走,那就是厨房,其实根本没有分开,只不过是延长,有一个很大的灶台,就表示是厨房。她把面条、酱油、莱油放到了灶台上,就用大嗓门对着老人喊:“大妈,这是面条、酱油、莱油。”老人听了两遍,点了点头,戴天娇又揭开水缸的盖子,弯下腰看了看,就对黄强说:“我们去挑点水吧。”
两人担着水桶进了门,黄强一放担子就大大的喘了口气,“天哪,每次都是你挑水?”
戴天娇笑了:“很重吧,我才不像这样呢,我每次都只挑半桶,多跑几次不就行了。另外村里也有团员定时来给大妈挑水的。”
这时,黄大妈已经点燃了煤油灯,小屋里亮了起来,黄强坐在床沿,四下里看了看,到处都是黑色,难怪在白天这里面也是一黑的。
走时,黄大妈依在门边上,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戴天娇对黄强说:“其实大妈就是不爱说,她心里什么都知道,我每次来她都很高兴,一个人也很孤独。”
两人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天已经全黑了,黄强忽然莫名地又想起了他曾经和张少伟说过的话,心里一阵莫名的慌张,身上好像上了紧箍咒一样,走着路的双腿忽然变得很重很重,几乎要绊倒。
戴天娇倒走到了前面,就转过身来:“黄强,你怎么了?”
黄强忙跑了几步,说:“刚才腿突然抽筋了。”
“现在好了吗?”戴天娇问。
“好了。”
又继续往前走,就只听见脚步声,那种踩在坚硬的土路上发出来的闷闷的声音。黄强很想说点什么,他实在不想听这种闷闷的声音,于是,脑子里就在快速转动,想找一个话题。
他突然说:“后来还是没有找到……”话一出口,觉得不对,赶紧停住。
“什么没有找到?”戴天娇问道。也难怪,四周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说话声特别清晰。
“没,没什么?”黄强忽然变得语句不畅。
“到底什么没找到?”戴天娇还在问。
“是鞋。”黄强吞吞吐吐地说。
“鞋?什么鞋?”戴天娇觉得奇怪。
黄强叹了口气,说:“我又想起了张少伟。对不起,天娇,我本来不想说他的。”
戴天娇说:“黄强,没什么,我喜欢听你说少伟,你一说。我又觉得少伟就在我们中间,听着亲切。”
黄强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搞夜间紧急集合,没想到一家伙把我们拉到了学校后面的山上,说是发现一个逃犯,要包围整个山搜查。我们班负责的地段是一片乱坟岗,许多同学都很害怕,突然有一个同学一脚踩到了一个狭缝里,使了很大的劲才把脚拔了出来,可是鞋却掉了,山上又黑,而且尽是一些低矮的灌木丛,这个同学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男生,胆子也小,没有鞋他连一步也走不了,可是又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不管,这边我们还有任务,大家都急死了,我伸手到那个狭缝里一摸,就知道根不找不到了。这时,少伟把他自己的鞋脱了下来,给那个同学穿上,他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又往山上走。回到宿舍,在灯光下一看,那双厚厚的军用袜子早就成了麻袋片了……”
黄强没有再说下去,自顾向前走,忽然听到后面有抽泣声,知道戴天娇哭了,就停住了步伐,心里恨死了自己。戴天娇的眼前仿佛看到张少伟一双流着血的脚,本来就觉得少伟没有享什么福就走了,心里就难过,现在就更难过了,又是那种极度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心在嘶喊着……说:“他肯定疼死了。”
黄强不知道该怎么办,怔怔地站着,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黑黑的,像黄强现在的心情。
第十九章
夏冰真的在八月份结婚了,不过她没有在医院办喜事,而是直接到了重庆,因为常克生在那里等她,他们将旅行结婚,从重庆出发,过三峡,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北上北京,再由北京到西安,回常克生的老家,然后返回。
夏冰走之前终于搬出了集体宿舍,她搬到了常克生那一间十二平米的房子,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天地,戴天娇、王萍平、任歌都去帮她收拾房子。什么家具也没有,任歌就到药房去要了几个大箱子,到县城买了花布,用花布一盖,就好像有了茶几、梳妆台、高低柜,再用相同花色的花布做窗帘,忽然就成了一个很温馨的家,空空荡荡的倒显得整洁。任歌还剪了大红喜字贴在了门上和窗玻璃上。就这样夏冰就走了。
宿舍里就剩了戴天娇和王萍平,她们把夏冰的小床搬回了木工班,房子忽然觉得大多了,两人床对着床,中间可以放两张桌子。王萍平把本来放在床边的书都放到了桌子上,戴天娇的桌子上也放满了书,一人买了一个台灯,每天晚上两人就一人一张桌子伏案看书,反正两个人都想等待着护理大专招生。
一天,护士长把戴天娇叫到了办公室,对她说:“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我们老吴要调走了。”
戴天娇摇摇头,不知道护士长想说什么。护士长很高兴的样子,用眼睛看了看外面,好像是看看有没有人在听。又接着说:“他要到一七九医院去当副院长。”
“哎呀,这太好了。”戴天娇说。
“是啊,他去我肯定是跟着去的,我们女人就是这样的,一切要服从他们男人。”护士长说。
“那,我们科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