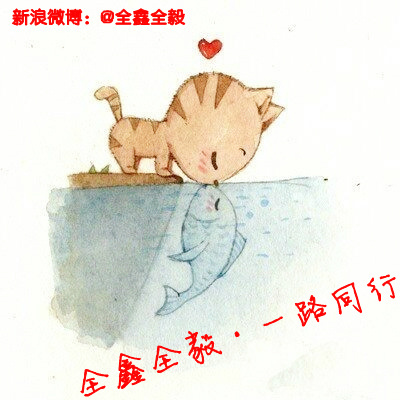军人大院-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决不像于海这样马马虎虎,对自己也太不认真负责了。
房子实在太小,就是再有人来也要坐不下的。王萍平就懂事地示意大家撤退,可是护士长硬是不让,她说,有年轻的姑娘在这,才显得喜庆。大家只好不走,就坐在各种各样临时借来的凳子上,嗑着瓜子,吃着喜糖。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恭喜,恭喜。”
那种特别的北京话的口音,使朱丽莎的心猛地一紧,她知道这是皇甫来了。戴天娇听到这声音后,立刻确定就是那个神秘的男人,她迅速转过头去,向门口看去。
皇甫忠军一进门就使得姑娘们愣了一下,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在风衣里面是驼色的羊毛衫,一条米色的长裤和一双白皮鞋。一切都与一五八极不相衬,好像他来自外星。
“皇甫,”于海说,“你也太隆重了。”
“这不是参加你的婚礼吗?”皇甫说着,做出一副才看见一群姑娘的样子,“哦,客人不少呵。”
于海就指着皇甫间大家:“认识吗?”
“不认识。”
“认识。”这是任歌说的。
“这是著名外科医生皇甫忠军先生。”于海说。
原来,他就是皇甫忠军。戴天娇在心里说道。关于皇甫忠军的话题已经在她们宿舍里进行过好多次了,总是任歌提起来,毕竟是他们科的医生。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工作能力很强,是北京来的高干子女。戴天娇就更奇怪了,她不明白那一天在操场上他为什么要那样说。
于是,戴天娇就来个先发制人:“我倒是不认识皇甫医生,不过,我们可不是第一次见面。”
“哦,”皇甫忠军吃惊的看着戴天娇,“何以见得?”
“我想你不至于记性那么差吧?”戴天娇说,“就在半年以前……”
皇甫忠军看着戴天娇,看上去好像是无话可说。他弯腰抓起一把瓜子,说:“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问问你,”戴天娇说,“你是什么意思?”
皇甫忠军听到后,笑了:“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说完他举起双手,做了一个篮球场上暂停的动作。然后,把两个嘴角向上一翘,冲着戴天娇点了点头。
因为来来往往的人,他们俩的对话大都被覆盖了,只有朱丽莎使劲竖着耳朵听,隐隐约约听进了几句。总之,她知道了在她们这批同学中,皇甫忠军不仅和她有关系,还和戴天娇有什么关系。她感到心又紧缩了一下,忽然觉得今晚的一切都那么叫人感到不舒服。
朱丽莎站起身,大声地对于海说:“于护士,我有点事,先走了。”说完,她用眼睛狠狠地剜了皇甫忠军一眼。
接着就有人起哄,要求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于海的脸一下子红了,倒是新郎很大方,他操着地道的四川口音:“没得啥子介绍的,那个时候,我是病号,她是医生,我追的她。”
“他说的对不对?于海。”有人在喊。
于海的脸更红了,干瘦的脸被笑容揪得紧巴巴的。
“我来作证,”突然,皇甫忠军说道,“说起来,我是他们的见证人。叶明就是第一个来找我说的。对不?你小子。”
给于海解了围,于海用眼睛偷偷地看了几眼皇甫忠军。的确,今晚他看上去要帅得多。不过,于海是一个务实的人,她知道自己的条件,所以从不去做不切实际的努力。她知道你皇甫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真正爱她的。可是她也知道,皇甫对她来说总是充满魅力的。只是她更懂得克制。
王萍平对护士长说:“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告辞了。”
说完四个人像小鸟飞出笼子一般,起身离开了。
“我看皇甫忠军这个人挺讨厌的。”回到宿舍,夏冰就这样说。
“我是说他长得帅嘛,”任歌说,“难道不是吗?”
“我看今晚倒像是他结婚。”王萍平说。
朱丽莎并没有口到宿舍,她站在一条皇甫忠军必经的路的一旁,她在等待着皇甫忠军回来。她的身子隐匿在一棵茂密的树下,已经是12月的气温了,站着站着就觉得全身发冷,她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以此来使身体暖和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朱丽莎感到时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得慢,简直是比上大夜班还让人难受。可是,她对自己说:就是不回去,一定要等到他。自从上次他们俩一块到山上去玩后,幽会的时间少多了。一方面,似乎那一次有些败兴而归;另一方面,工作也很忙,总是找不到机会。她知道自己是爱他的,每天在科里交班时,她就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她听来那跳声无比巨大,好像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她简直就不敢往他站立的那个方向看。在和他独处换药室时,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拿不住止血钳。她知道自己无法离开他,尽管离开是最理智的做法。她没有办法,她被他吸引,她渴望每天守着他,听他说话;她渴望被他拥抱、亲吻。她想:如果生活中没有皇甫,没有他的爱,那会是多么的暗淡无光呵。她还想,自己当初坚决要求到一五八来,不也是为了他吗?想到这,她就在放纵自己的情欲,她决心一定要等到他。
这时,几乎每一栋宿舍楼的住家灯都黑了,只有马路上亮着几个微弱的灯,远远的看去像偶而停在一根木杆上的蛮火虫。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几乎能听到山上传来的声音,在她站立的位置,正对着烈士墓山,这时看山什么也看不见,在天光下,一个个灰蒙蒙的墓碑,模模糊糊地。
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晰,听起来这个脚步声过于拖沓,甚至懒散,好像一个无事的人在黑夜里散步。朱丽莎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像是要跳到这无声无息的黑夜里。接着,一个人影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渐渐地她看清了,是皇甫。就在皇甫忠军路过她站立的那棵树时,她猛地站到了皇甫的面前。
“是你,”吃了一惊的皇甫看着朱丽莎说,“你在这干什么?”
朱丽莎一声没吭,一把拉着皇甫走到了树后面,接着她猛地扑进皇甫的怀里,“呜呜”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皇甫一边推着朱丽莎一边间。
朱丽莎使劲地往皇甫怀里挤,皇甫就停止了推她。而是把她紧紧地揽在自己的怀里。过了许久,兴许是朱丽莎哭够了,她对着皇甫扬起了脸,在黑暗中似乎能看到她脸上亮亮的泪光。
“我就是想你。”朱丽莎说。
皇甫仿佛如释重负,一把又把朱丽莎搂住了,他用一双大手在朱丽莎的背上一遍又一遍地摸着,把下巴额放到了朱丽莎的头顶,他的眼睛看着远处,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也不想看什么,他在用心体会他怀里的这个女孩,他忽然有一种羞愧极了的感觉,一种说不清的内疚。在这一刻,他几乎用一个男人的庄严在对自己发誓:爱她,好好爱她。似乎被感动,被这个女孩感动,也被自己感动,他猛地缩回双臂,用双手捧住了朱丽莎的脸,埋下头疯狂地亲吻起来。
许久,他们从激情中走出。朱丽莎说:“你认识戴天娇?”
“戴天娇!”皇甫说,“哦,你的同学呵。算认识吧。”
“你怎么没有和我提起过?”朱丽莎伸出双臂,像抱一棵树一样,环住皇甫的腰,说话时把自己的身子扯得远远的。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皇甫的身子被朱丽莎扯得一晃一晃的。
“那如果我要你说呢?”
“那也要看有没有必要。”
“你是不是觉得戴天娇比我漂亮?”
“真傻。”皇甫说,“在我看来你们都是一样的黄毛小姑娘。”说完皇甫用手指刮了一下朱丽莎的鼻子。
“那你爱我吗?”
皇甫听了这话,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无比深情地看着朱丽莎,突然用嘴堵住了朱丽莎的嘴,含糊道:“爱,爱你……”
戴天娇在心里想:他怎么还算是个男子汉。
躺在床上许久了,戴天娇就是睡不着,在夏冰和王萍平睡着后她又开着台灯看了一会儿书,可是还是没有睡意,怕再把别人吵醒,就关了灯。
脸朝上仰着,天花板还是白的,尽管白得不如白天那么耀眼,可是能看出来。把眼睛稍微向右斜一下,就能从窗户帘上的缝隙里,看到外面的天,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天娇像死了一样,无声无息。于是,又把目光收到天花板上,可是,天花板也不能告诉她什么。就只是自己想事。
当时是冬天,因为下着雪,地上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了,可是天上还在往下下雪,似乎要把整个世界埋藏。冷呵,真冷。这时就什么都不想了,想的全是火,是冒着热气的大脸盆,还想妈。
说是红军,可是这个男孩才11岁。身材瘦瘦的,好像从生下来就没吃饱过。
妈说:“跟着走吧,看样子能有一碗饭吃。”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就是走路,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有大人领着,路上不停地喊着,走呵,别停下,再往前就有热乎乎的大米饭吃了。就跟着走,也不敢停,到处是雪,连个人都看不见,离开人还不得死吗?
看一眼男孩,能吓人一跳,就一双大眼睛,一点神都没有,跟死了一样。
终于,男孩说:“不走了。”说完就像抽了骨头一样,软在地上了。
大人说:“就把他扔这吧,在雪地里还臭不了。”有几个一块走的,回头看了看,也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雪已经盖了男孩一半。天已经快黑了,如果天黑了还没有人来,那么这个男孩就死定了。
男孩醒来时,首先感到的是脚暖和了,动了动脚,一下踹上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又软又烫、男孩就想起了妈妈,这不是妈妈的奶吗?
“妈妈。妈妈。”男孩喊着。
可是周围“哗”地笑了。原来,男孩被几个女红军拣了,救了。
后来才知道,给男孩暖脚的是一个15岁的姑娘,倒是后来成了大家伙的笑话。
救了命呵。
这女人可了不得。是一个真正的女英雄。打起仗来比花木兰还嘎,像个小子。
这是爸爸给她讲的一个故事。在戴天娇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太忙,忙得没有时间讲故事,不过,爸爸好像也不会讲故事,他把戴天娇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讲故事?不好不好。”
可是,有一段时间,爸爸不忙了,很少去上班了,只是开会,每次一开会回来,爸爸就不高兴,小小的戴天娇能看出爸爸的脸色,一声不吭地靠在爸爸坐着的沙发边上,给爸爸送上报纸,爸爸把报纸放在一边。
“你不是要爸爸讲故事吗?”爸爸说,“那就讲一个。”
于是,爸爸讲了这个故事。听了这个故事,戴天娇第一次感觉到,雪是很可怕的,在她过去的记忆里,雪总是和童话连在一起的。从小生长在南方的她,几乎没有见过真正的雪。
“后来呢?”戴天娇问。
“后来这个小男孩被救活了。”
“后来呢?”
“长大了,他们后来都长成了大人。成了勇敢的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还把老蒋打跑了。”
在这个夜晚,戴天娇的眼前出现了爸爸曾经讲过的情景。由此,她又想到了远在省城的爸爸,她忽然特别特别想他。到了一五八以后,她几乎每星期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总是妈妈接的,每次妈妈都说,你爸爸说他没有什么说的,叫你好好工作。这时戴天娇就想笑,她完全可以想象她的老爸爸坐在一边,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看着在打电话的妈妈,样子认真极了。
她脑袋里忽然又跳出了皇甫忠军,看上去那么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怎么能在大操场上边说出那样的话?不管怎么说,他还算是个男子汉,还敢说敢当。不过,他会告诉我什么呢?戴天娇想。
想着想着,觉得两个眼皮打起了架,就睡着了。
这一夜戴天娇做了个梦:一个女人美极了,脸是白色的,像黑白照片一样,穿着碎花花衣服,梳着烫成花的短发。飘到了烈士墓山上,墓碑奇怪极了,都是水红色的,像一些水晶做成的,女人就只是对着戴天娇笑,笑的时候,戴天娇就觉得是妈妈,她就叫妈妈,女人不答应,女人跑,跑得很快,后面有人在追,好像是那个哑巴男人,那个女人跑到山边上,掉了下去,哑巴就哭了,戴天娇怎么会在山下面看到那个女人,一看是妈妈,摔死了,脸白白的。戴天娇就哭,哭呵,哭……
自从来到一五八以后,任歌已经收到了三封妈妈的来信了。妈妈的信总是不太长,似乎总是在匆忙中完成的,可是,每一封信都浸透着母爱。任歌知道这一切,她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看妈妈的来信,她甚至后悔在学校时对妈妈的态度,好几次她在桌子上铺开信纸,她写下: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爱你,我想你……
刚刚写下这几个字,任歌脑袋里就出现了临毕业的似乎妈妈来学校看她时的情景,现在她想起来觉得很后悔。
任歌把信纸揉成一团,她知道尽管她在心里深爱着妈妈,可是,她无法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她觉得从她记事起,她和母亲之间就没有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作为文工团员的母亲,下了很大的决心生下了她,她的出生既是母亲作为母亲生命的开始,也是母亲作为一个舞蹈演员生命的结束,母亲在她身上投入的情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她没有幸运到有一个可以管她的外婆和奶奶,让她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她就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可是,那是一个总在为事业忙碌的母亲。
任歌的父亲是一个作曲家,他在很多时间里生活在一个属于他个人的音乐世界里,他时常会忘了就在他身边玩耍的女儿,他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他的音乐里,总有一个又一个大型交响乐轰响在他的胸腔里,可是,作了一辈子曲的他,真正能够搬上舞台的却是一些他最不屑的音乐小品,小歌。他的一切总是那么不合时宜,可是他又总是那么对于这种不合时宜不管不顾。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抱怨,没有仇恨,也没有音乐以外的东西。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