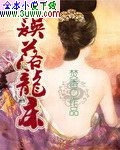寂寞单人床-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房东是四十岁的女人,她儿子今年才十三岁,没什么危险。”她垂下眼帘,淡淡地说:“而且,我还没有打算回去。”
“为什么?”耿于介不肯放弃,使力制住她想挣脱的动作。他的身体坚硬而有力,涂茹根本挣脱不开。
到后来,她累得直喘气,瞪他一眼。“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放手啦!”
一向言谈举止都优雅得体到惊人的耿于介被直接斥责,而一向安静柔顺的涂茹居然开口骂入口。
分别的日子,确实让两人都有所转变……而他们,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好不容易挣脱了纠缠,耿于介被指示去坐下。不过床边椅子上摆满了书,他索性就坐在单人床上。涂茹则是藉烧水泡茶的机会躲开他,至少,拉远了一些距离;否则,被他抱着,她根本没有思考能力啊。
耿于介很快浏览过斗室,不放过一丝一毫细节。
这个房间被她整理得非常好。虽然迷你,但非常温馨整洁,每个角落、每样小东西都可以看出她的巧思。家具很少,也很旧,用的物品都很廉价,但和他们的豪宅比起来,却多了一份人味。
小小的书桌上摆放着几本书,有一本摊开着;台灯旁边有个瓷茶杯,茶杯前则立着一张小小的纸片。仔细一看,耿于介才发现,那是他们结婚时的谢卡。
他的心头突然一暖。这么不显眼的小事,却证明了她也在思念他。要不然,为什么要一面看书、一面把他们的合照放在眼前呢?
茶杯旁边还放着一盒已经开封的成药。涂茹端茶过来时,耿于介微微皱眉,语带责备地质问:“你感冒了?为什么不看医生,自己随便买药来吃?”
“只是小感冒而已。”她轻描淡写,把茶交给他,自己则转身去搬开椅子上的书本,准备要坐──也就是不打算坐他身边。
耿于介才不管,长臂一伸,又把她捞进了怀里,按在大腿上坐好。这才是她该坐的位置。
“啊,不要这样……”
“别打翻我的茶。”耿于介充耳不闻,自顾自地喝茶。为了怕打翻热茶会烫到他,涂茹只得咬牙乖乖被他搂坐着,不敢乱动。
“这房间很不错。装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些有兴趣。”好半晌,耿于介才慢条斯理地开口。
“我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涂茹解释着。她从小到大都对劳作、工艺、家政之类的课有兴趣,只是读书时做这些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结婚之后,却又因为家里太豪华,毫无用武之地──她根本不好意思把拼贴碎布制成的抱枕放在价值数十万的沙发上。
就是这样的差距拉开了他们俩。在华丽的牢笼里,她无用武之地,连生孩子都失败了,她还有什么价值呢?
宝宝不在了,日子却正常过下去,正常到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正常到令她再也无法忍受。
看着她的脸蛋又黯淡下来,露出落寞的神情,耿于介放下茶杯,俯近,轻轻的吻落在那不断勾引他的小小泪痣附近,像是安抚,又像在品尝着她的泪。
一接触到她柔嫩肌肤,耿于介就像是尝到了迷药,浓烈的渴望中夹杂着心疼,一路吻到她的唇际。
“不行,我感冒……”
“已经太迟了。”他又覆盖住那柔软的红唇。
她尝到了茶的清香,以及渴望的热度。当他修长灵活的手指开始解着她陶前钮扣时,她晕眩到觉得整个房间、整个世界都在打转。
这是她的丈夫呀!她以身体、以心灵倾慕着的男人。今夜的他像是冲破了所有文明礼貌的外衣与约束,赤裸裸表现出一直苦苦压抑着的情绪──
火辣辣的吻一个又一个,落在她的颈、印上她被扯开外衣、裸露的肩头;当他的长指游移到内衣肩带附近时,涂茹战栗着,奋力在灭顶之前,挣扎推开了他。
“为什么?”被拒的男人挫败地低吼,无法接受。他恨不得立刻把她吃掉、吞进肚子里!压抑了好几个月的欲望,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要这样,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我们是夫妻,名正言顺,一切合情合理合法,哪里复杂了!”他知道自己的口气是破天荒的凶,但,这不能怪他,真的。
更何况,所谓的复杂状况,正是他拿手的项目啊。在医院里面,住院医师报complication上来,都是他在处理。
“可是,我还没有想清楚。”涂茹坚持着,虽然软绵绵的,却依然努力捍卫着自己的空间与自由。“如果我们又这样,那、那我搬出来就没有意义了。”
“你搬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
涂茹看着他的眼光,让他觉得自己的问题很蠢。“因为在你身边,我会太轻易就妥协,没办法好好疗伤,会一直有怨气,又一直压抑。”
“婚姻相处,不就是要妥协吗?”耿于介还是不懂。“我本身就是医生,在我身边为什么无法好好疗伤?我可以照顾你啊。”
“那,你妥协了什么呢?”她安静反问。
“我知道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但是已经在别的部分尽力补偿,只有时间这一点上面,真的分身乏术。这样不算又妥协、不算照顾?真的那么很不可原谅吗?”
要什么给什么,宠她宠到极点,连她执意要搬出来这件事都硬是吞忍下来,这样还不够吗?
“不是不原谅,而是……而是再这样下去,我连自己都没办法原谅了。”她轻轻地说:“不过,也许我对婚姻的要求实在太高了,高到不惜福的程度,才会被惩罚,所以留不住宝宝。”
耿于介震惊莫名。“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她只是淡淡地弯了弯嘴角,像是苦笑。
流产之后,她从来不曾主动提起过孩子的事。到现在耿于介才发现,她不是淡忘了,而是记得太深,根本无法面对,更遑论提起。
以医生,尤其是掌握生死的外科医生身份来看,他确实有着职业性的冷静;对他来说,孩子没了固然伤心,但很快就可以收拾心情,甚至继续努力;但对于母子连心、和宝宝有密切联系四个多月的涂茹来说,根本不是那么简单,伤痕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愈合。
只因为她安静老成,就认定她成熟到可以淡然接受?耿于介渐渐看清了自己的粗心与忽略,对她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我想跳脱一段时间,一个人过过看。要不然,我会被怨恨和自怜给淹死;而且,会一直一直要求你,对你发脾气……这样会比较好吗?”
他不知道。只知道,没有她在的家,不管再豪华、再舒适,他都没有回去的意愿。
反过来想,没有他的家……她为什么要守着呢?如果角色互换,如果是他每天这样等着另一半……他能等多久?
想到这里,他已经没办法再继续想下去。
耿于介整个人安静下来,涂茹也轻轻的挣脱了他的拥抱,低着头整理好衣服,小心退开了几步。房间小,所以退了几步,就到了墙边。她靠着木板墙,背着手,静静等着他。
两人实质距离不远,只有几公尺,但感觉上,却好像相隔了一整个海洋。
别人的恋爱、婚姻,看起来为什么都很简单?而他们,明明气质外貌都超级相配,明明都是一见就动心,明明可以很顺利的,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动心是一瞬间,但相爱不是只有动心。
婚姻需要的是经营。如果没有经营,再强再戏剧化的动心与吸引力都会渐渐淡去,被生活与彼此的不同点给磨损殆尽。
有人是先经历了惊涛骇浪,恋爱成熟之后,得到结婚这个甜美果实;而他们,却好像整个反过来了。
默然相对,安静凝视,两人都在自省,也都在深思。
耿于介离去之后,涂茹整个晚上都陷在恍惚之中。躺在一直想要、终于得到的单人床上,应该要很舒服的,却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睡。
她开着小灯看书,一本看完了,又拿起一本。看着看着,却没办法投入剧情中。想到耿于介之前就坐在这个位置,两人还差点擦枪走火……她翻过身,把发烫的脸埋进枕头。
当初出走的时候,她很确定自己没有冲动。但是现在想起来,却开始动摇了。到底,在坚持什么呢?是要逼耿于介放弃工作或至少不要支援外院、不要再两地跑了?毕竟一个职位就够忙……
她是在消极的威胁或抗议吗?她原来是这么一个狡猾又任性的人?
可是,当时她真的快要窒息了。像是野兽受伤之后、断尾求生的反应。如果继续留在他身边,伤口表面会愈合,但里面一定会渐渐溃烂。
训练自己独立一点、不再那么在乎或依赖之后,她会回去的。要当耿于介的另一半,在物质上也许很轻松,不用担心;但是在精神上,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这是外界从来不曾考虑过的。就连涂茹自己都没有料到。
没料到的,还有自己对他的依恋,以为会因为分离而减少,结果,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爱不是应该会让人坚强吗?为什么却让她变得如此软弱?
思前想后,辗转反侧,直到夜深,才好不容易暂时被疲惫打败,沉沉睡去。
结果才睡没多久,涂茹就被惊醒了。黑暗中,她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有人,那人不但坐在床沿,而且,还握着她的手。
不是耿于介!这只手的触感,根本不是他!
涂茹吓得猛然坐起,尖叫声黏在喉咙中,根本发不出来,全身都在颤抖,肌肉僵硬到几乎要抽筋。
“嘿,是我。怎么吓成这样?才几天没见,不认识我了吗?”故作轻松的嗓音,让涂茹辨识出了来人。
是消失了好几天的曹文仪。也只有她有这儿的钥匙,可以登堂入室。
“你……吓死入口!”惊吓还没恢复,涂茹的话声颤抖着,伸出去开灯的手也在发抖,努力了好几下,才把旁边的小台灯扭亮。
曹文仪嘲讽地笑笑。晕黄灯光中,她的憔悴显而易见。平常戴的棒球帽不见了,参差不齐的短发乱糟糟的,脸色不太好,黑眼圈好明显。
“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都不肯联络?”涂茹忍不住要责备她。“我很担心呀,以为又发生什么事了。下次不可以这样。”
像大姐姐教训妹妹,涂茹的长姐风范终于显露出来。曹文仪又笑笑,没有回答,只是转移话题:“床垫搬走了?房东太太来搬的吗?有没有罚你钱?我应该要帮你出的。不过反正你老公财大气粗,根本不稀罕这一点点零头。”
“我没有用他的钱,你很清楚。”涂茹打断她。“而且,他没有财大气粗。”
曹文仪的眉一挑,很挑衅。“又心疼了?讲两句都不行?你也太护着你老公了。既然这样,干嘛还分居?快点回到他床上去吧。”
“文仪!”涂茹真的生气了。“不要再说这种伤人的话了。我和他的事情你很清楚。如果没办法理解,至少也请你试着尊重,可以吗?为什么你要一直攻击跟你亲近的人呢?不管是朋友还是男友,都不该这样被对待!”
曹文仪闻言,脸色陡然冷了。“是不是那个姓夏的跟你说了什么?你跟他谈过了?”
夜里寒凉的空气袭上涂茹衣着单薄的身子,让她打了个冷颤。
“夏先生没有说太多,只说你们分手分得不太愉快。但是都过去那么久了,两方也都有错。文仪,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好坐下来谈?”
“我为什么要跟他好好谈?!”曹文仪暴躁地打断。“为什么一定要被男人摆布、一定要围绕着他们转?凭什么男人不管是忽略你、外遇、厌倦了、不想定下来……都可以被原谅?你搬出来,不就是决心要逃离这种苦情小媳妇的世界吗?还是说你的奴性又回来了,决定要回去当哈巴狗,整天乞讨着主人怜爱?”
眼看她越说越大声,涂茹当然不是跟人对骂、吵架的料,只是用那又黑又深的眼眸望着好友,任那伤人的字句如狂风暴雨般鞭打在身上。
“文仪,你是专程来跟我吵架的吗?”久久,她才轻轻地问。“我让你很生气?”
“不是。我只是受不了你这种不果断的个性!已经讲过多少次,要就要,不要就不要;爱就爱,恨就恨,不要半调子!”
“所谓的爱恨分明,就是跟人家说你前男友死了?去刮花、破坏他的车?去他住处的门锁里灌三秒胶,让他没办法进门?把对方的证件、印章扣留,不肯还?文仪,这不是爱恨分明,这已经是……已经是……”
已经是什么,涂茹根本说不出来。她乍听夏先生的叙述之际,确实震惊到无法相信。但是看曹文仪此刻凶狠的表情,涂茹的心沉了下去,知道她那位前男友所叙述的,八九不离十,并没有捏造。
“那……都是他活该。”曹文仪只是简单带过,捏紧了涂茹的手,用力到让她有点疼。
涂茹又不语了。
每个人都表里不一,都好复杂。爽朗外向的曹文仪,有着如此阴暗的内在;而她,从小到大众人公认的乖乖牌,内心也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执拗跟别扭。
好累、好累。
“所以,你打算这样下去?”终于,涂茹轻轻开口问。“拉着我作伴也不是办法。文仪,你报复了他,这样真的快乐吗?一直钻牛角尖,何必呢?”
“那你呢?这段时间以来,你又有多快乐?说我钻牛角尖,那你自己又怎么说?”曹文仪尖锐反问。
“我不快乐。可是,我也不是在钻牛角尖。”面对指控,涂茹蹙着眉,不甚同意。“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
这还不叫钻牛角尖?照涂茹的方法想下去,再想十年大概都不会有结果。
没有一点刺激,大概是不可能前进了。而涂茹那无用的老公,跟涂茹一样走温良恭俭让路线,宠老婆宠到死胡同里去了,两人就这样卡住。
曹文仪望着好友带点苦恼、轻愁的娟秀脸蛋,若有所思了好久、好久。
她的公主。王子为了她可以去屠龙、冒险、砍砍杀杀,都要让她生活在玫瑰花环绕的宫殿里,单纯快乐的过日子。
可惜,她只是假冒的王子,背着重重的包袱,有自己的恶龙要屠杀。她始终无法让公主展开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开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