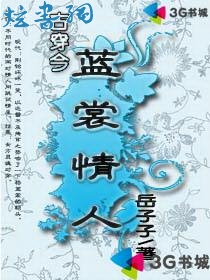情人座上的影子-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岢易望着她。接在她的味道之后,他爱上她的灵魂、她的身体、她的温柔、她的聪明……
他对她的爱多到连一天都不肯多等下去,不管了,不管她有没有暗恋的男人,他都要告诉她,他爱她,他要当她的男朋友,从今天正式开始。
话没来得及开口,杜家电话响起。
“这里是杜岢易的家,目前不方便接听电话,有事请留言。哔……”
“臭岢易,你到底去哪里了啦?你手机不接、电话不接是什么意思啦?我爸出车祸了,现在人在加护病房,还没脱离险境,呜……臭岢易、坏岢易,你到底跑去哪里了啦?你再不出现,我就要跟你绝交……”
那是丫头的哭声。
她的声音让杜岢易分心,以致没注意到自己的咖啡壶没拿稳,滚烫的咖啡正往姚子夜的手背浇去,他随手丢下咖啡壶,冲到电话旁,接起电话。
姚子夜很痛,但痛的是心,不是受伤的手背。一听到丫头的声音,他便忘记姚子夜,忘记姚子夜也一样会哭、会痛,会想要他留在身边。
“丫头,是我,你人在哪里……情况怎样……好,我马上过去。”他的口气急促,语调忧郁,他和丫头一样伤心。
挂掉电话,他像失速的火车头,完全无视于坐在沙发里的姚子夜,一下子冲进房间、一下子冲到屋外,再不久,当她听见摩托车急驶而去的声音时,缓缓地,嘴角渗出一抹苦笑。
她怔怔的看着没关上的大门,像被定身般,一动不动。
她在等,等岢易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一个姚子夜,也许他会调转车头,接她一起到医院,那么,她会和他一起安慰丫头,陪她哭、陪她笑,充份尽到身为好朋友的责任。
但……他并没有,当壁上的时钟滑过两格之后,她对于等待,死心。
是丫头的哭声乱了他的心绪?否则他怎么会慌成那样,不过是朋友的父亲啊。
她从没见过他那样失控,失控到看不见自己伤了她。
因为那个朋友是周采萱的关系吧,他们的生命,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叠在一起。
端起冷掉的黑咖啡,上面没有她期待很久的爱心,也没有加入糖粉的甜蜜,连香气也早已蒸发殆尽,她仰头,赌气似地,一口喝尽。
好苦,苦了舌头、苦了心,苦得教会她知道,这个叫做报应,报应她企图抢走好友的男人,报应她为了赢,不择手段。
低头,被烫伤的手背像在嘲笑她的愚蠢,一阵阵痛着,她背过很多次冲脱泡盖送的口诀,可现在像被点了穴似地,无法挪动身体。
时钟指针缓缓向前推送,姚子夜看着手背从红、到微微焦黑、到起水泡……那一点一点成形的,不只是她的手背伤口,还有心底哀恸。
她在杜家等过一天一夜,然后起身,拿起自己的行李,回家。
姚子夜始终联络不上杜岢易,但她联络上周采萱,丫头哽咽地说,她的爸爸还在加护病房,尚未清醒。
身为朋友,是该去探病的,因此她买了香香的百合花,走一趟医院。
半路上,她想着该如何安慰丫头,也想着该对岢易说什么,但这些话都来不及说,便一口气被歼灭。
她看见了,在加护病房外面,岢易紧紧抱着丫头,他亲着她的额头、亲着她的发梢,不断低声安慰她。
他们的动作亲密、态度亲密,亲密到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爱她。
姚子夜退了两步,把自己隐身在走廊边,就像隐藏着手背上的伤痕。
经过很久,探病时间到了,岢易环着丫头进入加护病房。
她从头到尾没现身,安静地离开医院,因为安慰……有杜岢易给,就足够。
几天之后,姚子夜打电话到杜家,是杜妈妈接的。她说,岢易一直待在医院,没有回家。
光是朋友交情,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所以一天一天,她深信,他爱丫头、丫头爱他,而丫头的矢口否认不过是欲盖弥彰的谎言。
第二十七天,她独自从妇产科诊所离开。
医生说她怀孕了,这是比放榜更吓人的消息。
她很慌,却不准自己表现出慌张,她刻意抬头挺胸,刻意把骄傲写在脸上,她不想看见任何人的同情,包括她自己。
岢易的手机还是没人接听,三天前,杜妈妈说她要出门,要帮岢易把换洗衣服送过去。
姚子夜想也不想,就往医院走。
她当然知道,现在不是和岢易讨论这种事的好时机,她也知道,要谈判必须先武装好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她甚至知道,最聪明的做法是先回家、沉淀心情,并且,她该谈的对象是杜妈妈而不是杜岢易。
她清楚杜妈妈喜欢自己,她相信杜妈妈会让岢易为她负责任,届时,就算岢易再爱丫头,仍旧会为她将就妥协。
但,这种赢法不光彩,她不要,她宁愿选择笨蛋的做法。
她又带了一大束香水百合在病房前站定,丫头的父亲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她敲敲门。
来应门的是丫头的母亲,她热情招呼姚子夜,“你来了,快进来。”
“伯父好多了吗?”
“对,前天总算可以拔掉身上的呼吸器,整个人轻松很多。”
姚子夜点点头,把花交给周妈妈,侧身,她看见单人床边的沙发上,杜岢易环着丫头,两颗头颅相互贴靠,沉睡。
“这两个孩子昨天在这里照顾爸爸到天亮,我来了,叫他们回去睡又不肯,实在是……”
周妈妈爱怜地看着杜岢易和丫头,然后拿着花瓶到浴室里装水。
两个孩子的爸爸?双方家长对于他们俩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认定?唉,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岢易的决定。
她走到沙发边,轻轻推了推岢易,他一下子就醒了,可见他不敢沉睡。
“子夜,是你!”杜岢易看见她,咧出一个温柔笑脸。
“谈谈好吗?”她指指门外。
“好。”他侧身,小心翼翼地把丫头放平,再用棉被把她盖紧,回身,解释什么似地说:“她很会踢被子。”
姚子夜没做反应,轻轻走出病房,杜岢易随即跟上。
他们在楼梯间站定,楼梯里来往的人少,大部份人都选择搭乘电梯。
她仰头望他,他瘦了,眼睛底下有着淡淡的黑眼圈。照顾病人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他却抢着承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这么好吗?还是对丫头特殊?
她想,答案是后者,如果这是他对待朋友的标准,那么,他会很累。
“你的手怎么了?”他发现她的手裹了密实的纱布,直觉抓起,心疼不已。
终于发现了吗?可惜有点晚,二十七天前就该发现的事,拖到现在……唉,她在想什么?她又不是丫头。
她讨厌自己的嫉妒和狭隘,可是她无法阻止自己。
“快说啊,你的手怎么了?”
低头,他抚着她的手,细细察看。
她很晚才就医,又不肯认真回诊换药,就这样,伤口时好时坏,医生恐吓她,再不好好照顾,以后会留下疤痕。
她并不在乎是否留疤,因胸口的伤痕比手上的更深更大,而且那道伤,叫做咎由自取,她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说,那天被咖啡烫伤时,她仍未觉醒,那么在医院看见他和丫头的亲昵时,也该醒了。只是呵,心底就是不甘愿,非要逼他表态些什么才行,所以,她来了,面对面,她试着做好被撕裂的准备。
“那个不重要。”她淡淡说。
“谁说不重要?你不说,我们就去找医生来说。”
他恼怒了,抓趄她的手,要带她去挂门诊,反正这里就是医院,别的不多,医疗人员多到可以当布景。
他好看的浓眉聚在一起,仿佛她的伤是罪大恶极。
真要听?好啊,他都不怕了,她怕什么。
带点刻意,她道:“旅行回来那天,你给我倒咖啡,然后丫头打电话过来,然后……就这样了。”
原以为不想不提,事情就会过去,谁知道才说了两句,那天的情景浮上心头,她想起那杯冷掉的黑咖啡,胸口就隐隐扯痛,仿佛有碗大的裂缝汩汩地渗出鲜血,酸涩的滋味充斥在唇舌间。
“这是我弄的?”杜岢易不敢置信地望住她,眉头拧得好紧,大有砍自己两刀的街动。
“没事,别在意,是医生包得太夸张。”她把手缩回来,放在背后。
“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包这么夸张?”他直指出事实,果然脑袋比别人好,一看就看出问题。
“有点重复感染,不谈那个,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重头戏来了,心在胸口擂鼓,一阵阵敲得她头晕,她很害怕也很紧张,她忧心他的反应是自己预估的那样,害怕他不要孩子,和她想像中一样。
“什么事?”他想不出有什么比她受伤更重要的事。
深吸气,姚子夜快速让四个字滑过嘴皮,“我怀孕了。”
震惊、恐慌、懊悔……无数情绪在他的脸上交织张扬,他盯住她,微张口,却好半晌说不出话,就这样,两个人僵立在楼梯旁。
许许多多的问题瞬地跃入脑海里,纷杂、乱章,乱得他的理智尽失。
很久很久,久到他连时间过去多长都没有概念,他只能看着她、望着她,发不出半点声响。
他们才十九岁,年轻的他们可以提供孩子什么样的生活与教养?
他会不会长成另一个渴望父母专注疼爱的杜岢易或姚子夜?如果十九岁的他们没有共同未来,孩子该怎么办?他能为了孩子而绑住子夜一生,像父母亲为他做的那样?
“你想留下他吗?”
终于他开口了,却丢出一个无情的问题,像冰水,狠狠地往她头上浇,冻得她嘴唇发紫,这回,她连微笑都挤不出来。
“我想听听你的说法。”她压压腹部,把满腹委屈压抑隐藏,刻意让声调淡漠得一如平常。
他能有什么说法?他想要孩子啊,那是一个生命、是他的骨血,他怎么可能不要?
问题是,他哪有资格要他。
杜岢易背过身,紧握的拳头像在抗议什么似的。只是背影,姚子夜已经看见他的愤怒。
在生气她吗?气她没做好保护措施,还是懊悔不该带那瓶红酒,让那个旅行放纵过度?好吧,错都算在她头上,她可以拒绝他的,是贪心惹祸,那一刻,她真的不想只做他的朋友。
岢易背着她,没发现她也很软弱、很恐慌,她的笃定和骄傲都是假的,他不知道她多想靠上他的背,从身后圈起他的腰,哭着说:“我真的好害怕。”
但是,他与丫头的亲昵让她却步,他的愤怒让她不自觉后退,她想,他肯定很恨她。
女人真是祸水,国二有个女生用跳楼来逼出他的罪恶感,高三又有个女生用孩子的命来迫害他。他怎么可能不恨?
全是她的错,明知道他和丫头才是一对,偏要加入中间,终是尝到苦果了吧,若是不放纵、若是谨守份际,他还会当她是好朋友,现在呢……通通毁了,老话说得好,自作孽不可活。
爱上他,是天大地大的错,偏她还要写出那封毫无自尊的信,偏她还要任欲望无止境蔓延,偏是还要为他,赌上未来四年……
姚子夜,你不值得同情!
终于,他回过头,捏紧的拳头放松了,大手搭在她肩上,他的手是冰的,带着些微湿气,他的脸严肃得让她认不得,而他嘴里吐出来的字句,冻死了她全身上下千万个细胞。
“我们才十九岁,没有成熟到可以负担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我们要念大学、要上研究所,我们要出社会、要工作,目前的你我甚至连自己都养不起……”
话说到这里,她听懂了,心迅速往下沉入地心,任岩浆烧灼焚化,疼痛从牙龈间漫开,紧咬的牙关咬住不能出口的哀号。
“子夜,你那么优秀,不该让一个孩子限制未来,总有一天,你会后悔,况且我们生下他,对他不公平,我们没办法全心全意爱他、照顾他,他不应该在父母亲缺席的情况下诞生……”
缺席?说的好,他不想参与,只想缺席……
心焦了、碎了,她愣愣地看着他张张阖阖的嘴巴,再也听不进他又说了什么。
没错,他的话是真理、是最正确的考量,只是,不该由他来说,他给的生命,怎能由他来当刽子手?
可怜的宝宝,未成形就被判处死刑,这是个多么残忍的世界。
真是的,她的预想真准,居然估得分毫不差,知道他不要这个小生命,知道他说“不要”可以说得这么顺畅。
她可以改行去算命了。
千针万针扎着她的每条神经线,痛死了,可她挺直肩,维护着可怜的骄傲,她忽略手脚在发抖,心脏在狂嚣,她甚至……还能在脸上保持住淡淡的微笑。
“很好,很高兴我们有了共识,这个孩子,我们的确要不起。”姚子夜低了低眉,再抬眼时,深吸气说:“就这样了,我会找个时间去动手术。”
转身,她迅速离去。
“我陪你去!”杜岢易飞快追上她,抓住她的手臂。
“担心什么?我不会偷偷生下小孩,二十年后跳出来找你分家产的。”她再也忍不住,话里带上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放心你一个人面对这种事。”
“你能陪我进开刀房?能代替我躺在手术台上?对不起,这种事,我终究要一个人面对。”
甩开他,她大步走,她必须走得够快,才不会让眼泪飙下来,她不想哭,不想在他面前软弱,是,她想要人家的疼爱关怀,但她绝不向他乞怜。
这一走,杜岢易失去她,整整九年。
第五章——被雷劈到般的重逢
“你知不知道九年有多么漫长,有多么难以等待?
你半点音讯都不留,让我像无头苍蝇地四处冲撞,
你知不知道到处都找不到你,我有多心急?“
像无头苍蝇的他,说的话也像无头苍蝇,
一口气撞痛了她的心,差一点点,撞坏她精心制作的虚伪面具。
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两个男女视线相对,像触电般,他们都栘转下开视线。
是他!她又怨又恨,却又割舍不下的男人。
是她!他又想又念,日日夜夜眷恋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