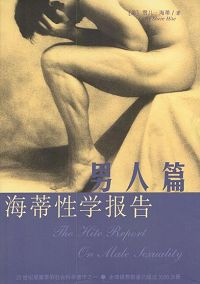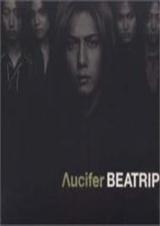恶质男人-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住一晚。好险她在台湾登机前曾去电通知对方的助理,要不然她在飞机上一定会坐立不安。
从下机、过海关入境到提领行李的这段路上虽然拥挤漫长,但人与物件一切平安、没有突发状况。她站在入境大厅等人来认领,不到十秒,就有一个黑人帅哥领着一个孕妇晃到她面前,冲着她笑。
黑人帅哥俏皮地比了一下搭在孕妇肚前的牌子。从右比到左,尽可能咬文嚼字她用拼音说“那——令?”那绫点头,但快速伸手往写了她大名的牌子比来,这回是从左比到右,顺便校正他的发音,“那——绫!”那根指头还刻意往上扬。
等到她发现他们皆以一种看待EQ的表情望着她时,她才警觉到平仄音的手势对老外来说没任何意义。她以洋文慢腔慢调地道歉。
大腹便便的孕妇马上安慰她,“别道歉,因为这又不是你的错。纽华克机场反而离齐放住的地方近。我是安妮,他叫约克,是齐放的助理。你一定累了,让我们尽快送你到齐放那里休息。”
黑人帅哥绅士地将那绫的行李接收过手,三人坐上一辆自用车出了机场领域,经过纽泽西州,往纽约市中心开去。那绫一边睁大眼吸收周遭景观,一边拉长耳朵听同伴聊天。
行车间,他们解释,“本来照计画,齐放要亲自来接你,但因为飞机晚一天抵达,公司大老板正巧又在今日安排一个酒会,他算是半个主人,分不下身,使请我们先带你到他的住处休息。”
约莫四十分钟后,车子开进纽约最繁忙的曼哈坦区时,已是华灯初上,原本细管霓虹的小店招牌逐渐被高耸撼立的摩天大楼取代,大型广告看板,盏盏闷气明灯及缤纷绚丽的彩色三角条旗相互竞逐,锦上添花地将一幢幢豪华富丽的摩天建筑物衬托得更加夺目。
由于正值下班用餐时间,车多人更多,衣冠楚楚的男土与时髦的社交名媛逐渐占据街头名店,表示夜生活才刚要开始。
约克的古董金龟车停停走走,硬挤在光鲜大型名牌轿车中,从空中鸟瞰,象极了被装甲坦克夹击的小虫子。约克告诉那绫,齐放住在曼哈坦上西区的一幢大厦吧,他的公寓面对赫逊河,不论晴而都有很好的视野,附近有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央公园、美食卫,她有空可以去逛逛,包准会有收获。
那绫率真地问约克和安妮,“齐先生人好不好?”安妮和约克快速地在后照镜里交换眼神,仿佛对她提出的问题感到匪夷所思。
约克是男生,个性比较直,坦率地反问那绫,“我以为你们认识。难道你从没见过他吗?”
他见那绫摇头,先道了声歉,马上问后座的安妮。“怎么办?是不是他们搞错,误会齐放的意思?该不该打电话问他一声住处的事?”
安妮看了一下手上的行动电话,再审视那绫一眼后摇摇头,然后迳自和那绫聊天。“我们的老板不算差!”意思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爱摆阔是惟一令人诟病的美德。”
那绫笑而不答,心里却嘀嘀咕咕,想来也是,要不然也不会省到让我这个陌生人入侵他的窝。
安妮继续表达她的看法,“在工作上,他要求很严,骂人很凶,私底下,则是不太爱讲废话,更讨厌别人跟他嚼舌根。但你只要肯努力,绝对能赢得他的肯定。”
“太好了,我正希望他是如此。”那绫违心陪笑,心里却哇哇大叫,还暗地在胸前书了一道十字架。完了,还没拜过码头。就已经开始排斥他,等正式上工共事,麻烦肯定一箩筐。她开始后悔没选花都逛了。安妮对管理员秀出访客证后,车直接开进地下停车场,五分钟后,三人搭乘旧式电梯上到齐放位于三十一楼的公寓。
进门后,约克先行将那绫的行李提到她未来三个月的安身之所,安妮领她参观这幢楼中楼公寓。这公寓虽大,却是开放式空间,厨房、工作室、客厅和餐厅都连接在一起,毫无隔间措施,想来主人是个习惯自由自在,而且痛恨受到空间束缚的人。
概括地看过楼下,那绫踩着雕花的旋转圆梯跟在安妮身后,踏进二楼的一间卧室,这间卧室本身的架构只有梁柱和栏杆,梁柱的四个顶端垂着长长的帷幔,可任人拉上,需要时形成一块隐密的天地。
那绫喜欢极了,不禁用欣赏的眼光打量这个房间。她的目光首先落在一张双人铁床,其雕工朴素雅致,床单床被等寝具皆是白的,尤其她的眼盯上那厚暖的白枕头时,忍不住想往上趴去,睡个一天一夜,但她忍住了,心里笃定地认为这个齐先生没有家眷,不担心隔墙有耳的问题,但当她注意到自己的行李堆放在地上时,反而吓一跳,心生警戒。她问安妮,“我住这一间吗?”
“嗯哼。”安妮点头。“隔壁是不是还有一间?”
“没错。比这间大得多,但都被齐放的衣服占领了。
“喔!原来有两间房。”那绫暗松了一口气。安妮将钥匙交给那绫。“我们只能介绍到这里,细节得等男主人回来后,问他才消楚。盥洗室就在隔壁,厨房的冰箱里有吃的,饿了自己拿。齐放要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不用跟他客气。”
送他们离去后,那绫像小兔子一样咚咚地跳上楼,踏进现代化十足的新颖浴室。她为自己放了一缸八分满的热水,整个身子沉进浴缸里,足足泡了半个小时,才依依不舍地跨出来,套上白棉睡衣裤,钻进软软的被子里,闻着晒洗过的枕头的味道,慢慢进入睡眠状态。
第七章
离开宴会场合,齐放难得不带一丝酒意地踏进公寓住所。虽然他有心理准备,但乍见满室灯火通明时,还是颇不习惯地瞪着吊挂在天花板的灯罩,乃因他常工作到深夜,回房连开灯这等举手之劳的事都懒得做,宁愿绕过客厅的家具,摸黑上楼就寝。
今天他反常了,勤劳地捻掉墙上的灯钮,将搭在肩上的外套随手往沙发一扔,扭身像一只安静的豹子跃上楼梯,目不转睛地盯丰着帷幔的空中阁楼,逐渐陷进自己夜袭的动机中。
他在卧室入口处止步,一手闲置在裤袋里,另一手将黑领结扯松,处于警戒状态的宽肩似有苦无地抵在缺了门板的门框边,寻思半晌。最后,他斜着脑袋,透过法式落地窗外的水灯倒影,双眼勾勒出蜷伏在白色软被单下的身影。宛若通过犀利准确的电脑扫瞄,核对被单下的女子真是他预期的人后,他僵硬的肩头才得松弛。
他立于床侧,眼带柔光地打量沉醉得像睡了几世纪的精灵的女子。
女子宛若被施过咒,记忆中微带红的长发此刻呈放射状地散开,有的在雪白的枕际蔓延,有的盖住她半片娇嫩的容颜,覆住白白的颈项间缠绕下去。他略弯身,魅眼低垂。逡巡她动静皆宜的美丽五官,想捕捉记忆中她或哭或笑的鲜活表情,将她仔仔细细地瞧个分明,但光瞧怎么够弥补他强烈要她的事实?尤其那双微微的诱人红唇虽默然不语。但看在齐放的眼底总觉得像在静候男人一亲芳泽。
每个男人对女人欣赏的角度不尽相同。第一眼看上的地方也略有差异,有人先看胸,也有人看臀,有人重视气质,有人只管五官,也有人只拿捏身材,当然还有脚躁、腰、腿、臂、颈,反正只要女人身上有,男人的眼睛就能膘到哪儿。
齐放当然不例外,他的第一眼多半落在女人的眉眼之间,其眉显示个性,其眼则是藏着灵魂;第二眼才落奋女人的鼻下人中与下唇瓣间;第三眼落在其下巴与颈项衔接处。至于其他部位,只要上床时不影响情趣,即使对方动过乳癌切除手术,他也不认为对方不完美,唯独塞了矽胶囊袋的胸部会让他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话说回来,从眉眼看,通常判断得出女方认真的程度、作为日后好聚好散的指标;从人中与下唇瓣间,他知道透过吻,能探知自己和对方向体内配合的程度,如果第一次的接吻中,对方肯让他的舌四处游走,甚至来个亲密舌战的话,他知道他们离床的距离已不远了;从下巴与颈项间的肤色差异度,他了解该女人对化妆的深度、懒度与自恋程度。
所以女人的眼、唇、下巴到耳垂的这四十五至九十度之间又对他来说虽然称不上黄金旋律,但总是用走了的公式,除非证明出一个例外,否则他到老都不知道这公式有失灵不管用的一日。看着眼下的这号otherwise ,他颇不是滋味地重新将她盘算一次。
她的眉浓顺而有型,是时下欧美正风行的那种,初识她时,他以为够时髦,象那些有空没事就找他泡主题咖啡店打探下一年度流行风的女人一样,为了走在时代尖端,甘愿忍受拔毛的不便,花钱找人大事修理一顿,但现在,正视着她,从她清晰的眉目间,他得知她自然生成的端倪。
她密长的眼睫毛此刻往上挑出优美静雅的弧形,但当时在酒吧里,她莫名其妙说掉泪就掉泪,泪水有温润眼睛的亮丽效果,再加上昏灯与灰雾的堕落作用,他以为她恻了特浓特亮的睫毛膏,三不五时就编着两段“檀香小扇”跟男人调情,睫毛膏对很多宣称懒得上妆的“公认美女”来说是随侍在侧的美容工具,往往有画龙点睛之效,但现在,正视着她,他只觉得若将那玩意儿用在她身上只是多此一举。
通常看完女人的眼睛他会直接跳过鼻子,但现在他连她的鼻子也不放过了,她的鼻圆挺却没有西方女人那种不可一世的高昂,不管正看、倒看、侧看都赏心悦目,她的唇型适中,把茱莉亚罗伯兹和林忆莲的嘴相加再除以二,差不多可得出这样迷煞人却又完全新品种的“惊叹号”,那个“惊叹号”似乎永远是红艳丰润的,让他误以为她涂了红胭脂,被男人吃了浓妆来不及再抹的风华模样,不时诱引他想起多汁甜美、光泽鲜亮的莲藕,想咬一口尝鲜,现在,正视着她,他明白,她的唇原是上帝的杰作,也是市场里贩售的人工口红烘托不来的真品。
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视觉上的第二眼竟与当初的第一眼发生了天大的差别,乍见她的第一眼,他只觉得她算得上漂亮,看起来舒服,但印象也是很笼统不清,甚至可以说粗糙肤浅,他肯定当时只是两人之间玩罢就算了的冲动与协定。
事实证明,太过高傲自满总有栽跟头的一天,一切都错了。
第一个错在他,他不该坏了原则乱报电话号码给她。
第二个错在她,她不该接受他热情假意的误导,天真地打电话给他,再来,早晚打不通就该知难而退接受暗示,没想到她脸皮比铁皮锅还厚,意志力比金钢石还要负隅顽抗,连打了好几个礼拜,让他陷入那种在家若没听见铃声响,就觉得自己短暂重听,甚至到失聪的地步。
第三个错也是在她,她可以是浪女、石女、疯女或妖女,但万万不该是处女,原因在于她没有“处女情结”,但他的情绪可就严重到必须去心理医师那里挂病号了,乃因他懂事后,什么都不讳,只讳处女,她却拐了他。
第四个错,若要公正地说,则是在他,因为他没趁早去看心理医师,现在才会发神经地想跟一个认真的女人发展出长期的关系。
把错清算推卸一番后,对现在这第二眼他又要怎么解释呢?可复杂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将他纷乱的心情一网打尽。
齐放十年前在美国的艺术学院念产品设计时,已是搞现代创意的怪诞高手,现代创意很多时候讲的是见山是山,见山又不是山的狗屎理念,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专门以华丽不实的包装与似是而非的意识型态来欺骗自以为是又看得懂普普艺术之流的顾客的感情,所谓干一行怨一行,等他搞懂自己创了半天却内容空洞的商业作品后,他已成了没定性,不相信广告、质疑权威又鄙视忠实品牌制度的云豹型难缠消费者了,这种漫不经心,不用固定品牌的理念连带套用在过往的女人身上。
所以,若说这个躺在他床上迟迟不肯醒来的精灵有风华绝代到令人茶饭不思是绝对夸张不实的,毕竟和她上次通话不欢而“挂”至今十多天了,他烟照抽得凶,酒照灌得猛,女人照常挽在手臂间从拥挤的舞会场所往陌生的床上带,三次里有两次他的女伴是跃跃欲试,而他却醉到偃旗息鼓的地步,另外一次虽是勃起醒着,也是吐到无能力不了事,好心点的女人肯施给他一条被子让他窝在沙发里呼呼大睡到天亮,恼羞成怒的那一个,则是当场把他当野狗似地赶出门,连一辆计程车都不帮他招呼,除了她那一头栗色科卡狗毛的头发外,他唯一有印象的是她的名字,唯一,象极了眼前这个蜷窝在他被子里面的女人。
行了,总之一句,他呆在床侧犹豫了这么久,找了一堆不成理由的理由拖延行动,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这个女子。
他吁了口气,掀被往床里钻,躺平后,整个身体突然发痛似地急欲偎着她,急切地想感受她曼妙的曲线与埋在她体内的律动,并描绘着自己从未曾在她体内奔驰释放的假想感觉,那一夜美好的种种跳进他的脑海,回忆真切鲜活得就象发生在昨夜,而非隔了久久的三个月。
这三个月来,他过得颓废荒唐,荒谬地是,并没有任何女人与他共享夜生活,不是他染上“认床”的坏习惯,也不是他突然“无能起来”,而是他就是不想要别的女人,也许是尺寸不合让他嫌,起不了那种燕归巢的温馨感觉,齐放刻薄地想着。
他静躺着,不愿吵醒她,但唇却不听使唤地欺近她的唇角,极其轻盈地吻着她,以鼻息逗弄她的面颊,冀望她能在瞬间醒过来。
家是感受到他心里面的召唤,她哼出了声,伸手往空中一拨,似要扫掉脸上的干扰,却在不知觉中替他制造一个机会。他伸指沿着她醉红的唇缘轻探慢捻,制造动乱,再以自己的唇来回厮磨,撩拨情火,也不知是哪根筋不对劲,也许是全部的筋都不对劲,他竟分外享受静静吻她的感觉,即使这一刻不玩攻城掠地的情欲把戏,也无所谓了。
想着,他撤开了身子与她保持距离,享受与她无言相处的时刻,不过十秒,她自动地往他这头挪过来一点,虽然“那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