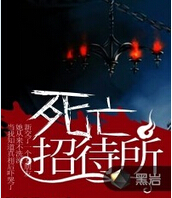过把瘾就死-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岜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岜开了一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又斟满杯,满饮。石岜说:
“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让她嫁给老外。”
他们三歌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里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岜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岜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去。敞开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子。”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岜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岜说,“我三十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屁股上了?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片肉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岜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婊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步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八十呢?”由于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说话已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们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去,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呸!”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屁股,给就给真不要脸的。”
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酒洒了她一身,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象你一样,比你还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岜呢?太不应该了。他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呢?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感,不是欢耍游乐时的肆意放纵;而是你这个年龄时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的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中开放;我要当一只小鸟,飞在空中,只让孩子们着迷……”
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岜,“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岜把唾沫星子全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过来。石岜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象个泡沫灭水机。石岜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咕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岜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岜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我往回推石岜。他身子也已经软了,一推就倒了。
“拉我起来。”他冲我喊,“想起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价吵,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从四面八方奔涌入心脏。接着,□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尤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无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籍的桌前坐下。房间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翁声翁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出,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和石岜对着干。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象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岜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象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前问。
“在岸上。”石岜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在屋里做游泳状,踩着椅子上了桌子。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