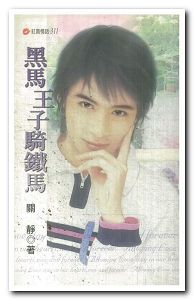金戈铁马-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孙不愧以水军起家,同时发出的圣旨,他地处最远,竟最早到。”孙丑双手抱胸,倚着庭柱。
“以长孙护的情况来看,他也只能最早到。”仲骸笑说。
五大诸侯家,位居南方的长孙护领地最小,兵也最少,倘若不及早出发,避开那些在他之前的强大诸侯,搞不好半路就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做掉了。
“明天大概是山登岳会到。”
“原东方家的养子吗?能爬到现在这个地位,此人不好对付。”
鸦峰原是东方家的领地,山登岳为前东方衡的养子,在东方衡战死后,继承他的位置。
表面上是这样,事实上,东方衡的死有另一种版本。
有人说是山登岳用计杀了东方衡,夺其之位,但原属东方家的军队对此嗤之以鼻,反驳这件事,并对山登岳忠心不移。
同样踩着别人登高位的仲骸则认为,山登岳必有其手段,因为东方衡除了养子,可还有亲生子啊!
“英雄知英雄,山登岳和主公非常类似。”孙丑吃吃笑着,如铜锣的余音,嘈杂刺耳。
“所以难对付。”对付山登岳就像和自己下棋,每一步都在预料之中,只能看谁算得远了。
“不过此番目标不在山家,如果主公担心,也可以先防范。”
“山登岳确实麻烦了些,让房术去办吧!”
孙丑了解仲骸的意思了。
如果是交由房术去办,代表意在安抚,还没有短兵相接的意思。
“我会转告房术。”孙丑顿了顿,“我猜距离最近的战慈会是最晚到的。”
“如今的五大诸侯里,战慈是最有年纪和资历的,他算是父执辈,走得慢些,是自然的。”
扬起挖苦的笑容,仲骸想也知道,好面子的战慈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到。
战氏战慈,当年也曾经叱咤战场。
如今在五大诸侯里领地第二大的战慈,较年轻时沉稳许多,前几年和厉家军一战后,已经很久没有动静。
“听说战慈的军师宰父治也会来。”
智冠天下,宰父治。
由世人给他的称号,不难知晓他是当今世上最聪明的人。当他成为战慈的军师,替他打赢第一场战争时才十八岁,那是战慈出兵攻打东方衡的一战。在军队、粮草皆备的情况下,相隔数月仍久攻不下东方衡所在的鸦峰,粮草的后应又被对方截断,原本就对山野之战不在行的战慈眼看陷入了难解的困境。
就在那时,宰父治以初生之犊之姿,告诉战慈攻陷鸦峰仅需半个月。对久攻不克的窘境已感疲惫,加上没有粮草、水土不服和兵卒思乡等等因素,战慈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告诉宰父治首先要粮,不出三日,宰父治冲破敌军,替他弄来了粮草。
战慈大悦,认为宰父治是可用之材,于是开始信任他的话。没多久,宰父治运用奇谋攻陷鸦峰,掌管鸦峰的东方衡也在那场战役中死亡。
当时东方衡的军师拥有“天下第一”的称号,宰父治犹胜他许多,于是被冠上“智冠天下”的美誉。
“你担心吗?”仲骸笑问。
“有什么好担心的?”孙丑的斗笠挑了一下。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
宰父治,终有被击垮的一天。
“很好。”仲骸不怕猛敌,只怕懦弱的部将。
“主公若只担心宰父治,那可不够,别忘了,战慈的慈,不是慈悲的慈啊!”孙丑哼了一声。
“那么就先杀战慈,再杀宰父治。”仲骸说得云淡风清,仿佛踩死两只蝼蚁般简单。
“除此之外,主公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吧!”孙丑的斗笠朝向太仪的寝殿。
提起最麻烦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仲骸抹了下脸。
“的确是要事。”
这次的御茗宴,为的也就是那件事。
如果不解决的话,才真是他的心头大患。
“我想主上很快会有动作。”孙丑的斗笠转回来。
“照孤之前说的,监视,但不要阻止。”
“我不爱监视这种工作,还是交给房术去做吧!”
仲骸白了他一眼,随后摇摇头。
“这也是孤派房术担任左史的原因。”
“知我者主公,那么我要去为明天迎接山家做准备了。”孙丑敛身告退,似乎也不怎么真心。
仲骸不在意。
自己的部将是什么性子,他大抵都了解。
孙丑是任性了些,却是带兵用计的奇才。
孙丑离开后,仲骸也没有多做停留,起身朝寝殿走去。
无声无息的走进寝殿,未上楼前,仲骸先遇上了房术和温罗,从他们手中接过太仪一日的言行纪录,他先遣退了温罗,在同房术简单说过稍早和孙丑的讨论后,才准备上楼。
“主公,今夜你可能不太适合去找主上。”房术唤住了他,暗示的说。
“难不成你以为孤每晚都过得风流快活?”仲骸挖苦自己。
“总之,今晚特别不适合就是了。”或许接下来的一阵子都不适合。房术暗忖,然后摇头离去。
仲骸照旧先走向太仪的大床。
他当然记得风曦在,但他和太仪最亲密的关系也只到吻而已,这还得在她心情好,有机可乘的时候。
从今天早上她看自己的眼神,仲骸知道,他的决定让她恨死他了。
思及此,他一阵郁闷。
故意挑极阳宫修好前举行御茗宴,就是为了把诸侯们集中在一起,方便监视。
他向来只想着对自己有利也有用的方法,却没想过他的做法可能会使某人伤心。
但是……她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
面色不善的来到太仪的大床前,仲骸没有上床,而是稍稍拉开芙蓉幕,让烛光照亮里头,看见了两张挂着相同笑痕的脸。
小的那张非常惹眼,笑得嘴巴合不拢,大的那张则内敛许多,笑容较浅。
回想起来,她从未在他面前笑过,连牵动嘴角都不曾。
走进了芙蓉幕后,仲骸靠着床头,只是注视着,神情不知不觉的缓和下来。
久久,他倾身,在她的额头印下一吻,很轻,好轻。
仲骸一走,太仪便醒了。
坐起身,定定的望着他离去的方向,直到身旁的风曦发出浅吟,她替妹妹拉上羽被,轻轻拍哄她度过梦魇后,才又躺下。
额头好烫。
她轻轻的抚着还残留余温和触感的地方,润顺的黑眸许久才合上。
他的温度,好烫。
第5章(1)
帝王,要懂得明目。
有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绝对是有道理的。
她时常告诫自己要清楚识人,因为三公常说父皇就是宠信九侍,才会酿成祸国殃民。其实父皇曾经看对人,毕竟三公是他挑选的。
寝殿内,难得无声息。
暂时送走风曦和她在几天内爱上的两只黄鹂,屏退仆人宫女,就变得很安静。
太仪跪坐在铜镜之前,素手纤纤,捻起敷粉调和水,均匀搅拌,然后敷上面容,粉饰连日来眼眶下难掩的疲惫;再调出淡淡的粉胭脂,涂抹两颊,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色。
以黛石画眉,在眉心贴花钿,绾上时下姑娘喜爱的高耸发髻,戴上镶了珠宝的闹娥,团花式的宝钿,挂上会随着步伐摇动的宝蓝耳饰,最后以嫩粉红色点唇,太仪站起身,裙摆翻飞着人雁,套上质料轻薄透明的夏裳,准备动作告一个段落。
她审视镜中不像自己的女人。
在温暖的寝殿内,穿这样并不会冷。
而且鼓动的心跳让她整个人不只温暖,还有点热了,但最热的是……太仪的手抚上额头,那个温度仿佛永远不会退去,跟了她好多天。
仲骸给过她男女之间的吻,没有感情的吻,带着抚慰的吻,她却独独对这个看不见的吻最有感觉。
事后,她偶尔会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凝视他的唇,莫名的看着,等到被它的主人发现时,再困窘得别开眼。
那个温度,她难以忘怀。
教人迷醉了心,撩乱了意,不住的放下了真感情……
怎么可以?
她斥责自己可耻的忘了仇恨,让儿女情怀困扰,但是每想一次,仲骸的身影只是更深植脑海中。
她好怕自己当初拚死记着的人,在模糊了情感的界线,会变成怎样的存在?
想忘又不能忘,不想想偏会想。
“仲骸”这两个字在她心里延伸出两条相反方向的线,一条始终系在仇恨上,而另一条……
踩着惶惶不安的步伐,太仪从未主动接近仲骸,但是今夜,她要用自己,来换取这个人的信任。
因为,她有想要保护的东西。
“有事?”坐在和太仪相同大的床上,仲骸一手搭在床头,另一手捧着书卷,正在研究。
但是太仪的出现,随即夺走了他的目光和鼻息。
生平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忘了呼吸,她光是站着,已经做到。
她的手一如平常轻轻交迭在胸腹之间,神情凛然。
别发抖。
暗暗握紧手腕偶尔还会疼的地方,太仪制止自己退缩。
“你换了衣裳。”仲骸异常缓慢的扫过她全身上下,做出结论,“穿得很美,像个舞妓。”
从未见她穿成这样。
“美就好,男人不都爱这样?”她开始走向他,一步一步,赤脚踏在木头上的轻响触动了耳膜。
仲骸双眼幽暗,瞬间了解她的来意。
“不是每个男人。”他手腕一振,书卷收得干净,反手一抛,书卷转眼间插入贴墙的木柜中。
太仪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
“所以你喜欢哪种女人?”她哑着声音问,甩不掉一身的惶惶无措。
“美人。”仲骸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她来到自己面前,大胆的跪坐在他岔开的两腿间,深吸一口气,双手颤抖的摸上他的脸,他挑起眉头,补了一句,“拥有江山的女人尤其美。”
太仪在害怕。
难道她以为用这种拙劣的方式诱惑男人能成功?
“那么朕是天下无双了。”
她描绘着他的眼眉,正要伸手探向被头发覆盖的左脸时,仲骸握住她的手,将她扑压在床上。
又是被他俯视的角度,太仪感觉到喉咙发干,两片唇瓣微微发颤。
“……朕的发髻会散掉。”
仲骸不理会她的不自在,抽出一根宝钿,抵着她的左胸口。
“所以孤留着你。天下无双,失之可惜。”他把宝钿随手扔了。
宝钿落地的清脆声音,震动她的心弦。
“你始终不相信朕。”今夜看来特别柔媚的双眸慢慢的转了方向。
“咱们俩之间,曾有信任存在?”仲骸好笑的问,也是提醒自己。
“朕不是来同你吵架的。”太仪避重就轻的闪躲。
“孤看得出来。”他的眼意有所指的停在她白皙柔腻的颈部。
她总是端庄圣洁,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穿成这样,以猎物之姿主动踏进他的地盘,怎么可能只是来吵架?
清楚她别有所图,仲骸决定陪她玩。
太仪二度试图碰触他,“朕是来求和的……”没了不安的抖动,指尖依然冰冷。
求和?
穿成这样求和,实在够诚意。
仲骸没把想到的说出来,只是说出正常人会有的反应,“你今天特别乖巧,无事献殷勤……”
太仪的一根指头堵住了他的嘴,“难道朕就不能只是想开了?”
他挑起眉头。
“想开和你呕气下去也不是办法,朕终究得靠你维持天下。”
靠他维持天下?
仲骸移开她的手,眼眸冷冽冻人。
“你搞错了,孤从来不是你的家犬。”他从不曾承认自己是诸侯。
枭雄,他倒喜欢这个世人给的称呼。
“朕没那么想。”她不自觉的转移目光。
“那就看着孤的眼睛说话。”他使力固定她的螓首,逼她看着自己,声音不可思议的温柔。
太仪畏惧的轻喘,气息很浅。
仲骸猜测着,她会如何反应?
孰料她什么也不做,仅仅开口说道:“朕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燃烧自己。”
他的神情紧敛,抽出摆在一旁的佩刀,低低的刀鸣,刺痛了太仪,她浑身紧绷,怕他给自己一刀。
锋利的刀尖挑开一颗颗衣扣,他欣赏她努力维持平静的娇容,聆听她破碎的呼吸声。
她是如此的荏弱,宛如在他手中绽放的一朵花儿……随他蹂躏。
直到夏裳被刀划得破烂,他俯首,薄唇贴着她的,低声呢喃,“孤确实喜欢女人燃烧自己。”
他正凝视着她,冰冷的眼眸不带半点感情,于是太仪了解,他早已看穿自己图谋不轨,只等她瞬间松懈落下的小辫子。
她恐惧不安,眼底铺上了一层薄雾,心一横,挺起上身,扑进他的怀中,双手不知所措的在宽阔的背上来回抚动,喉咙也干涩了,但她倒抽一口气,强逼自己发出声音,“朕愿意……为你而燃烧……”
像是解禁的咒语,仲骸不想再猜她的来意,遵循她的话,燃烧!
即使伪装冷静,他已经被她撩拨得彻底。
唇与唇的相接,总是伴随天雷勾动地火的迫切需要,仿佛将一切都卷入漩涡洪流中,直教人甘愿忘却自己。
“是你自找的。”他说,孟浪轻狂的吻落在她的眼上、眉间、鼻梁。
“朕别无选择……”她回应,热切的小手紧紧攀住在欲海里唯一的浮木,但神情恐惧。
仲骸的每一个吻,都和她四目相交,不像在探问,而是观察。
每当他的唇和手下滑,她眼里的惧意便一点点加深,等到他作势扯掉仅剩的粉橘色睡袍,她紧紧闭上双眼,不敢再看下去。
太仪屏气凝神的等着,最后却等到羽被当头盖下。
她在被中睁开眼睛,接着缓缓拉下羽被,探出头,瞧见他背对着她而坐的身影。
“为什么?”说不上完全松了口气,她竟感觉有些失落。
太仪透彻的目光,总盛载着一丝丝的愁。
那抹愁让她的眼变得深邃,令人穷极目欲参透。
“因为你希望孤能停下来。”此刻,他愿成为抹去那抹愁的男人,即使他也不懂为什么。
太仪抓着羽被,突然有种进退不得的困窘。
“无论你所求为何……成为孤的女人,孤不会亏待你。”他背对着她,轻柔又可怕的声音不复在,却教人无从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