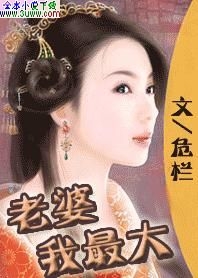老婆笨笨-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有事?”瞧这女人是怎么搞的,离他有一丈那么远,他会吃人吗?
木雪琴捉住帐口的支撑木,方才的勇气早就消失殆尽:“没!没!没事,我走错了路,对不起。”
他的凶恶让人害怕。
她当他没长脑子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她不是那种无缘无故会来求助的女人。之前,他已经领教过她的倔强和该死的胆小。
他这一凶喝,让木雪琴胆小的天性发作,她死命地摇头,眼泪扑籁籁而下。
石虎吞了一大口口水,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的眼泪。
“不许哭!”他笨拙地试图阻止她的泪,却不得其门而人。
木雪琴被他石破大惊的吼声震住潸潸的两行清泪,因为害怕,反而忘了哭泣。她似乎用尽所有的气力转身夺门而出。
该死的!他轻易搞砸了一切。
石虎想也不想,立刻追了出去。
好可怕的人,随便一吼就让她脑袋一片空白,忘了为何事而来。她不该寄希望于他的,不过施出援手帮了她一次忙,她就厚着脸皮而来,那人,他会怎么想?难堪的画面让木雪琴不敢再自行演绎下去。
“站住呀你!”不过三两步,石虎已然挡住她的去路。
她那么纤细,怕只怕他手轻轻一挥就会不见,他努力地放缓声调。
“别怕我,俺向来只是嗓门大,没恶意的。”
“请放我走吧!”过去的阴霾回到她不堪回首的记忆,木雪琴的眼中只见恐惧,听不进石虎的任何一个字眼。
石虎不情愿地退一大步:“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吧?”
他可没对谁这么低声下气过,心里虽有八百个不愿意,奇怪的是,他更不想看见她恐惧他的模样。
“嗯。”
“你找我是不是家里那两个兔崽子又惹是生非了?”
“他们不见了,我前前后后找遍他们曾去过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的影子……怎么办?”说到慌张处,才停住的泪又在眼眶中打转,“我找不到人商量,所以……所以才……”
“为什么不早说!”石虎差点又直起嗓门。
“我……”她绞着衣袖,委屈为难全在芙蓉似的脸上。
石虎见她这般模样,柔情顿生:“跟我来,有我在,孩子的事不用担心。”
由如此庞大的巨人说出这番话来,木雪琴紧绷如弓弦的心仿佛获得了安抚,原本纠结的不安飞走了,她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他。
石虎伸出蒲扇般的大手,然后似觉不妥,猛地收回在裤管上用力擦了又擦,才又伸向木雪琴:“我带你,咱们可以走得快一些。”
她蓦然红了脸蛋,好一会儿才把小手递上。
一颗用葛藤将水草和树叶紧紧捆扎成一团的藤叶球在主屋的广场飞来飞去,停不住的尖叫和笑声一波波传入胭脂的耳朵。
她无趣地踢着泥土,表情哀怨地又问了一次:“真的没有人想陪我玩沙包?”
几颗用绸布缝制的方型沙包被冷落在一旁,而广场上的厮杀声越来越激烈,惹得她心痒难当。
她决定了!
“我也要玩。”
“来呀来呀!”邯恩、邯德直朝她挥着手,“这玩意儿好玩透顶,胭脂姐姐快来!”
孩子王的袁克也但笑不语,要把他玩心颇重的小妻子拐来玩再简单不过,因为她根本经不起诱惑。
胭脂的加入刚好变成四人,两人一组,就只见四条人影满场盘旋,尘沙飞舞,虽然毫无规则可循,却玩得不亦乐乎。
然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便成一场同乐的场面。 石虎和木雪琴闻风赶来看到的就是一群面目全非的泥人。
石虎瞪大铜铃般的眼珠,摩挲下巴,忽然偏头望向木雪琴说道:“要痛宰那两个萝卜头的账先按下如何?让他们玩尽兴再说。”
木雪琴温柔地瞅着他:“你说就算。”
石虎咧嘴而笑,跃跃欲试地搓揉手掌,怂恿木雪琴:“我们也下去玩,如何?”
她有些吃惊。这么大的人居然也有颗不老的赤子心,真是难得!
“那么剧烈的活动,我……恐怕玩不来。”她没信心。而且,她这一生只知道工作持家,玩耍?太陌生的名词,那让她惶恐。
“有我在,不用担心。”石虎眉飞色舞。
又是这句足以安定她所有不安的话。木雪琴不再坚持,一并加人了众人。
“哇!”如猛虎出押的石虎一上场就踢出一记高飞球,藤球飞过半空掉入草丛里。
距离藤球最近的胭脂责无旁贷地负起捡球的责任,至于众人还有一颗备用球,毫无间断地继续比赛。
踏入草丛,胭脂兀自嘀咕:“明明就在这儿,怎么看不见哩!”
“姑娘找的可是这个?”是道地的江南腔,高昂处有转折,转折中有余韵,非常悦耳。
是个眼生的外地人,他头戴卫金龙镂腾银座冠冕,身着绎色袍子,绣的是麒麟之类的瑞兽珍禽,金马玉堂贵气俨然,只可惜,孤芳自赏和漫生的轻狂混浊了迸发的贵气。
他手上拿的正是胭脂追寻不着的藤球。
“正是。”胭脂忌讳着他身边的马匹,踯躅不敢向前。
他直视水灵灵的胭脂,粉脂味浓厚的脸忽地绽放一抹暧昧的笑容:“真是得来毫不费工夫,你一定是胭脂姑娘吧?”
一件浅红比甲,月白褶裙,羞眉圆目,好个水仙般标致的姑娘,与画中人一模一样。
胭脂警惕地盯视他。
“你是谁?”此人一身雍容华贵,她早该留心的。在山庄居住的这段日子太过惬意,使她的防卫心降低,该死!
“我特来迎娶你回去。”单枪匹马前来是他的意愿,人多只会坏事。
“哼!”胭脂嗤之以鼻。
她轻蔑的举动微出他意料之外。
“你可知我是谁?”
“不过又是一个想仰赖妻子带来丰厚财物的纨挎子弟,何奇之有!”每个口蜜腹剑的男人全是看上她一身勘舆、命相的本事,为的是能让他们一飞冲天,飞黄腾达,说穿了他不过是其中一个,以婚事做借口行目的之实。
“非也!在下知道无法轻易取信于姑娘,所以带来信凭。”他掏出一只精致的锦囊,托出囊中物,那是一个似金似乌的太极罗盘。
胭脂花窖惨淡。那是她义父随身不离的东西,她也有一只,似银似白,两者合起来恰恰是个八卦罗盘。
当初她与义父分道扬镳时,为了日后相见,以此为凭记,怎生落在这人的手中,可疑!
“你究竟是谁?”她不能逃,也不能将袁克也拖下水,除了面对,她毫无选择余地。
“姑娘终于对在下产生少许兴趣了吗?”他仍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对于这捡到的东西能发挥效果,令他有些意外的欣喜。
原来,他不过是想碰运气,孰料,还真瞎猫碰上死耗子,是老天爷助他!
“快说吧,等我夫君出现,恐怕你连说话的机会都不会有。”
“你已成亲?”他眼中连连闪过多种情绪。嗟!害他空欢喜一场,即便她有通天本能,谁愿捡一只破鞋穿。
就将她掳回交差算了。
胭脂根本懒得理会,他的情绪与她无关。
“不错!”
“既然如此,休怪在下放肆无礼了。”主意打定,他丢掉藤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封闭胭脂的气海及哑穴,然后将她挟持住,飞身纵马。虽处森森密林,马蹄却毫无滞碍,撒蹄直奔,转眼不知去向。
骏马不停蹄地往前驰骋,来到岔路,胭脂认得一边是通往小镇,一边通往京师,马儿要是朝向小镇,她或许还有逃脱机会,若是直奔京城……那可就惨了。
她的不祥预感很快应验,挟持她的人果真勒缰策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道,而且速度之快令她头晕目眩,全身骨骼几乎要散了般。
如果只是这些不适,咬牙她也会撑到底,但是扑面的灰砾使得她睁不开眼睛,更糟的是,马蹄声转为杂乱,不知有多少匹马和人的吆喝声搅和在撕裂的风中。
她这辈子肯定和有四只脚的动物与东西犯冲,否则怎么会这样。
“端王爷,放她下来,咱们好商量。”一匹饰以过多流苏的花马载着满身铜臭的主人。
被称为端王爷的尉迟端连瞧他一瞥都不屑,倏施杀手,蛇舐般的鞭在吞吐间已将对方打落马背。
胭脂看不清真伪,只听见不绝于耳的鞭答,声声在空气中飞削,哀嚎一声多过一声。
“胭脂!”清越沉厚的狮吼,宛若惊雷撼动胭脂混沌的思维。
她惊喜莫名。是袁克也!胭脂想放声大喊,只可惜哑穴受制于人,力不从心。
袁克也骑着黑驹,空手人白刃抓住尉迟端的蛇鞭,身形如猎鹰展翅扑向他,两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近身肉搏,且在急遽奔驰的马背上,真是险象环生,随时有坠马落地的危险。
两人激烈的打斗令马儿吃痛,又失去主人驾御,早已跑开大道,渐行渐远,来到荒郊野外。
袁克也的难缠颇令尉迟端不是滋味,年少气盛的他一向自以为是,在王府呼风唤雨,偏偏一人江湖便吃了瘪,锐气大挫。但也因为他傲气比天高,为了向他的父亲证明自己已然足够独当一面,方才讨来这份差事;若有差池,甭提一面称王,恐怕还会落人笑柄,永难翻身。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对裘胭脂,他志在必得。
不管她是否真有移山倒海、改天换日的通天本领,或只是道听途说,她对他的将来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所以,他决无放手之理。
也因为这点坚持,使得一心想速战速决的袁克也不耐其烦,对这公子打扮的男子他既不能痛下杀手,又要应付对方的死缠烂打,偏他全心牵挂胭脂的安危,几番煎熬,使他浓眉重锁。
铁拳喂进尉迟端的小腹,而他狡猾的端脚踢中袁克也,两人扭成一团,顺势滚落马背。
这厢打斗未休,胭脂失去尉迟端的倚靠只得抓紧马鬃,一任马儿载着她漫无目标地狂飙。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批远观缠斗的人马乘虚而入,由路一端挡驾,意欲阻止胭脂的去路。
他们手提大刀,迎面而来,直劈马的四蹄,釜底抽薪,他们的守株待兔终于要取得代价了。
刀影乍闪,飞马哀鸣,他们在乱蹄中将背上的人儿掀翻。
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僻叭响,眼看争夺的女子便要手到擒来,岂知,又有程咬金杀出,三批人马齐汇,厮杀之声震天撼动,各为其主,乱成一团。
被争夺的人儿被抛向半空,身体笔直掉下,在昏迷中滚落斜坡下的悬崖。
这样出乎意外的结局突地震住厮杀的人群——
袁克也最先反应过来,他扭身冲到悬崖边,眼眶皆裂,全身血液像霎时流个精光……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尉迟端满脸可惜神色,断然下令。
“对呀!对呀!没能把人带去,就算尸骸也好。”有人附和。
“费尽周章,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该死的笨女人。”
有好一会儿,袁克也变成木塑的人偶,他动也不动,就在众人秽语诅咒不断时,他抬起头来,缓缓地转身:“你们这些跳梁小丑令人厌恶!”枯槁如灰的凄厉化成冰珠的咆哮,不见他有任何动作,袁克也足尖挑动,一柄坠地的兵器瞬间幻为电虹,笔直插人其中一人的胸口,那人登时毙命。
痛苦穿肠入肺在他的胸口炽烈燃烧,他的忿恨熊熊烧毁他的理智,烧红他邪魁的眼,由他掌心发出的气流,招招夺命于眨眼间。
只见他身形过处,已成尸野,就连尉迟端也未能幸免。
袁克也站着,衣袂飘飘,冠已倾,发丝乱,杀人的快意为什么仍然填不满他心中的大窟窿,为什么?
他到底失去了什么?问苍天,苍天无语!
失速的撞击让裘胭脂的身子重重落下复被弹起,几经上下弹动,最后倒卧在一张织就的大网中。
网的四个角被巧妙地拴绑在不同的石柱上,仿佛是人的事先安排。
四周岑寂,飞泉倒挂直下,峭壁巨岩布满墨绿的青苔蓟草,可见这里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幸好还来得及。”清淡的释然声响骤然响起,在烟波浩瀚的水瀑中却格外清晰。
一袭布衣,一柄木杖,肩负褡裢,白面布履,系红丝绳编结的腰带,尾端是颗蜡蜒复眼图案的战国琉璃珠,为他一身的素雅缀上神秘丰采。
他用两指试试胭脂的鼻息,唤道:“无盐。”
“是,师父。”距离他数尺外一个声音粗糙、相貌极丑的女子应声而来。
“把胭脂带回去吧!”
“知道。”她力大无穷,轻易将裘胭脂的身子一扛,不即不离跟着布衣人的身后离去。
竹篱茅屋被四周茂密的树木所包围。
秋菊几穗,浅黄轻绿,芭蕉涉趣,一草一本全是自然景观。
透过户牍,可见竹丛青幽,蛱蝶数点。
胭脂苏醒过来,触鼻全是清凉爽脑的药草味。
模糊的人形逐渐清晰:“义父!”胭脂动容。
睁眼见到亲人,那错综复杂的情感非笔墨可以形容,她喉咙硬咽,千头万绪,无法言语。
被胭脂称为义父的人毫无老态,他长身玉立,询询儒雅,长发披肩,眉长入鬓,优美的单凤眼昭昭荡荡,三分落拓的潇洒,七分放意山林的逸气,犹如散仙。
他放下手中书册:“别动!无盐已经替你煎药去,稍安勿躁。”
胭脂苦笑,她挂怀的不是自己沉重的伤势:“义父,请原谅胭脂破了誓约。”
女子限制于先天本就不适合六韬纵横风水奇学的体质,当初在她苦苦哀求之下,郭问见她略带根骨慧心才传以相地之学,但也要她立下终生不语的誓言,如今——
看她挣扎着下跪,郭问并不劝阻,他反身,双手交剪:“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一切都是劫数。”
“徒儿有愧恩师。”
“不必多说,一切义父早已了然。”万般诸事不过包罗于屈指捻来间,玄机奥妙全在他方寸计算里。
“义父……”
“静心养伤吧!”他气定神闲。
“我不能,至少必须托人带个口讯给袁郎,我想让他知道我安然无恙。”
“没这个必要。”
胭脂哑口无言。她义父神机妙算,能决祸福于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