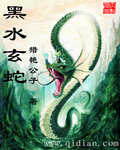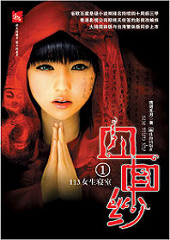黑水尸棺-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色渐晚,冯师兄开车载着我和师父,从地级市的火车站赶往我们的小县城。途中,我师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向我“授业”了。
当时冯师兄正在开着车,我师父突然没头没尾地问了句:“有义啊,你们豫咸那一脉,也是要学三尸诀的吧?”
冯师兄点点头,又苦笑道:“学啊,我刚入门的时候,每天不是背三尸诀就是道德经,到现在,一天不背一下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得劲(舒服)。”
我师父摸了摸下巴:“既然这样,那就不算是两面互通绝学了。”之后他又把视线转移到我这边来,很郑重地看着我说:“阳阳,我现在把三尸诀传给你,每一个字你都要用心去听,一个字都不许落下。集中啊,我开始念了:无忖,以之不欲。不欲,以之无心。三彭在列……”
也不知道我师父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对着我这样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唱起了古文,还要我一字不落地全都记住。我的确是很用心地在记,可往往是我师父刚说出这一句,我立刻就把前面一句给忘了,而且是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十六章 揠苗助长
念完三尸诀之后,我师父又向我解释什么是“三尸”,所谓三尸,就是道教所说的三尸神,在道教看来,人体有上中下三个丹田,在这三个丹田之中各有一位神灵,不过这三位神灵所代表的东西,却是修道中人的大忌。
上尸主华饰,中尸主滋味,下尸主***三尸神,就是人性中三种不同欲望的神化。
还说三尸诀的用意,就是为了斩三尸、稳固本心。
听过我师父对于三尸的解释之后,我就……更不记得三尸诀的内容了。
直到下车的时候,我师父也没问我到底记住了没有,我看我师父好像都没把这当回事,所以我也更加不把三尸诀放在心上了。
第二天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就看见师父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正捧着一本很旧的老书很认真地在看。
那时候,师父在我心里,依旧是那个亲切温和的老柴头,一看到他,我就打心里面高兴。
可师父抬起头来看我的时候,眼神却出乎我意料地严肃,他看了我一会,说了句更让我出乎意料的话:“把三尸诀背一遍。”
我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啊?”
师父就用很高的声音重新说了一遍:“把三尸诀背一遍。”
当时我就懵了,三尸诀?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师父在和我开玩笑,可看他的眼神,却异常地严肃,严肃中还仿若带着一股很强的威势,让我根本不敢正视他那双眼睛。
这种威势,和上次师父对付飞僵时散发出来的那股威势,简直一摸一样。
我不由地吞了口口水,很诚实地说:“我……我给忘了”
话刚说出口,我师父突然就两眼一眯,他平时看人的时候眼皮子从来没动过,可这次他一眯眼,我就感觉那目光像道闪电一样,一下震到我的心里,弄得我的小心脏都跟着哆嗦起来。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师父竟然还有这么可怕的一面,而且我师父从头到尾一句重话都没说,就是给了我两个眼神,我就被他给镇住了。
说真的,我当时就怕我师父会突然站起来,他当时如果真的站起来,我肯定瞬间就给他跪下了。
不过我师父终究没站起来,他把手里的旧书扔到我面前,一点表情不带地说:“抄,把三尸诀抄十遍。”
这本书,就是三尸诀的手抄本,我当时一看封皮上写着“三尸诀”,又目测了一下书的厚度,顿时就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十遍啊,这本书至少也有几十页吧!可我怎么记得,师父之前念三尸诀的时候,没有这么长啊?
可我又不敢违背师父,只能乖乖地抱着书本回了我的卧室,当天的作业也先放在一边,就在那老老实实地抄着三尸诀。
还好,三尸诀本身是很短的,全文加上标点也不过是五百一十六个字,那本书虽然厚,可三尸诀本文的篇幅不过占了一两页纸,剩下的,全都是对这五百多字的注解,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些和“斩三尸”有关的事例。
可即便三尸诀只有五百多字,十遍抄下来,也有五千多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要把这五千字写完,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而且那天晚上,师父不知道从哪弄来了我的作业单,我抄完三尸诀之后,又在师父的注视下做完了作业,完了师父还帮我检查作业,帮我预习明天的功课。
等折腾完,已经到了凌晨两三点了。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学习是件特别累的事,以前我不爱学习只是因为贪玩,可从这天开始,我对于学习,却可以说得上是厌恶。
可我越是厌恶,师父对我的要求的越发严格,而我的学习成绩也像长了翅膀一样开始突飞猛进。现在想想,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学业还是次要的,师父之所以关心我的学习,应该是受我妈委托的缘故。他最在乎的东西,归根结底,还是守正一脉的传承。
那段时间,为了传承,我师父真的把我折腾坏了,甚至都有点拔苗助长的嫌疑。
三尸诀只是一个开始,就在我很不流利地将三尸诀通篇背诵之后,师父又开始让我背道德经,三尸诀虽然只有五百字,可我看不懂古文啊,死记硬背,花了一个星期,才勉勉强强记住通篇。
可道德经呢?足足五千字不说,而且和三尸诀一样也是古文,生僻字无数!那段时间背道德经背得,我感觉我都快谢顶了。
每次我一背错,我师父就会对我说一个我至今很烦的字:“抄!”五遍十遍地抄。
那时候我比较粗心,经常抄错字,每次出现这种错误,师父不打也不骂,而是拿出二十根大头针撒在院子里,让我在二十分钟之内把所有大头针找齐,如果找不全,师父就会再扔二十根出去。
什么时候我把二十根大头钉都找到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真的,那段时间,真的被我师父折腾坏了,可也就是找大头针的那段经历,不但让我变得更加专注,连同耐性、观察力都一并被练了出来,我甚至能通过师父扔大头钉的姿势,判断出这些大头针散落的大体区域。
那时候,师父传授给我的看似只是两篇简单的古文,可事实上,诸如此类的锻炼,却是在教给我日后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危险之中,真正能救命的只有四种东西:胆量、经验、判断和运气,我师父此时教给我的,就是判断。
道德经背熟之后,师父接着又开始传授定禅、思存,说是学会了这两样东西,才能开始修习真正的“术”。
定禅,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它是缘于佛家,可与大部分流入守正一脉的东西一样,守正的禅意和佛家的禅意也是有区别,具体的很难去描绘,我只剩说,守正一脉的定禅,是和三尸诀、思存联系很密切,三尸诀是要稳固本心,定禅,则是在三尸诀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进入到思存境界。
而思存,说起来就有点玄乎了。
所谓思存,就是指思存九天、天人合一,我师父说,思存之后,就是念力。念力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似有似无,可没了它,所有的“术”也都无法施展出来。
在传授我定禅之后的第二个月,我师父又先后传我走罡、天罡锁、八步神行。
注意,我说的是:传授我定禅之后,而不是我学会了定禅之后,在我学走罡的时候,我还无法通过定禅来让自己达到思存境界,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思存境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可走罡的时候,每一步踏出去,都要思存九天!
我师父这样教我,瞎子都能看出来,这是急功近利、本末倒置!
除了这种填鸭式的授业之外,我师父还成了我的专属厨师,每天我吃什么,吃多少,每顿饭搭配什么肉、什么菜、什么水果,喝牛奶还是喝羊奶,我师父都会给我严格地把关。每天早上一起床,我还要喝一碗师父特意熬制的浓汤。
当然,那时候我们家是没钱给我提供这样的伙食的,我饮食上的所有开支,都是来源于我师父。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师父之前说他不缺钱,的确没有骗我们。
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的个头也开始不受控制般得疯长。
用我爸的话说,就我这种长法,以后的个头说不定能超过我师父。
我的个子高了,身子也壮了,这让我有了一种从前没有过的自信,可我师父的授业方式,也让我越来越吃不消了。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练习天罡锁的时候,我师父就站在旁边,一边看着我练,一边很无奈在旁边吼我:“你看你那手,怎么这么没力气啊,要*****抓进去!”
天罡锁,是一门脱胎于鹰爪翻子的功夫……其实也不能说是功夫吧,它也是一种术。这么说吧,如果不在思存状态下使用的话,它就是一门威力还算可以的擒拿功夫。可如果带上思存,听我师父说,这门功夫也能用来封住尸气。
守正一脉的很多术法都是这样,又是功夫又是道术,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的,可胜在实用。
天罡锁这门功夫练习的方式很特别,刚开始是扎马步、先把下盘练稳,在我下盘练得稍微有点起色之后,就开始练抓麻绳、抓石锁,有时候也抓木人桩,每次我练习抓功的时候,我师父都会在旁边嚷嚷着说我没力气,好像只有我用手指把胳膊粗细的麻绳掐断了、把木人桩捏碎了,他才会满意似的。
后来我师父大概是实在看不过眼了,就让我退到一边看着,他则走到那根粗壮的麻绳前,为我演练起来,一边为我演练,一边还要耐心地为我讲解着。
我在旁边听着,脑子却暗自开起了小差,眼神也跟着变得有些涣散了。
这时候,师父突然朝我吼了一声:“想什么呢!”
我先是被吓了抖了下肩,之后又回过神来,趁着我师父还没对我露出那种威慑力很强的眼神,说了句:“师父,我爸说,你太着急了。”
第二十七章 罗有方
我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的,我师父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太着急?什么事太着急了?”
我鼓了鼓勇气,又说:“我爸说,你教我的这种方式,是揠苗助长,我爸还说了,强扭的瓜不甜。”
师父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你爸说?这是你爸说的吗?熊孩子,嘴上没长毛,先学会说瞎话了。”说着说着,老柴头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抄道德经去,十遍!”
在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和师父顶嘴的,可那段时间的强压式授业,真的让我有些扛不住了,我当时很倔强地和师父对视着,声音很小地说:“揠苗助长。”
我声音虽然小,可院子里也没有其他人,这声音传到我师父耳朵里,是非常清晰的。
我师父当场就瞪起了眼:“你懂什么!你现在不好好地练,来年我带你回寄魂庄种棺的时候,你就,就……”
师父瞪着我,过了很久,终究还是没把话说完,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就回了屋子。
从这件事之后,师父对我的要求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格起来,我的压力也变得更大了。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两年,八岁到十岁这段时间里,我师父几乎想将守正一脉的所有秘诀和术法全都教授给我。可因为学得东西太多,大多数我只能做到一知半解,有些甚至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全是靠死记硬背才勉强记住。
直到97年二月前后,师父说有事要去趟北京,临走前,嘱咐我每天背诵三尸诀、道德经,晨练也不能落下。
师父这一走,就是整整半年,在这期间,我爸妈代替师父监督我每日的功课,学校的功课和师父布置的功课都要监督,所以即便是在这半年中,我也没有比平时轻松多少。
我师父走后的第五个月,正赶上香港回归,也就是在那年七月份的月底,我们家来了一个回祖籍投资的港商。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就看见老家属院的巷子口听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我这两年跟着师父和冯师兄,也算是见过点世面了,可这辆车,却是我平生第一见的豪车。
其实我到现在对车这东西也没什么了解,可那辆车,一看就知道是豪车,因为它是加长的,车头又宽又大,在车头的顶端还立着一个小天使的金色雕像。
而且那辆车的车牌也和别的车不一样,别的车牌大多都是蓝底白字,而这辆车的车牌,却是黑底白字的,这样的车牌和黑亮的车身搭配在一起,看起来特别的和谐。
当时我就想,难道是我师父回来了,不光回来了,还弄回来这么一辆特别的轿车。可再想想又不对,以我师父那种深入浅出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弄一辆这么惹眼的车回来。
带着满心的疑问,我回到了家,刚一进院子,就听见屋子里有人在说话。
说话的人不是我爸,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腔很浓重的南方口音:“我己是来看一看嘛,哎呀,大嘎都系盆友,左大哥就不要这么劳师动众啦。”
之前忘了提,我豫咸一脉的赵师伯说话的时候也带着南方口音,不过若论普通话,却比屋里的人标准太多了。我赵师伯虽然带点口音,可绝对不会把只是说成己是,把大家说成大嘎,更不至于把朋友说成盆友。
不过屋里的人口音虽然很重,可他的声音里,却有一种让人很难拒绝的热忱。
进屋以后,我就看见我爸正坐在沙发上,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有说有笑的。
起初在外面的时候,我还以为说话的人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可这时才发现,他是个青年。他长得非常白净,五官中,不管是眉眼还是鼻口,都很精致。这样的五官配上介于国字脸和鹅蛋脸之间的脸型,顿时彰显出一种罕见的帅气,而在这份帅气中,还有一分男性特有的雄性魅力。
他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