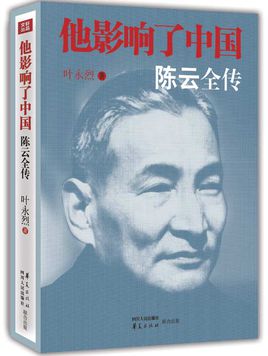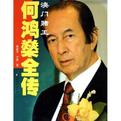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3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 ※ ※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 ※ ※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 ※ ※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