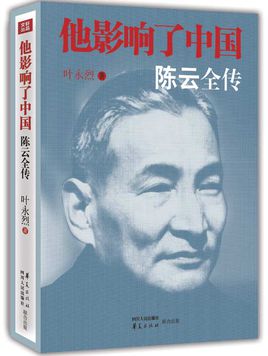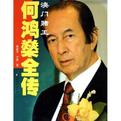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3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找个黄匣子盛好,亲手隔窗递与李莲英。
“烦你劝劝皇上,人死不能复生,又道是‘没有千年不散的筵席’,请皇上千万别伤心。”
李莲英心知瑾妃言不由衷,但仍旧答一声:“是!”
“还有,”瑾妃又说:“听说老佛爷准皇上亲自临视珍贵妃的遗容,这,实在可以不必。你务必给拦一拦,皇上是不看的好。”说到最后一句,瑾妃的声音哽咽了。
“奴才知道。”李莲英心想,这倒是很好的一个劝阻的借口。
于是,让随行的小太监捧着黄匣,李莲英又回到了养心殿。西暖阁中一灯荧然,窗纸上映出晃荡的影子,想是皇帝等得有些着急了。
李莲英微咳一声,窗纸上的影子立刻静止了,接着门帘打起,他从小太监手里接过黄匣,疾趋数步,走到门口说道:
“奴才给万岁爷复命。”
“好!拿进来。”
李莲英将匣子放在桌上,然后退后两步请个安说:“是瑾妃宫里取来的。瑾妃还有话,让奴才回奏。”
“什么话?”
李莲英将瑾妃所说的话,前面一段,是照样学了一遍,后面一段就全改过了:“瑾妃又说”半夜里寒气很重,那儿是个穿堂,前后灌风,万一招了寒,圣躬违和,那就让珍贵妃在地下都会不安。万岁爷如果体恤珍贵妃,就千万别出屋子了。‘“
皇帝沉吟了好一会,方始很吃力地说:“既是这么说,我就不去。
“是!”李莲英如释重负,问一声:“万岁爷可还有别的吩咐?”
“你跟皇太后回奏,就说我没有去看珍贵妃的遗容。”
“是!”
“这,”皇帝指着黄匣说:“这东西,别跟皇太后提起。”
“奴才知道。”
“好!你回去吧!”
李莲英便即跪安退出,顺便向屋里的太监使个眼色,示意他们尽皆退出。
于是皇帝亲手打开盒盖,一阵浓郁的香味,直扑到鼻,顿觉魂消骨荡,刹那间,眼、耳、口、鼻、意,无不都属于珍贵妃了。
那曾闻惯了的香味,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一下子都勾了起来。他记得这瓶香水是张荫桓出使回来,连同几样珍奇新巧的玩物,一起托一个太监,仿佛就是开照相馆的戴太监,转到景仁宫去的。
由于皇帝喜爱那种香味,从此珍贵妃就只用这种香水,算起来已四五年不曾闻见过了。
解开罗巾,触目更不辨悲喜,金盒中还留着两粒豆蔻,不由得就想起杜牧的诗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正是珍贵妃初入宫的光景。
算一算快十二年了,但感觉中犹如昨日。那年——光绪十五年,珍贵妃才十四岁,虽开了脸,梳了头,仍是一副娇憨之态。皇帝想起她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珠,不时乱转,而一接触到皇帝的视线,立即眼观鼻,鼻观心,强自矜持忍笑的神情,便不由得神往了。
那四五年的日子,回想起来真如成了仙一样。烦恼不是没有,外则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纵有一片改革的雄心壮志,却是什么事都办不动;内则总是有人在太后面前进谗,小不如意,便受呵责,而皇后又不断呕气,真是到了望影而避的地步。可是,只要一到景仁宫,或者任何能与珍贵妃单独相处的所在,往往满怀懊恼,自然而然地一扫而空。也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会体认到做人的乐趣。
如今呢?皇帝从回忆中醒过来,只觉得其寒彻骨,一颗心凉透了!一年半以前,虽在幽禁之中,她仍旧维系着他的希望,想象着有一天得蒙慈恩,赦免了她,得以仍旧在一起。谁知胭脂井深,蓬莱路远,香魂不返,也带走了他的生趣!
人亡物在,摩挲着他当年亲手携赠珍贵妃的这个豆蔻盒子,心里在想,这不就是杨玉环的“钿盒”吗?将古比今,想想真不能甘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在珍贵妃并无这样非死不可的理由,“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诚然悲惨,但自己竟连相救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不能如玄宗与玉环的诀别,这岂能甘心。
而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玄宗与玉环毕竟有十来年称心如意的日子,而自己与珍妃呢?转念到此,皇帝不但觉得不甘心,且有愧对所爱而永难弥补的哀痛。
“说什么‘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唉!”皇帝叹口气,将豆蔻盒子合了起来,不忍再想下去了。
可是涌到心头的珍贵妃的各种形像,迫使他不能不想,究竟她此刻在何处呢?是象杨玉环那样,在“楼阁玲珑五云起”的海上仙山之中?
也许世间真有所谓“临邛道士鸿都客”,当此“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苦思之时,翩然出现,为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觅得芳踪,又如汉武帝的方士齐少翁那样,能招魂相见。
果然有这样不可思议之事,自己该和她说些什么呢?皇帝痴痴地在想,除了相拥痛哭以外,所能说的,怕只有这一句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九一
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则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殁,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唯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未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 ※※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 ※※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