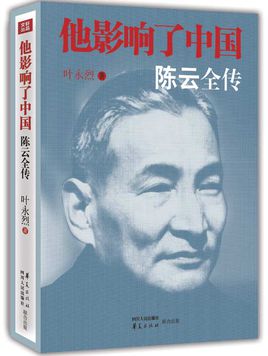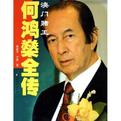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2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 ※※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 ※※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这样说法,而军机领班礼王世铎则在许庚身的敦促之下,特意上折奏报,醇王手足发颤,深为可虑。
奏折先到皇帝那里,看完以后,心中凄苦,却不敢流泪,直等到了毓庆宫,看见翁同龢终于忍不住了。“醇亲王病重!”他哽咽着说,“恐怕靠不住了。”说完,泪下如雨,而喉间无声。
翁同龢亦陪着掉眼泪,可是他无法安慰皇帝,此时唯一能安慰皇帝的,只有一道命皇帝亲临醇王府视疾的懿旨。翁同龢曾经想联合御前大臣,请这样一道懿旨下来,看看沉默的多,附和的少,他亦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