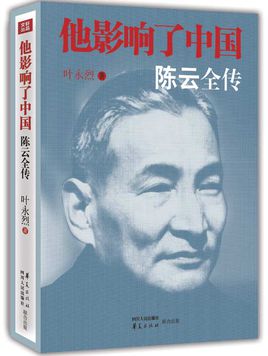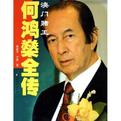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2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不必费事,买点酱羊肉、‘盒子菜’这些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顶要紧的一样……。”
“‘独爱红椒一味辛。’”她抢着念了一句他的词。文廷式笑了,“我想你不会忘记的。”他说,“也不要忘了给我带瓶酒。”
“算了吧!”她柔声答说,“你的笔下快,出场得早,第一场完了,回家来喝。”
“不!”文廷式固执地,“初十上半天入闱,要到晚上子初才发题。十一那一整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弄完,要到十二才能出闱。空等这一夜太无聊了,不以酒排遣怎么行?”
“那好!我替你备一瓶酒。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文章缴了卷才能喝。”
“是了!我答应你。”
于是一宿无话。第二天上午,他料理完了笔墨纸砚,以及闱中准带的书籍,便出门访友。等傍晚回家,龚夫人已经预备好了带入场的食物,另外做了几样很精致的湖南菜,预祝他春风得意。等酒醉饭饱,又催着他早早上床,养精蓄锐,好去夺那一名“会元”。
文廷式一觉醒来,不过午夜,起来喝了一杯茶,遥望隔墙,犹有光影,见得她还不曾入梦。她在做些什么?是灯下独坐,还是倚枕读诗?他很想去看一看,但披上长衣走到角门边,却又将要叩门的一只手缩了回来,只为明天要入闱了,应该收拾绮念,整顿文思。
重新上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破晓,方觉双眼涩重,渐有睡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惊而醒,霍地坐起身来,但见曙色透窗纱,墙外已有辘辘车声了。
文廷式定定神细想,梦境历历在目,一惊而醒是因为自己的“首艺”。第一场的试卷,被贴上“蓝榜”,因为卷子上写的不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是一首词,他清清楚楚记得是一阕《菩萨蛮》:
“兰膏欲烬冰壶裂,搴帷瞥见玲珑雪;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徐将环珮整,相并瓶花影;敛黛镜光寒,钗头玉凤单。”
“奇梦!”他轻轻念着:“‘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不自觉地浮起去年冬至前后雪夜相处的回忆。
这份回忆为他带来了无可言喻的烦乱的心境。旖旎芳馨之外,更多的是悔恨恐惧,他想起俗语所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不知道在“含娇故起辞”到“徐将环珮整”之间那一段不曾写出来的经过,是不是伤了阴骘?
为了这个梦,心头不断作恶。三场试罢,四月十二到琉璃厂看红录,从早到晚,还只看到一百八十名,不但他榜上无名,连南张北刘——张謇与刘若曾亦音信杳然。
回得家去,自然郁郁不欢。龚夫人苦于无言相慰,又怕他这一夜等“捷报”等不到,是件极受罪的事,便殷勤劝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却还期望着他一觉醒来,成了新科进士。
醒来依旧是举人。上年北闱解元刘若曾,第二张謇,竟以名落孙山,这使得龚夫人好过些,也有了劝他的话,“主司无眼,不是文章不好。”她说,“大器晚成,来科必中!”
“但愿如此!”文廷式苦笑着,心中在打算离京之计了。
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算得好的,而且榜后也不免有许多应酬,要贺新科进士,也要接受新科进士的慰问。一个月之间,荣枯大不相同,文廷式不是很豁达的人,心情自然不好,应酬得烦了,只躲在长善那里避嚣。
“告诉你一件奇事。”志锐有一天从翰林院回来,告诉他说:“醇王要去巡阅海军……。”
“那不算奇。新近不是还赏了杏黄轿了吗?”
“你听我说完。醇王巡阅海军不奇,奇的是李莲英跟着一起去。”
“那,那不是唐朝监军之祸,复见于今日了吗?”
“是啊!”志锐痛告而不安地,“可忧之至。”
“这非迎头一击不可!此例一开,其害有不胜言者。不过须有一枝健笔,宛转立论,如陈驵庵、张香涛诤谏‘庚辰午门案’,庶几天意可回。”
“我也是这么想。这通奏疏一定要诚足以令人感动、理足以令人折服,不但利害要说得透彻,而且进言要有分寸,不然一无用处,反而愈激愈坏。”志锐仰屋兴叹:“现在难得其人了!”
“只要细心去找,亦不见得没有。”
“芸阁,”志锐正色问道,“你能不能拟个稿子?我找人出面呈递。”
文廷式报以苦笑:“我现在这种境况,心乱如麻,笔重于鼎,何能为力?”
“好吧!”志锐无可奈何地,“等我来想办法。”
志锐的办法,不用文字用口舌,他决定鼓动他的姐夫“谟贝子”劝醇王力争。主意一定,立刻写了一封信,专人送给奕谟。
奕谟倒也很重视其事,接到信便套车直驱适园,只见王府门庭如市,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军机处、神机营,以及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都是为了醇王出海巡视舰队这一件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举动。有的是有公事要接头;有的是办差来回复车马准备的情形;有的是随行人员请示校阅海军的地点日程;有的是因为醇王这一次离京,起码有个把月之久,许多待办的紧要公事,要预作安排,以致奕谟等了有半个时辰,方始见到醇王。
这是他们二十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上次见面之时,还没有派醇王巡阅海军的上谕,因而奕谟首先问道:“这一次派七哥出海,大家都认为应有此举,只不明白,怎么会有李莲英随行?”
为何有李莲英随行,醇王亦不大明白,照他的想法,也跟派太监悄悄到南苑去看神机营出操那样,无非慈禧太后怕臣下瞒骗,特地遣亲信作耳目。但太监出京,到底过于招摇,因而当时便表示拒绝。拒绝得有一个借口,他的理由是,李莲英三品顶戴,职分过大,似乎不便。那知慈禧太后答得很爽利:“让他带六品的顶子好了。”这一下,别无推托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现在听奕谟问到,他先不作答,看看他手中的信说:“怎么?外头有什么话?”
“七哥看!这是志伯愚的信。”
信写得很切实,说本朝尽惩前明之失,不准太监出京,更是一项极圣明的家法。同治年间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两宫太后与穆宗的宸断,天下臣民,无不钦敬感佩。现在李莲英奉旨随醇王出海巡阅海军,自然不敢妄作非为,但此例一开,随时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察军务,督抚非醇王之比,必不能抑制此辈。这样,远则唐朝宦官监军之祸,近则前明“镇守太监”之非,都将重现于今日。最后是劝奕谟:“曷不勿以口舌争之,当可挽回体制不少。”
话是说得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无奈到此地步,生米将成熟饭,万难挽回。但如老实相告,说慈禧太后如何如何交代,奕谟或许会责难:当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同时也一定会极力劝说,不折不挠,务必设法请上头收回成命,岂不是平添许多麻烦。
这样想着,便不肯道破真相,索性自己承认过错,“是我不好,我自己奏请派遣的。”醇王说道:“我不能出尔反尔。此刻无法争了,以后我想法子把他们压下去就是了。”
这一回答,大出奕谟的意料,骇然问道:“七哥,你怎么想起来的?奏请派太监随行!这不是长他们的气焰吗?”
“我亦是一番苦心。”醇王勉强找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在深宫养尊处优的人,也看看外头的情形,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将士之苦。”
话也还说得通,不过醇王老实,言不由衷的神色却不善掩饰,所以奕谟微微冷笑:“七哥倒真是用心良苦。不过在我看,自以为有了坚甲利兵,或许反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但愿如七哥所言。”奕谟又问:“七哥是不是要把御赐的杏黄轿带了去?”
“那怎么可以?”醇王懔然作色,显得相当紧张郑重,“逾分之赐,恩出格外,为臣下者,岂可僭越?”
对于延煦在东陵争礼的深意,奕谟亦约略听人谈过,很疑心慈禧太后特赏醇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就象雍正对年羹尧的各种“异数”一样,是有意相试,看他可有不臣之心?所以此刻见到醇王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知道他已深深领悟到了持盈保泰的道理,自然感到安慰。
不过,他也许只是如条几上所摆的那具“欹器”,记取孔子的教训:“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未见得想到,慈禧太后对他已有猜忌之心。这一层,最好隐隐约约点他一句。这样想着,正好抬头发现醇王亲笔所写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便即指着那张字,故意相问:“何谓‘天样大事’?”
“这……,”醇王为他问住了,“无非形容其大而已!”
“‘事大如天醉亦休’,是少陵的诗。不过,我倒觉得,出诸七哥之口,别有深意,要让子孙明白才好。”
醇王听他的话,有些发愣,但很快地脸色一变,是更深一层的戒慎恐惧。显然的,他已经领悟到了,慈禧太后始终存着戒心,有一天他会以皇帝本生父的身分,成为无名有实的“太上皇。”
“我错了!”他颓丧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急流勇退?”
“存着这个心就可以了。”奕谟反觉不忍,安慰他说,“‘上头’到底也是知道好歹的。”
等奕谟告辞,醇王一个人发了好半天的怔,正在心神不定,坐立不宁之时,有人来报:“荣大人来了。”
荣禄现在又成了适园的常客了。他是上年年底,由醇王提携,以报效神机营枪枝的功劳,开复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仍旧成为一品大员,但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请求暂不补缺,经常来往适园,作为醇王的智囊。这时听得他到,心头一宽,立即延见。
“仲华,”他悄悄问道:“言路上有什么动静?”
荣禄知道,这是指的李莲英随行一事,便从容答道:“此刻还没有动静。不过十目所视,等他回来,也许会有人说话。”
“这件事,实在出于无奈。”醇王叹口气说,“现在越想越担心。”
“王爷既然已经想到,宜乎未雨绸缪,该透个信给他。”
“怎么说法?”
“他,”荣禄忽又改口,“其实,我看他也知道,他究竟不比小安子那样飞扬浮躁。”
这是说,李莲英应该以安德海为前车之鉴,醇王深以为然,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透露给本人?便又向荣禄问计。
“我看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再提醒他一次,总没有错儿。你看,这话该怎么说才合适?”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也不必专跟他说。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通饬随行人员,不得骚扰需索,如敢不遵,指名参办。我想,他总也有数了。倘或不然,王爷不妨拿府里的人作个杀鸡骇猴的榜样。”
“对,对!这个法子好。你就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
说着,醇王亲自为他揭开砚台的盖子。荣禄赶紧亲自检点纸笔,站在书桌旁边,为醇王拟了一道手谕,虽是一派官样文章,语气却很严峻。醇王看完,画个花押,随即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
“还有件事,我只能跟你核计。昨儿立豫甫告诉我说,上头已有口风露出来:说这多少年真也累了,想早早归政。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随便回答,荣禄想了好半天答道:“王爷只当没有这回事最好。”
“要不要得便先表示一下,请上头再训政几年?”
“不必!”荣禄大摇其头,“那一来倒显得王爷对这件大事很关切似地。”
“说得是!”醇王深深点头。
“上头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无从悬揣。反正,果然有这个意思,自然先交代王爷,那时再回奏也还不迟。”
“是的。”醇王想了一下又说,“最好先布置几个人在那里,到时候合词陈奏,务必请上头收回成命,比较妥当。”
“不用布置。到时候自然有人会照王爷的意思办。”醇王点点头,想到另外一件事,“仲华,”他问,“你看,上头要叫皮硝李跟着我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未净身入宫以前,做的是硝皮的行当,所以有这么个“皮硝李”的外号。荣禄心想,醇王这话可是明知故问?
如果他真无所知,话就只能说一半了。
说一半就是只说一件。李莲英此行的任务,据荣禄所知,一共有二,其中之一是,慈禧太后想要知道,醇王的声望到底如何?这自是“雄主猜忌”之心,说给忠厚老实的醇王听,会吓坏了他,不宜多嘴。
于是他只说另外一半:“北洋练兵,水师也好,海军也好,花的钱可真不少了。上次不有人说,济远舰不值那么些钱?后来李少荃奏复,不如外间的传言,事情算是压下来了。不过上头到底有些疑心,派皮硝李去,我想,就有个明查暗访的意思在内。”
“说得有理,倒要留点神。”
于是他第二天便传下话去:这一次校阅,务必大张军威,意思是要让李莲英震眩于军容之盛,好回去向慈禧太后侈谈其事,觉得大把银子花得很值。
六六
出海那天,正值满月,半夜一点钟上船,子潮已过,海面异常平静,李鸿章称颂:“全是托王爷的福!”
坐的是最大的一艘定远舰,舰上最大的一间舱房,也就是定远舰管带,到德国去过的“总兵衔补用副将刘步蟾”的专舱,重新布置,改为醇王的卧室。其次一间,不是李鸿章所用,而是特为留给李莲英。专门办这趟差的天津海关道周馥,亲自领着李莲英进舱,原以为一定会有几句好话可听,那知不然!
“周大人,”穿着一身灰布行装的李莲英问道:“这间舱也很大,跟王爷的竟差不多了。是怎么回事?莫非船上的舱房,都是这么讲究?”
“那里?”周馥答道:“兵舰上的规矩,最好的一间留给一舰之长的管带,就是王爷用的那一间,再下来就数‘管驾’所用的一间,特为留给李总管。”
“李中堂呢?”
“李中堂是主人,用的一间,要比这里小些。”
“这不合适。”李莲英大摇其头,“李中堂虽做主人,到底封侯拜相,不比寻常。朝廷体制有关,我怎么能漫过他老人家去。周大人,盛情心领,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