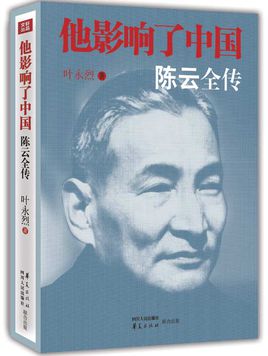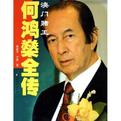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2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炫)畏(书)惧(网)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