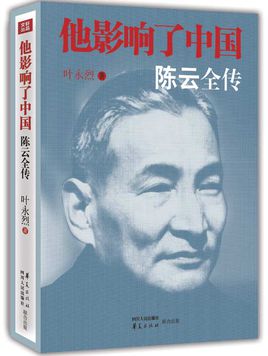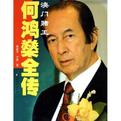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1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爷呢?”
“大爷头疼,不能陪你。”郝顺陪笑说道,“二爷有话,吩咐我也是一样。”
兆润沉吟不答,尽自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因为这天他的所欲不小,说话便须格外慎重。
“二爷,”郝顺劝道,“大爷遭了这档子窝囊事,真正是叫‘哑巴梦见亲娘,说不出的苦。’二爷总是体谅他才好。”
“哼,”兆润愤愤地摔着酒杯,“就为了大爷窝囊,才有这样窝囊的事。不用他出头,我替他去挺,该杀该剐都有我,他还怕什么?一个劲拦着,我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那也无非大爷胆小。如果他能看着二爷闯出大祸来不管,那叫什么同胞手足?”
“同胞手足?”兆润撇撇嘴,“他哪里当我同胞手足?外面说的话,可难听了。”
“外面怎么说?”郝顺很谨慎地问。
“怎么说,你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告诉你听吧!”兆润眼望着郝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说他卖老婆!”
“啊!”郝顺作出讶异万分的神色,“这是打哪儿说起?”
“你不信是不是?”兆润有意诈他一诈,“说的人有凭有据,大奶奶带回来三千两一张银票,大栅栏恒泰钱庄的票子。”
兆润知道是一千两,故意加了两千,是指望着套出郝顺一句话来:“没有那么多。”这就好紧追着往下问了。谁知郝顺心机深沉,不上他的当,只摇着头说:“没影儿的事!”
“没影儿的事?照这么说,大奶奶就白白让人霸占了?”兆润接着又问,“她忽然回家,可又为了什么?”
“这,”郝顺陪笑道,“我们当下人的,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话NFEA3 !好些事你不知道,非得跟大爷自己谈不可。好了,反正我的主意拿定了,门风要紧,我不能看着不管。”
说着,站起身来要走,郝顺自然不能放他走,好说歹说地将他留了下来,自己进上房去跟兆奎讨主意。
“我哪有什么主意?”兆奎哭丧着脸说,“我一见他,脑袋就跟笆斗那么大。”
郝顺是他的心腹,无事不参与,也无话不可说,但不论如何,办事须奉主人之名以行,所以这时便先替兆奎拿宗旨。
“这件事,大爷得抱定宗旨,无论如何松不得口,一则名声不好听,再则,二爷的口气不小。不过也得给他一个指望,一等放了缺,上任的时节,给他撂下几百银子倒可以。大爷,你说是不?”
“对!你就想法子,跟他这么去说。”
这话实在也很难说。郝顺在想,“二爷”大概只知银票其一,还不知有放缺其二,一说反倒泄底。有这么大的好处,他更是不依不饶了。
想了又想,只有这样措词:“二爷,你先请沉住气。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完,不过做事总要稳得住,对头太不好惹,一步错不得。反正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工夫,一定能让二爷好好儿消气。”
照郝顺的想法,有NFDA7 贝勒那么硬的靠山,说放个副都统,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有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见了上谕,一切便都好办。因而这样许下兆润。
兆润不知其中有此曲折,只是一向信任郝顺,既然他说能让自己“好好儿消气”,顾念以后还少不得有托他的事,便卖个交情给他。
“好吧,冲你,我就等个十天半个月。”
半个月过去,音信毫无。奎大奶奶倒是把话带到了,载NFDA7 却办不通。这件事他只有去求宝NFDA1 ,为了志在必成,他特意说是“已经答应了人家了!”
“我的大爷?你真是少不更事!驻防的副都统,又是广州,能说换就换吗?”宝NFDA1 大摇其头,“兆奎是出了名的无用。这话,我怎么跟你阿玛去说?”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37节豪门家丑(2 )
“我不管!”载NFDA7 撒赖似的说,“你去想办法。”
“办法倒有,我把你的事儿,和盘托出,你肯挨顿揍,兆奎的副都统就当上了。”
这叫什么办法?载NFDA7 自然不肯,宝NFDA1 被磨不过,答应试一试,但哪一天能成功却不知道。
“只好等吧!”奎大奶奶听说了经过,也只好这样万般无奈地表示。
又等了半个月,这天奎大奶奶正打算带着小云上前门外去听戏,只见院子里闪进来一个人,高声喊道:“大嫂!”接着便请了个双安。
“啊!”奎大奶奶倒有些忸怩了,“二弟,是你!”
“是的。”兆润神色自若地说,“特地来给大嫂请安。”
“不敢当,不敢当!”奎大奶奶不能不以礼相待,“请屋里坐。小云,拿茶,拿烟。”
于是兆润从从容容地进入堂屋,坐下来先打量四周,古董字画,窗帘椅披,色色精致,便赞一声:“真是好地方!”
奎大奶奶矜持地微笑着,心里在打主意,如何早早将这位不速之客送走。
兆润的话却还未完,接着又说了:“怪不得大嫂不想回家了。”
这句话不中听,奎大奶奶只能装作没听见,心里却更觉得他是早走早好,因而开门见山地问:“二弟,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只是老没有见大嫂,怪惦念的,特为来看看。”
“多谢你惦着。”她又追一句,“二弟要是有事,请说吧!自己人不用客气。”
最后这句话是假以词色的表示,兆润就不必惺惺作态了,苦着脸说:“还不就是那一个字吗?”
“哪个字?”
“穷!”兆润又说,“弟媳妇又病了,小三出疹子,小四掉在门前沟里,差点儿淹死。唉,倒霉事儿不打一处来。”
“噢!”奎大奶奶慢吞吞地说,“我手里也不富裕。不过,二弟老远的来,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说着,便将手里的手巾包解了开来,里面有两张银票,一张十两,一张五两,本想拿五两的给他,不道兆润先就说在前面。
“多谢大嫂,不用全给,只给我十两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在说:倒真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全给!然而那张五两头却拿不出手了。
由此开端,隔不了三五天,兆润便得来一趟,他也真肯破工夫守伺,总是等载NFDA7 不在家的时候来。护卫因为未奉主人之命,也没有听奎大奶奶说什么,'炫Qisuu。com书'不便拦他,所以他每次都能找着“大嫂”,伸出手来,也总有着落,不过钱数越来越少,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渐渐地,奎大奶奶不能忍耐了,终于有一天发作,“你倒是有完没有完!我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她厉声质问。
“就是大嫂说的,自己人嘛!”兆润涎着脸说,“大嫂,你哪儿不花个几两银子?就算行好吧!”
“好了!这是最后一回!”奎大奶奶将一张二两的银票摔在地上。
兆润还是捡了走,而且过不了三天还是上门。这一次护卫不放他进去了。
“找谁?”
“咦!”兆润装出诧异的神色,“怎么,不认识我了?老马!”
“谁认识你?NFEA5 ,NFEA5 ,你趁早请。”
兆润一时面子上下不来,既不能低声下气跟他们说好话,便只有硬往里闯。这一下自然大起冲突,好几个人围了上来拦截,其中一个出手快,叉住兆润的脖子往外一送,只见他踉踉跄跄往后倒退,却仍立脚不住,仰面躺了下来。
如果他肯忍气吞声,起身一走,自然无事,但以兆润的性情,不肯吃这个亏,存着撒赖的打算,希望惊动奎大奶奶,好乞怜讹诈,便站起来跳脚嚷道:“你们仗势欺人。我跟你们拼了!”
这一声喊,惹恼了载NFDA7 的那些护卫。在王府当差的,最忌“仗势欺人”这句话,所以这一下是犯了众怒。领头的是个六品蓝翎侍卫,名叫札哈什,曾在善扑营当差多年,擅长教门的弹腿和查拳,这时出腿一弹,将个正在揎拳掳臂的兆润,扫出一丈开外,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这一次兆润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了,“打死人NFEA3 !救命啊!”极声高喊。
“这小子作死!”札哈什咬着牙说,“把他弄进去。”
于是上来三四个人,掩住他的嘴,将他拖了进去,在马号里拿他狠揍了一顿。揍完了问他:“服不服?”
怎么能服?自然不服,但不服只在心里,口头上可再不敢逞强了,“服了!服了!”他说,“你们放我回去吧!”
“当然放你。谁还留你住下?”札哈什说,“可有一件,你以后还来不来?”
“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好,我谅你也不敢再来了。你走吧!”
开了马号门,将兆润撵了出来。他只觉浑身骨节,无一处不酸痛,于是一瘸二拐地先去找个相熟的伤科王大夫。
“二爷,你这伤怎么来的?是吃了行家的亏,皮肉不破,内伤很重,可得小心!”
“死不了!”兆润狞笑着,“你先替我治伤,再替我开伤单。这场官司打定了。”
王大夫替他贴了好几张膏药,又开了内服的方子,然后为他开伤单,依照兆润的意思,当然说得格外重些。
回到家却不肯休息,买了“盒子菜”,烙了饼,把他一帮好朋友请了来,不说跟奎大奶奶索诈,只说无端受那班护卫的欺侮。向大家问计,如何报仇雪恨?
“NFDA7 贝勒还不算不讲理的人,应该跟他说一说,他总有句话。”有人这样献议。
“他能有什么话?还不是护着他那班狗腿子!我非得要那班狗腿子吃点苦头,不能解恨。”兆润问道:“咱们满洲的那班都老爷,也该替我说说话吧?”
“来头太大。谁敢碰?”
“润二哥,”兆润的一个拜把兄弟说,“你如果真想出气,得找一个人,准管用。”
“谁呀?”
“五爷。”这是指NFDA3 王。
“对!”兆润拍桌起身,顿时便有扬眉吐气的样子,“这就找对了。”
如果是想在载NFDA7 身上出一口气,只有请NFDA3 王来出头。当然,能不能直接跟他说得上话,或者他会不会一时懒得管此闲事,都还成疑问。但要顾虑的,却还不在此。
“老二,”兆润的一个远房堂兄叫兆启的说,“你别一个劲地顾前不顾后,第一,得罪了六爷,犯不上,再说句老实话,你也得罪不起。第二,这件事到底是家丑,不宜外扬。”
前半段话,兆润倒还听得进去,听得后半段,兆润便又动了肝火,“照你这么说,我就一忍了事?”他又发他大哥的牢骚,“我们那位奎大爷,才知道什么叫家丑!如果我要替他出头理论,他能挺起腰来,做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儿,我又何至于吃那么大的亏?”
在旁人看,家丑不家丑的话,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家丑能够瞒得住,才谈得到不宜外扬,如今“NFDA7 贝勒霸占了兆奎的老婆”这句话,到处都能听得到,已经外扬了,却默尔以息,反倒更令人诽薄。要顾虑的是不宜得罪恭王,诚如兆启所说的,兆润也得罪不起。
“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六爷挺讲理的,也并不护短,NFDA7 贝勒的事,他是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不管。照我看,最好先跟他申诉,他如果护短不问,就是他的理亏。那时候再请五爷出头,他也就不能记你的恨了!”
说这话的,是兆润的一个好朋友,在内务府当差,名叫玉广,为人深沉,言不轻发,一发则必为大家所推服。此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兆润本人在内,无不认为妥当之至。
于是就烦玉广动笔,写了一张禀启,从奎大奶奶失踪谈起,一直叙到护卫围殴。第二天一早,请兆启到恭王府投递。
恭王府的门上,一看吓一跳,尽管NFDA7 大爷在外荒唐胡搞,还没有谁敢来告状。这张禀启当然不敢贸然往里投递,直接送到载NFDA7 那里。
载NFDA7 很懊恼,但却不愿责备札哈什。想跟奎大奶奶商量,却又因为替兆奎谋取副都统的缺,不曾成功,难以启齿,一时无计可施,便把这张禀启压了下来。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38节惇王行法(1 )
一压压了半个月。而兆润天天在家守着,以为恭王必会派人来跟他接头,或是抚慰,或是询问,谁知石沉大海,看来真的是护短而渺视,心里越觉愤恨。于是又去找玉广,另写了一张禀启,半夜里就等在东斜街NFDA3 亲王府,等到NFDA3王在五更天坐轿上朝,拦在轿前跪下,将禀启递了上去。
奎大奶奶的事,NFDA3 王早有所闻,只是抓不着证据,无法追问。这时看了兆润的禀启,勃然大怒,在朝中不便跟恭王谈,下了朝,直接来到大翔凤胡同鉴园坐等。
等恭王回府,一见NFDA3 王坐在那里生气,不免诧异,但亦不便先问,只是亲切地招呼着。老弟兄窗前茗坐闲话,看上去倒是悠闲得很。
也不过随意闲谈了几句,NFDA3 王还未及道明来意,听差来报,总理衙门的章京来谒见,恭王一问,是送来一通曾纪泽的奏折。往来指示及奏复,一直都用电报,往往语焉不详,这道奏折是由水路递到。由于奉有谕旨,凡是对俄交涉的折件,交NFDA3 王、恭王、醇王及翁同NFDA2 、潘祖荫公同阅看,所以总理衙门的章京接到奏折,先送来请恭王过目。
为了尊礼兄长,恭王拿着折子先不拆封,回进来向NFDA3 王说:“曾NFDD5刚来的折子,大概这些日子交涉的详情,都写在上头了。五哥,”他将折子递了过去:“你先看吧!”
这些地方,NFDA3 王颇有自知之明,照他看:“办洋务找老六,谈军务找老七”,他自己以亲贵之长,则约束宗亲,维持纪纲,责无旁贷,所以不接折子。
“不必!你看好了。”
于是恭王拆封,厚甸甸的折子,共有十四页之多,定神细看了一下,然后念给NFDA3 王听:“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着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
“原来是这么召回的!”NFDA3 王插了句嘴,他是指俄国驻华公使布策被召回国一事,“曾NFDD5 刚到底比崇地山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