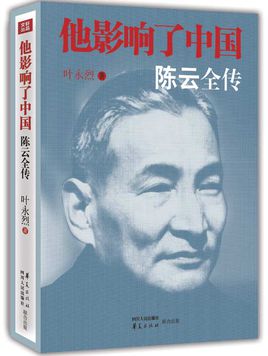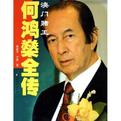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16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海工程,尽力节省,两位皇太后的意思,你们已经听见了,军机写旨来看。”皇帝又转脸问两宫太后:“两位皇太后可是还有话要问?”
“就是这两句话。”慈禧太后说:“时势艰难,总要靠上下一心,尽力维持。千万不要存什么芥蒂。”
“臣等不敢。”恭王又说:“臣也决无此意。”
由于谈到了三海工程,皇帝命御前大臣及翁同龢先行退出,只留下军机大臣承旨。始终未曾说话的慈安太后,认为应该再降一道谕旨,申明务从简约,尤其要力戒浮冒,同时问起,前一天谕旨中的“该管大臣”,是不是指内务府大臣而言?
“内务府大臣,当然也是该管。”恭王答道,“不过奉宸苑兼管大臣,应该是专管。”
“那么,你们看三海工程,到底应该派谁管呢?”慈安太后率直地说了她的顾虑,“可别再闹得跟修圆明园一样,教外头说闲话。”
这是极中就要的顾虑,内务府的惯技就是小题大做,如果名义上由圆明园换为三海,实际上仍旧搞出各样各目,要花几百万银子,那就大失群臣力争的本意了,所以恭王这样建议:“要说工程,自然以内务府主办,工部襄助为宜。但为力戒浮冒,核实工费起见,似宜简派王大臣一员,负责监督。”
“这话说得不错。”慈禧太后说道:“五爷的差使不多,将来就让他来管吧。”
“是!”
话说到这里,出现了沉默,慈禧太后倒是有许多话想问,但这一来便似越权干政,所以不便多说。只命李鸿藻传谕翁同龢,说他讲书切实明白,务必格外用心,以期有益圣学,随即便结束了这一次例外的召见。
这天是八月初一,每月朔望,照例由皇帝侍奉两宫太后,临幸漱芳斋传膳听戏。皇帝闹得一天星斗,结果风清月白,什么事也没有,自己想想也灰心,所以在漱芳斋一直面无笑容。慈安太后了解他的心意,特为叫他坐在身边,一面听戏,一面劝了他好些话。皇帝的满怀抑郁委屈,总算在慈母的温煦中,溶化了一大半。
等散了戏回寝宫,只见载澂闪出来请了个安,笑嘻嘻地说:“臣销假。给皇上请安。”
一见他的面,皇帝心里便生怨恨,沉着脸说:“载澂,你跟我来。”
“是!”
到了殿里,皇帝的脾气发作:“你给我跪下!我问你,你在你阿玛面前,说了我什么?”
载澂敢于销假来见皇帝,便是有准备的,跪下来哭丧着脸说:“臣为皇上,挨了好一顿打。”
这话使得皇帝大为诧异,声音便缓和了,“怎么啦?”他问。
“请皇上瞧!”说着,载澂把袖子往上一捋,露出半条,一条膀子伸了出去。
“起来,我看!”
一看之下,皇帝也觉恻然,载澂膀子上尽是一条条的血痕。“这是臣的父亲拿皮鞭子抽的,非逼着臣说不可,‘不说活活打死’,臣忍着疼不肯说。臣的父亲气生得大了,大家都说臣不孝,不该惹臣的父亲生这么大气。臣万般无奈,不能不说。臣该死,罪有应得。”说着他又跪了下来,“臣请皇上治臣的罪。”
皇帝听罢,半晌无语,然后叹口气说:“唉!起来。”
皇帝跟载澂的感情,与众不同,到此地步,怨也不是,恨也不是,而且还舍不得他离开左右,连“御前行走”的差使,都不能撤,真教无可奈何。在载澂,自己也知道闯了大祸,虽然使一条“苦肉计”搪塞了过去,歉仄之意,却还未释,所以格外地曲意顺从。就这两下一凑,真如弟兄吵了架又愧悔,抱头痛哭了一场那样,感情反倒更密了。
在外廷,一场迅雷骤雨的大风暴,已经雨过天青,停园工的诏令,如溽暑中的一服清凉散,就是内务府以及跟内务府有关的营造商,亦有如释重负之感。碰上钉子的内务府大臣,自感无趣,但转眼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必有恩典,革职的处分,必可开复。而修理三海,不论如何力戒浮冒,诸事节省,仍有油水可捞。这样想着,便依旧精神抖擞了。
唯一可以说是倒霉的,怕是只有李光昭一个人。皇帝对停园工一事,想了又想,最气不忿的就是此人,所以在八月十二特地又下一道手谕:“迅速严讯,即行奏结,勿再迁延!”
谕旨到达直隶总督衙门,正也就是审问属实,快将结案的时候,于是加紧办理,在中秋后一天出奏,叙明经过事实以后,李鸿章这样评断:
“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诳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其捏报木价,尚属轻罪,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拟两罪,皆系斩监候,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所称前在军营报捐知府,是否属实?尚不可知。但罪已至死,应无庸议。查该犯素行无赖,并无家资,实藉报效为名,肆其欺罔之计,本无存木,而妄称数十年购留;本无银钱,而骗惑洋商到津付价;本止定价五万余元,而浮报银至三十万两之多,且犹虑不足以耸人听闻,捏为‘奉旨采办’及‘园工监督’名目,是以洋商竟有称其‘李钦使’者。足见招摇谬妄,并非一端。迨回津后,恶迹渐露,复面求美领事代瞒木价,致法领事照请关道,将其拘留,诚如圣谕:”无耻之极‘,尤堪痛恨。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便想,本年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停止勾决,斩监候就得等到明年秋后处决,让李光昭多活一年,犹觉不甘,所以批了个“着即正法”。
修圆明园一案,随着李光昭的人头落地而结束。眼前的大事,就只有两件了,一件是对日交涉。日本的专使大久保利通,八月初四在总理衙门,与恭王、文祥等人当面展开交涉,首先就辩论“番地”的经界。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想“证明”台湾的“生番”,不归中国管辖,这都是毛昶熙一句话惹出来的祸,恭王和文祥当然不能同意,就这样反复辩论,一拖拖了半个月。
第二件大事,就是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的庆典,而这一件大事,又与第一件大事有关。恭王等人都知道,停止园工,慈禧太后内心不免觖望,为了让她的生日过得痛快些,应该将对日交涉,早日办结,只是这层意思,决不能透露,否则为对手窥破虚实,就可以作为要挟的把柄了。
在大久保利通,亦急于想了结交涉。因为看到中国在这一重纠纷上,已用出“狮子搏免”的力量,一方面派沈葆桢领兵入台,大修战备,不惜武力周旋;一方面李鸿章在天津与美、法公使,接触频繁,争取外交上的助力。原本是自己理屈的事,迁延日久,骑虎难下,真的打了起来,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不如见风使帆,早日收篷,多少有便宜可占。
因此,大久保利通,表面强硬,暗中却托出英国公使威妥玛来调停,就在这时候,沈葆桢上了一个奏折,说是“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利。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恭王与文祥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当威妥玛转述日方的条件,要求赔偿兵费三百万元时,文祥答得极其干脆:
“一个钱不给!”
调停虽然破裂,恭王却密奏皇帝,说交涉一定可以成功。听得这话,皇帝乐得将此事置之度外,巡视三海,巡幸南苑,驻跸行围,看神机营的操,看御前王大臣及乾清门侍卫较射,到九月初才回宫。
※ ※※
就在回宫的那一天,小李伺候皇帝沐浴时,发现两臂肩背等处,有许多斑点,其色淡红,艳如蔷薇,不觉失声轻呼:
“咦!”
“怎么了?”皇帝叱问着。
这是不用瞒,不敢瞒,也瞒不住的。“万岁爷身上,”小李答道,“等奴才取镜子来请万岁爷自己瞧。”
小李取来一面大镜子,跪着往上一举,皇帝才发觉自己身上的异样,“这什么玩意?”他颇为着慌,“快传李德立!”
传了太医李德立来,解衣诊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问皇帝说:“皇上身上痒不痒?”
“一点儿不痒。”
不痒就坏了,而李德立口里的话,却正好相反,“不痒就不要紧。”他说,“臣给皇上配上一服清火败毒的药,吃着看。”
“怎么叫吃着看?”
“能让红斑消掉,就没事了。”
皇帝对这话颇为不满,“消不掉呢?”他厉声问说。
李德立因为常给皇帝看病,知道他的脾气,赶紧跪下来说:“臣一定让红斑消掉。皇上请放心!这服药吃下去,臣明儿个另外再带人来给皇上请脉。”
于是李德立开了一张方子,不过轻描淡写的金银花之类,从表面看仿佛比疥癣之疾还要轻微,而暗中却大为紧张,真如怀着鬼胎一般,想说不敢,不说不可。
想想还是不敢说,本来不与自己相干,一说反成是非,且等着看情形,有了把握,再斟酌轻重,相机处理。
这样过了几天,忽又传召。这次是在养心殿西暖阁谒见,皇帝意态闲豫,正逗着一群小狮子狗玩,见了李德立便说:“你的药很灵,我身上的红斑全消了,你看看,还要服什么调理的药不要?”
接着解衣磅礴,让李德立细细检视,果然红斑消失,皮肤既光又滑。李德立便替皇帝贺喜,说是:“皇上体子好。什么调理药也不用服。”
等他叩辞出宫,跟着便是太监来传旨,赏小卷宁绸两匹,貂帽沿一个。李德立谢了恩,开发了赏钱,同僚纷纷前来道贺,他也含笑应酬,敷衍了一阵,独独将一个看外科很有名的御医,名叫张本仁的,留了下来。
“我跟你琢磨一宗皮肤病。”李德立说:“肩上、背上、膀子上,大大小小的红斑,有圆的,有腰子形的,也不痒,那是什么玩意?”
“这很难说。”张本仁问:“鼓不鼓?”
“不鼓。”李德立做了个抚摸的手势,“我摸了,是平的。”
“连不连在一块儿?”
“不连。一个是一个。”
“那不好!”张本仁大摇其头,“是‘杨梅’!”
虽在意中,李德立的一颗心依然猛地下沉,镇静着又问:“这杨梅疹,多少时候才能消掉?”
“没有准儿,慢则几个月,快则几天。”
“坏了!”李德立颓然倒在椅子上,半晌作声不得。
“怎么回事?”张本仁凑过去,悄然问道:“是澂贝勒不是?”
“不是!是他倒又不要紧了。”
“那么……?”张本仁异常吃力地说:“莫非……?”
两个半句,可以想见他猜想的是谁?李德立很缓慢地点了点头。
“有这回事?”张本仁大摇其头,“敢情是你看错了吧?”
“我没有看错。除非你说得不对。”李德立又现悔色,“我错了!当时我该举荐你去看就好了。”
“得!”张本仁一躬到地,“李大爷,咱们话可说在前头,你要举荐我,可得给我担待。”
李德立不解,翻着眼问:“怎么个担待?”
“这是个治不好的病!实话直说,还得掉脑袋,你不给担待怎么行?”
“我知道,你说,要我怎么给你担待?”
“仍旧是你主治,我帮着你看,该怎么治,我出主意,你拿主意。”
李德立不响,过了好{炫&书&网}久才问:“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又会发作?”
“这可不一定,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也许一辈子不发。”
“谢天谢地,但愿就此消了下去,一辈子别发吧!”
“就算一辈子不发,将来生的皇子,也会有胎毒。”
张本仁黯然叹息,“我看大清朝的气数快到了。”
李德立没有那样深远的忧虑,只在考虑眼前,这个自古所无的“帝王之疾”,要不要禀报,如果要,应该跟谁去说?
一个人坐困愁城,怎么得了?李德立想来想去,必须找一个人商议,这个人自然应该是庄守和。太医院院使悬缺,庄守和是右院判,李德立是左院判,平日他大权独揽,很少理庄守和,兹事体大,不能不让他知道,也不能不让他出个主意,将来好分担责任。
“只好装糊涂。”庄守和要言不烦地说,“这件事是天大的忌讳,病家要讳疾,医家也要讳疾。”
“这话固然不错,就怕将来闹出来,上头会责备,何不早说?”
“早说也无用,是个医不好的毛病。”庄守和又说,“而且也决计不会闹出来!万乘之尊的天子,怎么能生这种病?”
李德立通前彻后地考虑了利害关系,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装糊涂。”
于是皇帝的病,就此被隐没下来。他本人亦不觉得有何不适,每日照常办事,召见军机第一件事就是垂询对日交涉。交涉几乎破裂,大久保利通提出了“限期五日答复”的最后通牒,恭王不理他,便又自动延长三日。三日一到,正值重阳,大久保又到总理衙门,与恭王作第五次会谈,要求赔偿兵费二百万两银子,恭王坚持不谈“兵费”二字。大久保利通便改口要求“被难人”的抚恤。至此地步,便只是谈钱数了。
到了九月十四,谈判决裂,大久保利通告诉英国公使馆,说是决定两天以后离京。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再一次出面调停,百般恫吓,将病骨支离的文祥,累得头昏眼花,答应给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天津教案,赔偿各国被难领事、教士的数目,不过算法不同,十万两银子是抚恤,四十万两银子作为收买日军自番社撤退后所遗下的房屋道路。并且在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三条《中日北京台事专约》。大久保利通此行的最大收获,不在五十万两银子,而是“专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惟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被害的是从明朝洪武五年以来,就为中国藩属的琉球渔民,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国属民”,而恭王、文祥和李鸿章还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