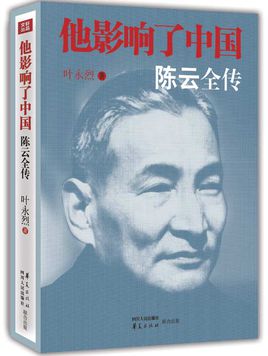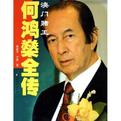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ȫ��-��16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乺��֮�ѣ���ɸż������������������д�ʱ����������֮�⡣
�������Ĵ��ܶ����ĵ����ۡ���˵��������꣬��ּ�ɰ�骰��İ���������ھ�ʡ����ʮվ�Ĵ��¯��һ�������֡��п���������������ˮ·��Զ���м���ų�ɽ���룬����ն���������˵������˺ü���Ĺ�����ܰ��˳�ɽ����һ���������������ǰ�ζ������������ɽ֮�У���Ϊ���������յ��գ����Ŀ����ɲľ�ľ����Ϊ������������ɸ�Ա���ָ����˾۾�֮������ͬ�Է�����������Ѱ�٣����к��ʵ�ľ�ϣ���Ҫ�����·���Ȼ��м���������������Ѷɣ��㲻�ò����Է����������ܹ��˳�ɽȥ����Ҫ����ˮ·���ζ��������ϣ���ΪɽϪС�ӣ���鮲�ͨ����ľ�������Ư�ŵ��ζ���ӣ������������¡�
���������ӣ��ʵ����ҿ����Ҳ������Բ���ĵط���ֻ�����˸����������롱�������ˣ��õ���Ϣ���������ţ���������һͨ���ۣ�������ж����ǧ���ص���Բ����ʲô���ޣ��������Ĵ��ܶ����ģ����ܴ���̫����ߵغ�֮������������˵ʲôҲҪ�߳ϱ�Ч�����Ա��ż����ϣ������֪������ôһ�����õ�˵�ʡ���ν������չ�����ڡ�ԭ�Ǿ���̽�Ļ���������ް�������������˽�������ľ�ϣ�����������ϧ������������롱����һ��չ�ޡ���ңң���ڣ�����ָ���ˡ�
�ʵ۵������ᣬ���²������������Ƶ��ˣ��������磬�������������൱ðʧ�������Ѻ�Ϊ��֮�ƣ�Ȼ�������ﻢ���£����Ǽ����ù��ټ�������˾�٣����ľۻᣬ�ܳ�Ӧ��֮����
�����鵽��ͷ���ˣ�˵���ϲ��㣬ֻ��Ӳ���ţ�����˾���ල�Ĺ����б��Ź�עһ�����뷨��ϣ��������������ճ�֮�ʣ��ܰѴ���̫��ᶯ���������ִ�ƣ����������������š���˵����ǰ���飬��ͷ�ǻ������Ҳ���������أ��������Ǹ����ϸ�Ǯ�������˶�������������������Ұ�ú����֣���
���ڱȽ����أ�ҡ��ͷ˵��������Ǵ�飬��������ү�����������Ƕ����֣���ʡ����˵ʲôҲ�������ӡ������������������������һ������һ���ߵ����ƣ���ָ�����ʹ����������ڵ��ſ����֣����DZ�Ū�ò����ճ�����
������ү�����������ѳ����ֶ�������ɣ��������⻰��˵��Զ�ˣ���ּ���£���ͷ��������̫���ѵ�˵������һ������ܣ�����������Լ�����ʹ������ùģ�����ָ���˼����𣿡�
����Ҳ�ÿ��ط���Ϲ����ʲô�ã���������˵���������ȵÿ������������Ǽ������Ӹ�ľֲ�ǿ���ס�ģ�����Ϊ���������ȴ�
��Ҫ��ס�ͺ����ˡ������ƽӿ�˵�������㶫�������Ƕ��ǿ���ס�ģ�������Ҳ�ǿ���ס�ģ�����������ôһ��ˮ���������ˣ���ͷ��û�ˣ��������ص����룬�������������ѣ�������������˵��
����ͷ��˵��ͷ�ġ������ӳ��˸����⣬���ҿ��ò��ŰٷϾ�٣���������һ������Ū���������������ֳɵĶ�����������ͱȽ�����˵���ˡ���
������飬�������ˣ����ϡ������ȼ���ȫ��������������һ���ǻʵ����ڸ���˫��ի��һ���ǹ����д����ݵİ��ӹ���
���Ǹ��������ô���ˣ��ҿ��е㿿��ס�ɣ�������������˵��
�����ܿ���ס������ס����������ôһ���������dz�ȥ���ޣ����Ǻõġ���
���⻰˵��ͷ�ˣ�����ĬȻ�����ǵ���Ͱѹ��̷�Χ�����°�����һ�¡��������³���˫��ի�Ͱ��ӹ������¾������౨�ʵۣ���С��ͣ���������ʮ���գ������ӹ�����Ȼ������һ����ڡ�
�������죬�ʵ����ݳ��������ˡ���ǰ���ߡ���һ�����������Ĺ�Ա��С����ˣ���Բ����������Ӳ���һ������˫��ի������֮ǰ���ټ����ڡ����ӡ����ơ���������ѯ��
Ѳ�ӵ�ʱ���ǻʵ۵Ļ��������װ��Ҫ�������磬�����¥��Ҫ�ض���¶����ӵ�����Ա����֣�����µر�ʾ����ּ�����������ټ�ʱ���;��ǹ��ڻʵ���ǰ�����ĸ��˵Ļ��ˡ�
˵��˵ȥ����Ǯ�����������������ʮ������Ӳװ�ޣ��û���ľ����̴��һ�ó�Ϊһ�ۣ��ܼ���ʮ���ۣ��������ء����족����֮������������֮һ��С�����ھ����̳а졣�����ľֲ�������Ĵ��ܶ����ģ���һ��ڻݶ�ʵ�����ġ�չ�����ڡ��ij�ŵ���⣬�����ʡ�����;����ɣ���ʾ���Ǹ��δ����ã�ʵΪ�Ұ����С�������Ҫ���������ӵĹ��Ͽ�Ӻ����䣿
�ʵ�Խ��Խ�ķ������ֻ�������Ը������������Ű죬��һ�ʿ��ӿ��Զ��ã�ֻҪ����������˵ͨ�ˣ���һ��������
�⻰����δ˵�������������˵��ͨ���ֺα��Ϸ���ԣ���������һ˾�ٻس��ԺϽ����ټ����飬����������ÿ�����ľ��ѣ�һ��һ����ϸ�������ܹ����õĶ����˳�����Ҳ������ʮ�������ӣ���֮���������£�ֻ�о��������ڴ���̫���ڲ��ʽ��ȵġ����һ�Ҵ������档
������������
���˻ʵ����٣�����˵�����Ѿ��ؾ�����Ҫ����ȥ�ң������Լ��������˵���������һ��������ľ�����ӣ�˵��������Ѿ�����۶����������ǧ�ߵ���ľ������Ȼ��һ������Ϣ�������ǧ����ľ����ʵ����Ҫ�ģ�����úܶ࣬��������һ��������������ˣ��ܱ�Ч�������ӣ����Զ�������֮�ڣ���������������Ȱ����䣬���Թdz��˷ܡ�
�������ڣ�������;���õĺ��ѣ�����δ̸���⣬��Ҫ������һرܣ�ͬʱ��ɫ������һ����֪���鲻�
�����ү���������һ�仰���ǣ������������Ǹ�����ĵ��ˣ���
�����������������������ڴ��һ�������ŵ��ʵ�������ô�أ���������˵����
������Ļ���ʮ�䵱��ֻ����һ�䣬��ֱ�ͽл��������������ɥ����˵�������ү���ҿ��治���ˣ��������ӡ���ҩ��������������һ��������ͷ����
��һ˵�����ܲ��Ծ�������������ˣ�����ǿ�����ţ�����˵˵�������������ôһ���ˣ���
������ǹ㶫�ͼ��ˣ��ľӺ��ڶ��꣬������ʶ��Щ���ˣ���ר��թƭΪҵ��ƭ����һ����֮���������������뺣�ڣ����ֳ��֡�
����ǰ����Ѹ���������һ�����⣬����ӳ���֮����һƬ�ĵأ����˸����ˣ��������˵������в��ʣ��������������棬Ҫ���˻�ԭ������ƭ����Ǯ��һ�뻹ծ��һ��ӻ������ѹ������Ǹ�����������˵������һ���̣�ʹ����Ƭ���ݻĵأ�����ˮ��������Ҳ��������ʵ��ȥ�������ֻҪ�ܰѵ�����������Ƭ�ĵ�ȷ�ɳ�Ϊ����֮�ء�
����װģ���������˼��������������������̱����˳�����棬������ǵ��ص���ʿ�������尡�
�����ܵط�ί�У��������������档��Ƭ��ˮ�ĵأ�����ˮ��й֮��������û��ʲô�˳�����ҵ���������������أ��������һ���̣���ˮ����ʱ��û�г�·�����·��ij��֣�����������ϰ��գ������亦��
����Ѻγ��������ⷬ��������Ϊ�˶�������������������������ǻ����Ҫ���̲��ɣ���ʱ�������䣬��������Ȱ�ܣ��Ų������ͷ��Ѫ����������ѵ���Щ��������Ƶ��������尵�Ȼ�����˽⣬ֻ���ô��˲���������Ψ�п�֮�ڹ٣������ɺ����ص����������ٴӺ��Ƶµ��浽Ѳ������˾����˾�������ܡ�����������ͻ�ʾ���Ͻ����̣��Ա�������
�����Ǵ�������й����ģ�������Ѷ�����˵������͢�ǽ������ģ��ط�����һ�����ܵط�ʿ�𡣲�Ҫ�����ҵ�����ȥ�棬�ǰѹ�˾��ʤ�˲��ɡ���
����Ѿʹ˽衰���ء�Ϊ�������������˵���ƣ�Ҳ������ε��˾�ʦ������ȥ������һ��������һ���������������������£�������ǰ���˺����Թ�ת��һ�룬�������ѵ���Щ���£�������������˵��
�����������ʹ������˵ģ�֪�������Ѿ��ϵ�ù���˹����Ÿһغ��ڡ���������˵������·����ӡ��һ������������ּ����Բ��ľֲ����������������ӣ�Ҫ�ڴ��Ϲҳ������ҿ�������Ҫ���£��ѵ���С�����ö����������Դ�����һ˵�����������ס������˵Ļ�����࣬��Ҳ������˼��죬Ҳ�����ó�ʲô����������
�¶�������뽲���ֲ�������������˹�һʱ�ĸ�ãȻ���������仰ȴ�Ǻ�������������������������ѵ�����δʧ��������ǰ����˵��������������ǰ����գ����뵽����ʲô��˼����Ҫ����һ�ʡ�
��������һ������ľֲ����ַ�����������ܳ�ɽ��������δ�����ڣ��Ⱦͽ����ؾ���ԭ������Ѹ���˵�����絽�������ľ��������ۣ���һ�����̶��������ǧ����ľ�������Ҵ����������ӣ�����Ѹ��˶���˵Ҫ���´�Ǯ�����صظϻؾ��������ү������ʵ�ij�����һ��ʮ���ѿ�����ı���˵����Ϊ�˲�ȱ����Ҳ�˲����ˣ����ܴն��پ��������ľ����Ϊ�ҵı�Ч����ʱҪ���ү����������û���ҵĿ��ġ������ҽ������ƭ�ˣ�ҲҪ����ү������ԩ����
��һ���⻰��ֻ�������������㰲ο��˵����������������������࣬��ͷ��֪����С�Ľ���ȥ��ɣ���
�����������������Ļ�������������ֹ��������������˸����ӣ�Լ���˼��������ѣ��������ص���Դ¥���ã�Ԥ�����Ұ�æ����һ����������ȥ��Чľֲ���ò��ϱ���ʽ��ʵȱ��
Լ������������ӣ�һ����������������죬����������׳�������ſڿ���̨վ�ţ�˫Ŀ���ƣ�ֻ��ע�������ʳ�͡����ŝ����յ��ˣ�ֱ����¥���и�׳�������ų��룬������̤��¥�ݣ�����Խ������
һ���أ�¥���ź�����������Ҳ��⣬�����������ϵõģ�ȴ��֪��һ������������˭������������������ƺ�������ͷ��С��
��������������λ�������Ŀ��ͣ�һŤ�����������ã����̾Ͱ���һ�ɣ��������ڵر��˹�ȥ��
���㶮��ز��������������õ�����һ�ƣ��������ʡ�
���õ�͵���˿͵Ķ������Ƿ�����Ĵ�ɣ�������֪�������Ͻ���Ц�����ص�Ǹ������ү�����������ҿ��øղŽ�������λ��ү���졭������
��ʲô���������ģ���������˵������������������Ҫ������ˣ��������ա�����������
���ô�Ӧ�ŵ����������ʣ��ø�СֽƬд�����룬�ص�¥�ϣ�ֻ���ǿ��ͻ��ڵ��ţ�����̡����ҡ����գ��Ա���ʡ��ǿ���ҡҡͷ�������������õ�����˵�û������ա����Ǿ���ķ��ף��ǵ�����������ס���ˣ�������ָ��֣����ǿ������Ǽҷ��ݣ���м����֮�⡣�������õ��൱�ż�����Ϊ����Ϊ�˸ղŵ��ж�ʧ�죬�����˹�͡�
����һ��Ҫ�����ӣ�һ�������յĵ�����ֻ�������������Ż���������������������漴���ں��棬һ��һ�ӣ�������¥����Դ¥��ǰͣ��һ�����仪���ĺ����Ȼ����������˳������������Կ�ԯ��˿���ﴦ��������ȥ���ǵ�·������Ŀ��
����ʱ����Щ׳�����ﳤ��ȥ�����������¥������ֻ�Dz��ɣ������ǻ���������˭�������Լ������¶������ˡ�
������̫����Щ���侭�˵��飬�����л�һ��δ�������õ����ϲ����������������ģ��������ꡣ����������ͣ����õ��ƿ�����������û����͵�����Ŵյ������ߣ��ü��͵�����˵�������Ҹ�����˵�˰ɣ����Ͽ�ǧ����ڶ����
��λʮ�˾��꣬���ü������Сү���ǵ�����ϡ���������һ������������˵�����и������¹��ӳԷ��ģ���������ô˵����Ҳ�����Ǽ�����ţ���Ϊ�뵽�������Ѽ��˿����Σ����������˿�ԯ�������ֵ���������Ǹ����������������ôһ�����ӣ�
��һ�㶼���١�����������˵�����Ǻ����µ�����ү˵�ġ�����ү������ͷ�Ǽ������������ڹ��ﵱ���֪�������϶��ٻأ������ˣ���
�������˿����������쳣���棬�������Dz��٣������������������˽�У����Ǽ�����˼����¡�
�������Ʋ��ţ����õı��־�֤��������¥���Ƕ����ţ������ܸ�֪������
������¥����ʲô���ţ��������ʵ�������ȥ�������������ջ�����һ�㶼��֪������
���Ǿֲ����ˣ������õ�˵��������Ժ������ү������ү�����Ƕ������˻��ϣ����ϻ�������ү����һ�ΰ���¥���������ƻ�������һ�����궼���˹��ˡ���
��˵���棬Ҳ���̳��벻�����ţ�Ȼ�����������ʣ���Ϊ������Ŀ��ˣ���½������Լ�ˡ�
��Щ���˰�������ı��ְ��պ����ڣ����ó�������������������ѳ��������ѳɣ�������أ�����һ������ء�Խ�ǹ�ά�ú�������������Խ�ѹ���ҲԽ�ż�����Ϊ��Ǯ�Ļ������ѳ����ˡ�
�ò����ף�����Űѻ��������⣬˵���Լ�Ҳ������һ����ľ��Ч��ϣ������ȴ�һ��Ǯ������
�������������պͲ���������ʣ����Լ����ʣ�������֪������˵���ܴ�ʮ������������ľ�𣿡�
��������������Ͻ��ӿڣ��������������ģ������ҵġ���
���⻰�Ͳ����ˣ������պ����ƴ��𣬡�����ԭ����ô˵�ģ�һ�������ľֲ������Ǯ��������������ͼ��ı�����ȥ���������з֣�ֻҪ��������ʵȱ֪����������Ҳ�ܲ���һ����Ʒ����ʽ�������㻨Ǯ��Ч����
�⻰�ѳ����ʵ��ſڽ��࣬ԭ�α�¶���������˷�����˵���������緸���ϻ���Ǯ����ʹ��Ҫ��Ч������֪����ľֲ�˵����ȳ����٣���������£��ö��ټۿ�����뷨�Ӵ��˻�������
������������������˼ҹ������ӵ�˵�����Ȳ�֪Ȥ����˵��ȥ����Ҫ��ڵ����ѵĵ�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