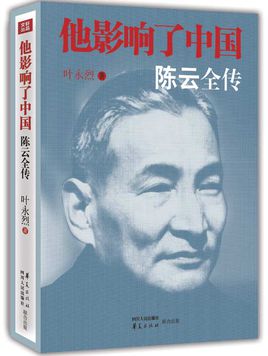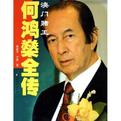慈禧全传-第1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在窥看得出神的时候,那辆蓝呢后档车,忽然停了下来,皇帝便轻轻叫一声:“小李!”
跨辕的小李跳下车来,也正要跟皇帝回话,他拨开车帷,轻轻说道:“奴才去打听‘查楼’。”
“嗯!”皇帝点点头,又说:“有人的地方,可别自称‘奴才’,也别叫我‘万岁爷’。那不露了马脚?”
“那,那,”小李结结巴巴地说,“那就斗胆改一个字,称‘万大爷’?”
“大爷就是大爷!还加上个姓干什么?”
“是!大爷。”
小李答应着,管自己去打听“查楼”。皇帝这时候比较心静了,默默地背诵着一首诗:
“春明门外市声稠,十丈轻尘扰未休。雅有闲情征菊部,好偕胜侣上查楼;红裙翠袖江南艳,急管哀弦塞北愁!消遣韶华如短梦,夕阳帘影任勾留。”
一面默念,一面想象着红裙翠袖,急管繁弦的光景,恨不得即时能作查楼的座上客。
“打听到了。”小李掀开车帷说,声音很冷淡。
“在那儿?”
“敢情就是肉市的广和楼,”小李说道,“实在没有什么好逛的。”
“不管了!去看一看再说。”
于是车子转西往南,刚一进打磨厂,只听人声嘈杂,叫嚣恶骂,仿佛出了什么事似的。皇帝从未听见过这种声音,一颗心立刻就悬了起来。掀帷外望,只见路中心对峙着两辆极华丽的车子,两名壮汉戟指相斥,几乎就要动武,四下看热闹的人,正纷纷围了上来。
“走,走!往回走!”他听见小李急促地在喊。
然而已经晚了,后面的车子涌了过来,塞住来路,只得“搁车”。过了一会,小李又来回奏,说是礼王府和贝勒奕劻家的车争道,互不相下,两家的主人都喝不住。
“那不要反了吗?”皇帝很生气地说。
一句话未完,只听“叭哒、叭哒”的响声,极其清脆地传了过来,小李立刻欣慰地说:“好了,好了!巡街御史到了!”
果然,豪门悍仆,什么不怕,就怕巡街御史,一听“响鞭”声,顾不得相骂,各自上车赶开。霎时间,车走雷声,散得无影无踪,而小李则比那些人还要害怕,深怕泄露真相,催着车伕,从东河沿回城。查楼始终没有看到,不过皇帝倒体谅小李,虽白跑了一趟,并不怪他。
一回宫皇帝就听总管太监张得喜奏报,说皇后违和,于是皇帝便又到承乾宫去探视皇后。病是小病,只不过玉颜清瘦,并未卧床。
要药方来看,已有四张,皇帝才知道皇后病了好几天了,虽是感冒微恙,究竟疏于慰问,内心不免歉然,所以问长问短,显得极其殷勤。
等皇后亲手奉茶的时候,皇帝忽然说道:“我看你换个地方住吧!”
好端端地,如何想出这话来?皇后微感诧异,便即问道:“皇上看得这里,那儿不好?”
“我怕这屋子……。”
皇帝缩口不语,因为怕说出来会使皇后心生疑忌。承乾宫是东六宫中很有名的一座宫殿,在明朝一向为贵妃的寝宫,崇祯朝宠冠一时的田贵妃就住在这里。到了顺治年间,相传为董小宛的董鄂妃,也住在这里,这异代的两位宠妃,都不永年。道光年间,皇帝的嫡亲祖母孝全成皇后,大正月里暴崩于此,死时才三十三岁,宫中相传是得罪了恭慈皇太后,服毒自杀的。总而言之,在皇帝的感觉中,“这屋子不大吉利”!
皇后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但也不便追问,只觉得承乾宫近依慈安太后的钟粹宫,慈爱荫拂,没有什么不好,因而含笑不语,无形中打消了皇帝的意思。
“你阿玛到差了没有?”皇帝问。
问到后父,皇后再一次谢恩,但崇绮是否到了差?皇后不会知道,同时觉得皇帝这话问得奇怪,“我在宫里,”她这样笑道,“那儿知道啊?”
皇帝想想不错,“倒是我问得可笑了。”他说,“也是你阿玛运气好,正好有这么一个缺,户部堂官的‘饭食银子’,每个月总有一千两。”
“那都是皇上的恩典。”皇后又说,“听说桂清为人挺忠心的,有机会,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的好。”
“哼!”皇帝冷笑,“本来是看他在弘德殿行走的劳绩,有意让他补户部侍郎的缺,调剂调剂他,谁知道他不识抬举,专爱捣乱。”
“喔,怎么呢?”皇后明知故问地。
“他跟李师傅搅和在一起,专门说些让人不爱听的话。”
“话不中听,心是好的。”皇后从容答道,“史书上不都说,犯颜直谏是忠臣吗?”
“就为了成全他自己忠臣的名声,把为君的置于何地?”皇帝摇着手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有些话,都故意那样子说说的,根本没有那回事儿。”
“是!”皇后先答应一声,看皇帝并无太多的愠声,便又说道:“史书上记那些中兴之主的嘉言懿行,皇上可不能不信。”
皇帝默然。沉吟了一会,忽然问道:“你说说,你愿意学那一位皇后?”
“历代的贤后很多,”皇后想了一下,“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太祖的马皇后,都了不起。”
“本朝呢?”
“本朝?”皇后很谨慎地答道,“列祖列宗,都该取法,尤其是孝贤纯皇后。”
这等于把皇帝拟作高宗。皇帝一向最仰慕这位得享遐龄的“十全老人”,听了皇后的话,自然高兴。
就这样谈古论今,而出以娓娓情话的模样,皇帝感到很少有的一种友朋之乐。皇帝有时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他没有朋友,勉强有那么点朋友味道的,只有一个载澂,然而载澂虽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却比他懂得太多。因此,皇帝跟载澂在一起,常有争胜之心,而有时又得顾到君臣之分,这样就很难始终融洽,畅所欲言。
跟皇后不同,皇帝认为“状元小姐”自然是才女,学问上就输给她也不要紧,而况又没有外人听见,不必觉得着惭。当然,皇后受过极好的教养,出言非常谨慎,从不会伤害到皇帝的自尊心,只是相机启沃,随事陈言,如果皇帝沉默不答,她亦很见机,往往就此绝口不提。而遇到皇帝有兴趣的话题,即使她无法应答,也一定凝神倾听,让皇帝能很有劲地谈下去。
谈到起更,宫女端上来特制的四色清淡而精致的宵夜点心,皇后亲自照料着用完,宫女来奏报,说宫门要上钥了。
这意思是间接催问皇帝,是不是住在承乾宫?皇后懂她的用心,却不肯明白表示,只说:“再等一会儿!”
皇帝自然也知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却颇为踌躇。想到慈禧太后,又想到慧妃,再想到皇后,如果这一天住在承乾宫,明天说不定又被传召到长春宫,要听一些他不爱听的话,而皇后则至少有三、五天的脸色好看。一想到慈禧太后对皇后那种冷淡的脸色,皇帝就觉得背上发凉。
“我还是回去吧!”皇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头也不回,他怕自己一回头,看到皇后就会硬不起心来。
一回到乾清宫,在皇帝顿如两个天地。迢迢良夜,世间几多少年夫妇,相偎相依,轻怜蜜爱,而自己贵为天子,却必得忍受这样的清冷凄寂,如何能令人甘心?
“万岁爷请歇着吧!”小李悄然走来,轻声说道:“奴才已经叫杨三儿在铺床了。”
杨三儿是个小太监,今年才十四岁,生一双小爆眼,唇红齿白,伸出手来,十指尖尖,象个女孩子。这一夜就是他关在屋里,伺候皇帝洗脚上床。
第二天就起得晚了,在书房里,觉得头昏昏地,坐不下去,托词“肚子不舒服”,早早下了书房。跟军机见面,也是草草了事,另有两起“引见”,传谕“撤”了。
※ ※※
转眼到了年下,园工暂停,各衙门封印。这年京里雨雪甚稀,所以清闲无事的官员,在家围炉纳福的少,在外玩乐饮宴的多。最普通的玩法,就是约集两三至好,午后听完徽班,下馆子小酌,日暮兴尽而归。
因此,饭馆跟戏园都是相连的,而每家饭馆,无不预备胡琴鼓板,为的客人酒酣耳热之际,要“消遣”一段,立刻可以供应。前门外几家有名的饭馆,广和居、福兴居、正阳楼、宣德楼、龙源楼,入夜无不大唱皮簧,唱得好的,可以使行人驻足,有个翰林王庆祺就有这样的魔力。
这天是他跟一个同僚张英麟,听完程长庚和徐小香的《镇澶州》,在宣德楼吃饭,一时技痒,张英麟操琴,王庆祺学着徐小香唱了一段小生戏。
王庆祺在小生戏上,颇有功夫,又是天生一条翎子生的嗓子,清刚遒健,真有穿云裂帛之概。“力巴看热闹,行家看门道”,王庆祺又不仅嗓子让外行欣赏,咬字运腔,气口吞吐,废寝忘食地,下过不少琢磨的苦工。加上张英麟的那把胡琴,因为常在一起“消遣”的缘故,衬得严丝合缝,把王庆祺的长处,烘托得如火如荼,而偷巧换气的地方,包得点水不漏。所以一曲既罢,左右雅座和帘外倾听的食客、跑堂,喝采的喝采,赞叹的赞叹,都巴望着再听一段。
王庆祺和张英麟,也都觉得酣畅无比,但京师是藏龙卧虎之地,切忌炫耀,讲究的是“见好就收”。王庆祺倒还兴犹未尽,而张英麟自觉这段戏,这段胡琴,都颇名贵,“人间那得几回闻”?因而不待王庆祺有所表示,便将弓往轴上一搭,拿胡琴套入一个布满垢腻的蓝布套中,顺手取一块手巾,使劲擦着手。
就这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十八岁的华服少年,后面跟着个穿了簇新蓝洋布棉袍的俊仆。张英麟始而诧异,继而恼怒,这样擅闯客座,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正想开口叱斥,只见王庆祺已在跟那少年搭话了。
“尊驾找谁?”
“找那唱《镇澶州》的。”华服少年答说,声音平静从容,但听来字字如斩钉截铁,别具一种威严。
王庆祺看到那少年的帽结子是一块紫红宝石,心想大概是那家王府中的子弟,荫封的镇国公之类,公爵的顶戴,不就是宝石吗?
有此警觉,王庆祺不敢怠慢,“喔,就是我。”他说,“偶尔消遣,不中绳墨,贻笑了!”
华服少年点点头:“不必谦虚。唱得很好,弦子也托得好。”
“那是敝友。”王庆祺指着张英麟说。
华服少年看着他微微笑了一下,接着转脸又对王庆祺说:“你能不能再唱一段我听?”
王庆祺回脸去看张英麟,他脸上是困惑好奇的神色,也没有发觉王庆祺的征询的眼色,那就不管他了。“可以!”王庆祺说:“我再唱一段二六,请教!”
张英麟这时有些如梦方醒的模样,既然王庆祺已经答应人家,自然不能不算,便拿起胡琴,坐了下来。那俊仆却不待主人逊座,自己动手端了张椅子,放在王庆祺对面,用雪白的一块手绢擦干净,才叫一声:“大爷!”
大爷便毫不客气地坐了起来。听胡琴“隆得儿”一声,王庆祺张口就唱,同时把一条腿踡曲着,做成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两手合在一起搓弄着,是耍手铐上的链子的“身段”,这就不用听,便知王庆祺唱的是《白门楼》。
王庆祺因为有知音之感,这段《白门楼》唱得格外用心,把穷途末路,万般无奈,以及犹存万一之想的贪生的哀鸣,曲曲传出。等唱完了,放下腿来,拱拱手矜持地笑道:“见笑,见笑!”
“真不错。”华服少年问道:“你在那个衙门当差啊?”
“我在翰林院。我叫王庆祺。”
“喔!”华服少年问道:“你是翰林吗?”
“对了!”王庆祺答道,“翰林院检讨。”
“那么你是戊辰科的罗?”华服少年问。他的算法不错,王庆祺应该是同治七年戊辰科的进士,点为庶吉士,到同治十年大考、散馆、留馆,授职为检讨,不然就该转别的职位了。
但王庆祺却不是,“我是庚申科的。”庚申是咸丰十年。
“中间因为先父下世,在籍守制,所以耽误了。”
华服少年又指着张英麟问:“他呢?”
“这是张编修。”王庆祺代为回答。
“你们是同年?”
“不是!”这次是张英麟自己回答:“王检讨是我前辈,我是同治四年的。”
“你是山东人?”华服少年问他。
“山东历城。”
“名字呢?”
这话问得很不客气,张英麟怫然不悦,但就在这时候,王庆祺抛过一个眼色来,他便忍气答道:“张英麟。”
华服少年点点头,转脸向他的俊仆看了一眼,仿佛关照他记住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似的。
“今天幸会。”王庆祺将手一伸肃客,“不嫌简慢,何妨同饮?”
“不必!”华服少年摇摇头又问:“你的小生戏是跟谁学的?”
“我是无师自通。喜欢徐小香的路子,有他的戏,一定去听,有时也到他的‘下处’去盘桓。日积月累,自觉还能道得其中的甘苦。”
“‘下处’?”华服少年回头问他的俊仆:“什么叫‘下处’?”
“戏班子的所在地叫‘大下处’。”王庆祺答说,“成名的角儿,自立门户,也叫下处。”
“喔,那就是说,你常到他家去玩儿?”
“对了。”
“最近外头有什么新戏?”
“很多。‘四箴堂’的卢台子,编了好几出老生戏……。”
“我是说小生戏。”华服少年打断他的话说,“生旦合串的玩笑戏。”
“这……,一时倒想不起来。”
谈到这里,一直侍立在旁的俊仆开口了,“大爷!”他说,“请回吧!别打搅人家了。”
华服少年点点头,站起身来把手摆了两下,似乎不教主人起身送客。然后,踏着安详的步伐,回身走了。
“这是什么路道?”张英麟不满地,“好大的架子!”
“轻点!”王庆祺说,“我猜是澂贝勒。”
“不对。澂贝勒我见过。”
“反正一定是王公子弟。慢慢儿打听吧。”
话虽如此,王庆祺年下要躲债,避到他京东的一个同乡家,没有闲心思去打听。送灶那天,张英麟不速而至,一见面就说:“我找了你好几天,真把我累坏了!”他又放低了声音,叫着他的号说:“景琦!你知道咱们那天在宣德楼遇见的是谁?”
“是谁?”
“是皇上。”张英麟唯恐他不信似的,“千真万确是皇上。”
王庆祺又惊又喜,只是不断眨眼发愣,张英麟却有些惴惴然,看见王庆祺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