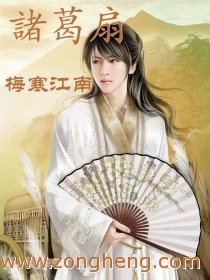诸葛亮传(I-V5部全)-第2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敲出一个个旋涡。
就要离开江州了,为了盘踞在这两江交汇的要隘,用了很多心机,使了很多手段,最终还是不得不走。
他不想去汉中,搬迁去新地方也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他只是不想成为受人牵制的傀儡,总是被无形的阴影压住,唯唯诺诺如同百无一用的窝囊废。
当张裔的死传入江州,他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他虽然惊讶于张裔没有出卖他,也隐隐感觉是诸葛亮放了他一马,可他最终推翻了这个猜测。诸葛亮不会这么仁慈,他之视诸葛亮为死敌,一如诸葛亮视他为死敌,他们暗中角力很多年,彼此都想彻底打倒对方。就算诸葛亮掌握了他在盐铁亏空上的罪证,却没有举报朝廷,也是诸葛亮出于对他的忌惮,而不是因为情谊。
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倾轧中,从来就没有软弱的同情,谁若软了心肠,谁便会遭到失败,而失败者永远不会有好结果。
李严叹了口气,看见儿子李丰从前廊走过来,一身簇新的武官朝服,李丰新擢为江州都督,督典汉中军务后事。
“父亲!”李丰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李严轻轻扶起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刚上任的新官,五分欣慰,五分怅惘。
对李丰,他既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又有许多的失望,父子虽然血脉一体,可儿子在很多事上不和自己一条心。在李严和诸葛亮争权的事情上,李丰并不完全赞同李严,他以为诸葛亮忠勤王事,忘身为公,是值得尊重而拥戴的长者,不该揣了私心去夺权,便为这不能媾和的妥协,父子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想起儿子对自己的反抗,李严有些沮丧,他握住李丰的手,轻轻拍着,意味深长地说:“丰儿,你这都督之职来之不易。”
李丰约莫知道父亲的意思,可他不愿意勉强自己,只诚挚地说:“父亲,你此去汉中,一别千里,定要保重。”
李严想要的其实不是这句话,他殷殷期望儿子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可让一个人改变太难,他觉得无力,偏是有苦说不出,他放开了儿子,郁闷地皱着一张脸:“我这一去汉中,也不知是个什么下场。”
李丰和风细雨地安慰道:“父亲都督汉中军务,为北伐后援,又获开府之权,更为朝廷倚重,何为发此喟叹。”
李严摇摇头:“你不懂,我哪里是受倚重,我这是掉进网罟里,成了人家砧上的鱼肉,生死由不得自己!”
李丰以为李严多虑了,他笑劝道:“父亲想太多,哪里有这许多顾虑,父亲为朝廷尽力,只会受恩典,何来网罟一说。”
李严不知该怎么和他解释,他私下里做的很多阴事儿,包括盐铁亏空都瞒着儿子,若是李丰知道自己在悬崖边上已走了多年,也许就不会如此宽怀了。他不禁惆怅一叹:“你啊,偏是个好人!”
他定了定心神,一字一顿地吩咐道:“自此父子远隔,你专阃一方,大小事都要给我来信,万万不可专断。”
大小事都要书信往来,这也太拘束手脚了,李丰觉得奇怪了,他承诺道:“父亲放心,儿子定当小心做事。”
“你没明白,”李严正色道,“你太年轻,遇事易躁急,处分一旦不慎,既误了公事,又损了自己,你不要嫌麻烦,不过多动动手,两封书信转手,也能少犯错不是?”
李丰想父亲也许当真是为自己考虑,便应了一声:“是。”
李严重又挽住儿子的手,脸上抹开了捉摸不透的笑。
※※※
凄风苦雨中,一行马队艰难地爬行在西汉水以北的崎岖栈道上,仿佛一条浊流一点点推进被群山环抱的汉中平原。遥远而不可及的前方,秦岭那宽厚的脊梁被灰色的冷雾笼罩,仿佛被水打湿的书页里,一条用淡墨染出的巨龙轮廓。
雨丝很细长,仿佛一柄柄从天空刺下的透明冰剑,或许是要下雪了,天色越发阴沉黯淡,半边天向前坍陷俯冲,便要和远处蜿蜒的秦岭山麓闭合成一条死线。
道路难行,马车忽地一阵颠踬,车帘荡了起来。诸葛亮抬起头,刚巧看见姜维擦身而过的背影,他失了一霎神,忽然喊道:“伯约!”
姜维一勒马,回头问道:“丞相何事?”
诸葛亮有好一会儿没吭声,似乎觉得难以启齿,他见姜维的肩上落满了雨珠,像是长了一层晶莹的毛边,他伸出手:“你上车来。”
姜维没有反对,他对诸葛亮几乎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一撩缰绳,便登上了马车,车里本还坐着修远。修远很懂事地跳下车去,还把车帘拉紧,吩咐车夫赶车慢一点儿。
诸葛亮静静瞧着姜维,目光满是慈和:“伯约,有点私事问你。”
“丞相,您说。”姜维恭敬地说,他对诸葛亮,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无限的爱戴,诸葛亮吩咐他做的事,他一定会妥妥帖帖地完成,若是诸葛亮此时令他孤身闯敌营,他也会义无反顾地舍身以往。
“我有一个女儿,”诸葛亮生平第一次感觉说话是那么困难,像在转动一具笨重的大磨盘,“果儿,你知道的。”
“唔,知道。”姜维点头,脑子里过影似的飞过一个女孩儿好看的笑容,他觉得脸有点烫。
诸葛亮磨蹭着:“她……”
唉,真是没用,身为持掌一国权柄的丞相,无数次在三军阵前慷慨陈词,无数次在百官齐聚的朝堂上振振言事,竟然没有勇气说出一个父亲的渴慕。
诸葛亮以为自己拖沓得太可恨了,索性将旁敲侧击和娓娓道来一概抛弃,他干脆利落地说:“你愿不愿意娶她?”
姜维的脸红透了,他低着头,许久没有回答。
雨滴敲着车板,宛如女儿家不经意掉落在水面的耳珰,一圈涟漪,又一圈涟漪,荡漾出瞬息缤纷的无数张脸孔,有熟悉的,也有熟悉却被远远离弃的。他仿佛从梦中缓缓苏醒,用很小的声音说:“丞相,对不起,我不能。”
姜维说的是不能,而不是不愿。
这是姜维这一生唯一一次拒绝诸葛亮。
诸葛亮像是早知道答案,他没有太多的失望,也没有一丝责备:“没关系。”他看着这个局促不安的年轻人,温和地笑了笑。
两人便没再交谈,似乎被沉重的心事压住了,雨还在下,点点滴滴如泣如诉。
再看那外边,已是铅云低垂,天色如垢,雪越下越大,迷迷茫茫犹如撒盐,不过片刻,整片天地笼罩在白皑皑的纱幕中。冰雪统治的世界里,一切都在逃避,一切都在藏匿,生气勃勃的激烈,鲜活明亮的热爱全没了影儿。
车马顶着风雪迟滞地前进,一行行车辙印、马蹄印、人足印彼此交叠,弯弯曲曲地伸向雾气蔼蔼的远方。
大雪缤纷中,建兴八年就这样过去了。
卷三 征程艰难
卷首
南来的春风犹如脱缰的野马,驰骋之处,冰雪尽消,绿意抽芽。危峰耸峙的祁山显出了俊俏的轮廓,仿佛淡妆的女子终于洗净铅华,把天然去雕饰的面容坦白地展示在镜子似的阳光下。天地间浮躁起蠢蠢欲动的力量,仿佛一只冬眠太久的庞然野兽,便要从洞穴里钻出来。
上邽城外,在一面绣着“司马”墨字的硕大旌旗下,鲜红的流苏像血一般淌在司马懿的脸上。他一夹双腿,坐骑踏踏地奔出去百余步,极目远去是朦胧如粉黛的薄雾,雾下沉默着一簇流动的金黄色,那是大片的麦田,在暖风里不甘寂寞地摇曳,好似女子旋转的裙摆。
司马懿感慨道:“秋粟熟了。”
跟在他身后的众将军听得司马懿生出这般喟叹,又是疑惑又以为可笑。大战在即,三军统帅还有闲心吟赏风物,是他强作镇静,还是心不在焉呢?
张郃忍不住了,驱马上前,郑重其事地说:“大将军,诸葛亮围攻祁山,贾嗣、魏平二位将军告急频仍,望大将军早做决断。”
司马懿沉浸的神色像被挖了一个缺口,那份入迷统统流了出去,他似乎对张郃妨碍了自己观赏风景有些不满,眉目微有郁色,却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当年张郃在街亭大破马谡,创下不世奇功,皇帝倍加赞赏,特进爵禄,以为“微张郃,诸葛亮入长安久矣!”加拜他为征西车骑将军,专以他为抵挡蜀军的巨擘,张郃既开了个头,其余人都七嘴八舌起来。
雍州刺史郭淮说道:“大将军,用兵之机一瞬即逝,还望大将军早做决断,贾、魏二位将军等不得了。”
“末将愿请命去救祁山!”费曜慨然说道。
“末将也愿往!”
“大将军,祁山危矣,援兵当速行!”
司马懿只觉耳际有成群的苍蝇在扇翅膀,这帮武将自视太高,一个个摆出慷慨激昂的雄伟模样,全不把他这个专阃大将军当回事。他太知道他们,个个身负战功,又是三朝宿将,眼皮都长在头顶上,不甘服膺人下。曹真任大将军时,因他为皇室亲贵,兼之战功彪炳,自曹操之世便深蒙倚重,尚能约束武将。去年曹真病逝,魏国的功勋武将们越发脱了管束,你不服我,我看不惯你,朝堂之上往往因口舌不忿而拳脚相加,也不知惹出多少笑话来。皇帝曹睿超擢司马懿为诸将之首,也是看重他为三朝元老,又屡立功劳,但要镇住这些盛气凌人的武功之臣,仍然费力。
“救是要救,可不能轻举妄动。”司马懿尽量和气地说。
张郃抢先道:“请问大将军,当如何谋划?”
追问太咄咄逼人,全没有上下级该有的尊重,司马懿很不高兴,他忍住不悦:“我之意,是由费耀将军率四千精兵守护上邽,余众随我西救祁山。”
张郃追着司马懿的余音说:“大将军三思,全军出动恐非上策,莫若再分兵雍、郿,以免诸葛亮偷袭后方,致使我首尾不相及。”
司马懿淡漠地笑了一声:“俊乂所虑,虽合兵法,然俊乂忘记楚分三军,乃为黥布所擒之故事乎?”
张郃一阵哑然,司马懿所说的典故他并不陌生,这说的是汉初黥布谋反,寇掠荆楚。楚军为抵御黥布,将兵力一分为三,欲成掎角互依之势,不料正因其分兵反而酿成大祸,黥布以全军出击楚军一军,其一军败亡,余两军自溃。
司马懿慢悠悠地说:“若前军能独当之,俊乂言是也,若不能当,我军又一分为多,此为重蹈楚军覆辙也。”
张郃虽以为司马懿在理,却还是不甘心地说:“可若以全军出战,万一遭了蜀军埋伏,外无援兵,内损斗志,或有覆军之忧。”
司马懿不想和他争执,再争论下去,只会惹彼此嫌隙,他着力地说:“不必多言,且照此策而行兵,费耀、戴陵二位将军留守上邽,余下全军出击。”
他一甩马鞭,策马朝前跑了两步,把那些仍想进言的武将落在身后。
面前的世界开阔而充实,一壁青山像天地的门户,挺立着静穆的面孔,山脚下是海浪般起伏连绵的春麦。农人们骑着牛悠闲地穿行在麦田里,自在地哼鸣出陇右一带的歌谣,歌声悠远、深沉而古老,仿佛承载着这片广袤土地的千年传说。
司马懿仰起头,有一行燕子剪着风匆匆飞过,一簇簇白云像肆意盛开的奶色牡丹,欢乐地吐露着芬芳。
司马懿玩味地笑起来,又一行飞鸟穿云而出,仿佛一支鸣镝,清啸着直入天尽头那一片妍丽的春光中。
第一章 引蛇出洞卤城获大捷,中军论兵将帅生分歧
蜀汉建兴九年,祁山。
绿杨芳草,翠叶藏莺,春光如轻薄的纱衣笼在天地间。
晚间淅淅沥沥下了一场蒙蒙细雨,因是春雨,并不急切喧哗,恰似听了一夜的轻歌曼舞。早起雨渐收了,道路也不泥泞,浅浅的几行雾水零星般点缀在叶面上,宛若喜极而泣的泪珠子。
西汉水北侧的祁山脚下密匝着累累营房,背靠横亘绵延的祁山,面朝广阔无垠的原野。营帐的最高处竖起两面豁然醒目的大旗,其上分书“汉”与“诸葛”,明灿灿的春光照上去,像打了一层不褪色的蜡。
营门缓缓开了,一队百人左右的蜀兵逶迤进入营寨,身侧辚辚驶着二十余个奇怪的机械家伙,说它是牛,又像马;说它是车,偏没有轮子,行动之际,只需人力时不时轻轻搏动,竟能堪堪自如。
“回来了?你们可是最后一拨!”辕门口哨楼上的士兵探出头来,喜滋滋地朝下面的小队喊道。
领头的士兵抬头大声地说:“是哦,我们策应后队,所以最后一拨到!”
哨兵笑道:“昨儿晚上,丞相跟中队回来了,我还琢磨怎么你们没来呢,原来是押后的。如今粮草归入仓廪,足足够大军用两个多月呢!”
“嘎嘎!”营门再次关严。
这一百来人负载粮草的小队安静地行进在肃然齐整的军营,径直走向仓廪营库,迎面不时走来巡营的士兵,并不多话,只用眼神微微一睨。
昨晚上,飞絮般的细雨中,司马懿率领魏军主力奔往祁山救援,一直围困祁山的蜀军却忽然折转向东,除留少部主力牵制魏军主力,大部队轻骑奔往上邽。魏军留在上邽的兵力到底单弱,被蜀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蜀军便趁此大胜,刈割上邽小麦,分队运回大营。
蜀军都已经见识过夜晚大队押粮军的浩荡雄壮了,这会儿见到小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虽仍微微有点兴奋,总也比不上昨夜的热血贲张。上万人的军队绵延在上邽城郊的南北要塞间,无数燃烧的火把连成了一条蜿蜒的火龙,在星空寥落的天幕下翻腾咆哮,仿佛黄河奔流到海的壮阔伟烈。
诸葛亮故意大造声势,让收到消息提兵从祁山返回上邽之东的司马懿不敢出击,眼巴巴地看着蜀军大摇大摆地运了粮草回营,亦只有扼腕沮丧的份了。
小队押粮兵经过中军帐时,迎面急匆匆地走来一个人,怀里抱着一扎文书,似乎正要进帐。
“费司马!”领头的士兵行过一礼,后面的士兵都跟着一拜。
费祎点点头,他刚从成都赶到祁山,满面风尘,还来不及休息便要赶去见诸葛亮。
这几年来,他已习惯了几地奔波,将成都的重要公文亲自送给远在前线的诸葛亮,再把已经处理好的公文或者节略呈给尚书台,或直呈皇帝。若是寻常官曹署文一般由驿传邮递,若是皇帝公谕和重大公务则由他一路护送。诸葛亮细致到苛刻,寻常之人怕是跟不上诸葛亮的思路,接回的处分节略哪些要分署派送,哪些属加急文书,应定什么层次的加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