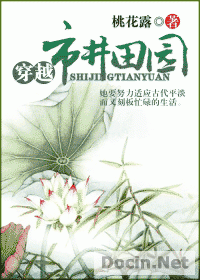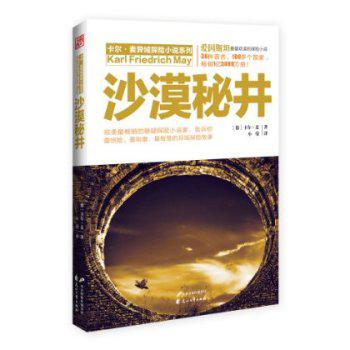梆子井-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下来的动作更不能让人忍受。“全体蹲下,抱住头走一圈!”于是,就这样子,象鸭子似地走了一圈。然后又俯身向下,“把屁股抬起来!”后面的人扳开屁眼看了看。接着,就触摸到那个要害的地方,这又使我产生了一阵恐慌。记得那个“医学鉴定”上说,我没有性功能,但医生很快就放过了我,却在张文庆的那里揉捏了半天……
一切终于完了,接下来就是静静地等待。这个阶段,我做了许多美好的设想。穿上军装我要见的第一个人,你猜是谁,无疑是彭敏敏!我要到她的家里去,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交谈。首先,我要对不能履行诺言表示遗憾,但也不能说我不履行诺言:剧本毕竟引起了轰动,还得了奖,那么,也就不存在到一个地方下乡的那一说,不存在什么诺言。那么,遗憾也就不必要,致歉就更谈不上,那又谈些什么呢?老实说,我还没有想好交谈的内容,也许仅仅就是告别吧?但是,只要穿上军装,我就有许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只要我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什么美好的语言不会有呢,什么动听的词句不会从我的嘴里迸出呢?况且现在,各方面都露出了好的迹象:奶奶的遣返再次放黄了,老刘神不知鬼不觉把奶奶从名单上抹去了!尽管舅舅说,不能让他担太大的风险,尽管我和奶奶已经做好了下乡的准备。
那天晚上,老刘和舅舅谈了半宿。“我就把伯母的名字从名单上一抹,再填上个别人的名字,这样最简单。”舅舅还一再说,风险太大,让他想个两全的办法。“有什么两全的办法呢?何况现在也没有时间了,明天就要交给下面办理呢!”奶奶听说把她删去还要填上个别人的名字,“老刘,咱不做那事情,别人和咱又没仇没怨的。”“这是个刚死的人,老天爷已经遣返过了。”最后,老刘又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老陈,我的党籍是你为我保住的,现在就是丢了也没有啥,丢了,大不了不当所长了,我还是一般干警。”舅舅拉着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临走,塞给他了一瓶退字灵。
事后我才知道,老刘在分局时和一个女干警发生了不应有的关系,局里为此要开除他的党籍,负责此事的部门让他写一个事情经过,说视情节给予不同的处理。于是他来找舅舅,舅舅用了一个星期,终于使他保住了党籍。最后不过是降职,调到我们这个所任所长了。
但是过后老刘又对舅舅说:“即就是没有这事情,伯母的事我也要管,因为伯母是个好人,当然这也是我来找你才知道的……”
体检结果终于下来了!张文庆被刷,他的睾丸发育不健全。这么看来,我还是健全的!难怪最近体内总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对女性,尤其是彭敏敏,总有一种特别想接触的要求。但我还是决定,穿上军装再去找她。说不出什么就不说什么,只要穿上军装往她面前一站、就胜过万语千言,可这又免不了有炫耀之嫌。那么,究竟以什么方式和她告别呢?总不能走的时候也不和她见一面,那样的话,只能说明我无情,我因为境遇的变迁而忘了同学、忘了朋友,忘了昔日的情分,而我也本无意这么做,我必须和她私下里见上一面!也许,她会来找我吧?象那次补课一样,无非找一个冠冕的理由,她又会找什么理由呢?“你要走了,我来看你一下。”眼睛低垂,揉着衣角。或者是,“要走了,也不和老同学说说话?”眼睛直视,面带微笑。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问题!
体检完后就是政审了。这是一种不允许当事人参与的漫长的等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过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父亲是革命干部,四五年就参加了革命。母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至于奶奶吗,实际与我并没有太大的牵连,不能说我在这里寄养了一段日子,就沾上了资产阶级的血缘,这毕竟是我的外祖母家,要论血缘也不是直系。这样一想,也就坦然地接受了那八个字!
但,等待总是难熬的!即使结果再好,也希望这个过程缩至最短。因为它延长一天,你的思想(那讨厌的思想啊!)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迫使你将已得的结论推翻,重新审视每一个细节,而只要你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也就会对自己进行一番必要的审查。别人的审查不过是发现一些你没有发现的东西。因而;你审查得越细,别人的审查就越和你接近,结果也必然趋于一致!倘若;你确实有“不洁”之处,那么一味地等待,只能是自欺欺人!须知;审查者的眼睛是经过磨练的鹰眼,专门于细微处见功夫!即使芥粒般的东西,他们也会放大了来看。他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如剥茧般看到你的骨子里去!他们的想象丰富至极,胜过一切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会由现在想到未来,甚至千秋万代。你那些尚未暴露的缺陷,他们早已为你设想了结局!而且其中的细节也完美无缺,他们不愧是天才的诗人和作家!
而我现在却要徒劳的取而代之-------我试图站在他们的位置,把我解剖了来看;把我十七年的人生作一个细细的回顾。解剖自己毕竟是痛苦的,等待愈漫长,这个过程就愈残忍、愈惨烈!然而,毕竟没有对我不利的发现!于是,思想就向着美好的境界驰骋——这也许就是幻想的定义吧?
彭敏敏的影象又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同学、朋友、甚或别的,而目前也只能是同学,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好到什么程度呢,不过是让我偷看了一次考试卷。至于我送她上医院;她给我补课,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唯有这一次让我偷看试卷,是对我的一次惠顾,抑或是传递着一种信息。总之,从这个细节,我看到了她内心的某种东西!
她对我的剧本,那蹩脚的剧本,竟然给予了那么高的评价,而最后的结局;也竟然与她预料得完全一致!虽然剧本是失败了;但她的那份真情却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就要应征了,我原先的设想,因多变的生活而发生了变化,那么彭敏敏怎么办呢?我们马上就会天各一方,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她对我的那份情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呢?不;流失的只是时间,我们的感情将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永放光泽!
“常友新;你被刷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结果终于下来,这次被刷的只有我一人!李大军;穿着军装;到校园和同学们告别了;他仍然是那种自信满足的笑容,仿佛生活永远都充满阳光,仿佛他的人生永远都是光彩照人的。当然截止目前,也确实如此!所有被录取的同学,在校园里连转了三天,把他们的激动和兴奋传染给每一个人!
而我;几乎无颜再在校园里出现了!老师同学见了就问:“你是怎么搞的吗?体检都通过了,政审却被刷了!”而这也正是我来校的目的,我试图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启示,得到这件事情确切的原因,现在他们这样子问,我又能说什么呢?就连老陈见了也问:“我想不通;你怎么能当兵呢?*思想的大学校怎么能要你这种人呢?”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学校逗留下去了。
参军完了,像一片云在我的眼前飘散了!我编织了多少美好的想象,却原来,全是无谓的幻想!如今回想起来,当初就被人象小丑一样地推上了台;在台上还郑重其事地表演了一番;可是给观众留下了什么印象呢?也许在人生的舞台上;我永远都是点缀,都是配角!正如奶奶所说,“是给别人打旗旗的。”奶奶指的是我当不是红卫兵。如今参军,竟然也给别人当了陪衬。而且;当的这么冤枉:竟不知被刷的原因!唉;应征的过程是何等的漫长,又是何等的短暂!但不管是漫长还是短暂;给我的结局却全然一样!一场无谓的梦;一台自嘲的戏;一阵只有雷声没有雨点的风!唉;我可悲得就像那墙角的蜥蜴!可悲而又可叹,这也许就是我的人生写照吧?
但是,一个人,被捉弄到如此地步,却没有人来告诉一声,这是为什么?那又是何等的可怜!“回去问你自己吧!”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但我已经反复自问过了!我的经历短暂的就像天上的流星;清澈的就像丛林深处的清泉!唉;我比张文庆甚至还可怜!他就知道他的睾丸发育不健全。而我呢,却什么也不知!
“奶;这次参军我没参上;是政审刷了,我想可能是住到你这儿受了影响?”“那你就回你爸那儿去吧。”奶奶还没有说,舅舅却进屋说道:“你奶把你从小养大,你现在说受了你奶的影响?你奶也不想影响你,你还是回你爸那儿去吧。”奶奶问:“到底是啥事情吗?”我被舅舅说得满面羞愧,呆在一边无话可答。“就是他参军没参上,还有啥事情!”舅舅说:“你小舅回来说把他影响了,你现在又说把你影响了,那你们都不要在这个家呆好了,谁也没有让你们非要呆在这里。这个家就是再不好,也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倒怪罪起这个家来了。”想想也是,没有这个家,没有奶奶,我就没有存身之地,也就谈不上什么应征和参军的事,我怎么能埋怨起奶奶呢?但是奶奶说:“娃在这儿住着也是没办法,现在弄啥都讲出身。娃应该跟着他爸,他爸好着呢,但是他爸,唉,要不是有个后妈我就让他去了。”最后奶奶对舅舅说:“你看老刘和武装部认识不,让他打听一下,看到底是啥原因。”“老刘也不是万金油,抹到哪儿都行!”不过舅舅最后还是答应,让老刘打听一下。“把这个原因也就是得搞清楚,不然今后又要说把他影响了。”
老刘最近一直很忙,不是抓反革命,就是遣返地富反坏,好几次在街上我都看见他坐在三轮摩托里,把大盖帽的那个带子使劲地往下拽。现在斗争形势这么严峻,似乎不必再拿我这样的小事去麻烦他了。况且,我也不想再知道什么原因了,总归是没有参上,这就是现实!除了面对现实再没有别的,你又何必非要知道那个原因呢,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徒然悲伤,还不如不知道!小舅回来也对我说:“参军不行了就赶快活动招工,再不要钻牛角了。”于是在班上召开的摸底会上,我决定把我的底也亮一亮。
桂老师在班上说:“这次参军和留城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咱们班有四十名同学,也就正好是四名同学。现在,一个参军走了,还有三个名额,就是留城参加工作的,这三个同学必须是思想进步,学习优异,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同学。大家提议一下,看哪些同学具备这些条件呢。”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总会有人站起来:我提议某某同学,我认为他(她)思想进步,学习优异。某某同学在学工活动中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某某某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挖防空洞中,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等等等等。可是今天,桂老师等了半天,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真正说起来,同时具备“思想进步,学习优异,家庭有实际困难。”这三个条件的也几乎没有。于是桂老师说:“那就把各自家庭的情况摆一下吧。”马上就有了反应,王长顺站起来:“我把我的情况摆一下吧,我妈长年卧病在床,我爸今年都快七十了,虽说有个我姐,可我姐迟早要出嫁的。所以吗,我实际是独子养二老,大家说,我的负担重不重,我的命苦不苦,我的情况是不是特殊情况?”“好了,你坐下吧。”桂老师摆摆手;“还有哪位同学?”
刘光辉站起来:“我家的情况是,俺哥俺姐全下乡走了,俺妈虽然没躺到床上,但是也有病。更主要的,是我本人也有病,啥病?传染性肝炎!这么长时间我为啥一直没说,怕的是同学们不接受我……”刘光辉一说,各种各样的病马上层出不穷,肾炎、肝炎、高血压、关节炎,最后,有一个同学竟自称是“神经病”。桂老师问:“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犯过呢?”“我这个病是随环境呢,”他非常平静地说:“环境好,我的病就好;环境坏,我的病马上就犯!”哄堂大笑。
我倒没有笑。根据我的经历和医学常识,他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精神病,也不是一个什么要紧的病。前不久,舅舅带我到精神病院去了一趟。说了我的症状:没完没了地洗手,无休无止地做事。“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医生说:“也就是神经病,不是精神病。”由此我才得知,这两个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医生又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也由精神因素引起,不及时治的话,也可能发展为精神病。”因而我的病要比他的严重得多。他的“病”正如小舅所说,“到农村锻炼三年,啥病都没有了!”可他却说:“大家想想,我去了农村会产生啥后果?只怕是永远也回不来了!”“行了,你坐下吧。”桂老师说:“还有哪位同学?”
外号叫“栾平”的站了起来。“我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家弟兄俩个。我上有六十岁的老母,下有患羊羔疯的弟弟,我要是去了农村,他们怎么办?尤其是我弟弟,他离不开人,没人了他就要寻死,我得把他守着。”“俺妹子我也得守着。”前面一个同学站了起来:“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继母,她经常虐待我和俺妹子,我倒无所谓,俺妹妹年龄小我不能离开,我一走,俺妹妹就没命了……”
同学们的情况都令我同情,尤其是这一位,他的身世竟和我一样,但是他却没有象我那样有一个奶奶,于是,李翠仙折磨先房娃的那些场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总之,我觉得他的情况可以考虑。但是桂老师说:“据我所知,班上象你这种情况不止你一人。”并且,还举了我的例子。
接下来,同学们表述各自家庭的情况大致相同。不是父母有病就是本人有病,再不就是兄弟姐妹有病,而且个个说得情恳意切、潸然泪下,总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也说不清!末了,桂老师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同学们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但是我只有反映权,绝没有决定权。我想连里和学校是会综合考虑的。”散会后,她却走到我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