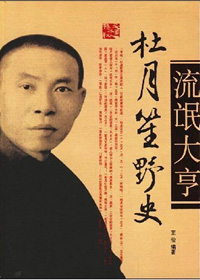杜月笙传-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刘航琛或则为刘湘的特使,或则为他自己的经济事业奔走,每一年至少有半年以上,仆仆风尘于渝、蓉、汉、京、沪各大埠间,其中尤以到上海的次数最多。他每一次到上海,必定身为杜门座上客,而且长日盘桓,为时甚久。在杜月笙的外界朋友之中,刘航琛要算是最亲密的了。
范绍增畅游黄浦滩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他本来是杨森的部将,后来改投刘湘,接洽时他提出一个条件:往后只要甫公有命令,叫我打什么人都可以,我就是不打杨子惠(森)。有此一条,刘湘反而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赏识。
他在四川帮会组织的主流──「袍哥」中,地位很高,他部下的官兵,清一色是袍哥因而平时不分级职,不论军阶,彼此都以哥子,兄弟互称,打起仗来,却是相当的剽悍勇敢,以此外间谑称他们为「袍哥军」。
范绍增这个人,生性豪爽,小事胡涂而大事精明,就外表上看来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他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喻人憨而傻也。范哈儿又颇有雅量,尽管他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即使有人当面以「哈儿」相称,他也笑嘻嘻的照答不误,而且丝毫不以为忤。
范哈儿好赌、好玩、不耐空谈,他出手阔绰,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因此他的阔名声传遍黄浦滩上,历久不衰。比诸张宗昌,毕庶澄的「夕阳无限好」,还要更胜若干倍。
民国二十年,刘湘和刘文辉一对堂叔堂侄,分据渝、蓉,势成水火,刘文辉不吝重金,意图收买刘湘的将领,范哈儿和蓝文彬各得大洋十万蓝文彬秘而不宣,种下他后来一囚七年的祸根;范哈儿拿了钱立刻陈明刘甫澄,大获刘督办的欢心,叫他把钱收下,再跟刘文辉虚与委蛇。
廿年六月广州生变,中共又在赣、湘、鄂境内猖獗;蒋总司令调徐源泉军入赣粤边境防堵,命刘湘出兵三万,接替徐军的防务,在湖北洪湖,跟共军贺龙作战;刘湘以王陵基代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跟贺龙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使贺龙的主力大受损失,鄂境共军从此一蹶不振,但是范绍增自己也因为身先士卒,亲冒锋镝,于是右腿受了重伤。
杜月笙在上海得到消息,立派他的爱徒张松涛,赶赴洪湖前线,把范绍增接到上海,送进最好的医院,延聘最高明的医师,悉心救治
总算挽回了范绍增的一条命,保全了他的一条腿,──祇不过略微有点儿跛范哈儿从此多了个绰号,范跛子。烽火余生,兼又在大上海花花世界,范绍增挟巨资以俱来,免不了想要大赌特赌,大玩特玩一番,以资庆祝,而遂自我慰劳。刘湘准了他一个月的假,杜月笙一连多日盛大招待以后,再派顾嘉棠奉陪,一天到晚的花天酒地,征歌逐舞
腰缠十万贯,重苏黄浦滩,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当年他出手之大方,居然在十里洋场引为奇谈,至低限度,一时不作第二人想。──范师长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欧、赏司阍的小郎,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金鱼头──上海人俗称红色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一百元为单位
花天酒地,誉满沪上,老上海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开盛燕,为他祖饯,席间,杜月笙身为地主,未能免俗的问他一声
「范师长,你这一次畅游上海,玩得痛不痛快?」
他这一问,恰好兜起范哈儿一件心事,于是,他眉头一皱的说
「痛快到是痛快,只不过,上海鼎鼎大名的那位红舞女,黄白瑛,这人实在是目高于顶,随我怎么样的陪小心,」福至心灵,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同席的陪客不禁为之喷饭,举座哄堂,──唯有杜月笙莞尔一笑不赞一词。范哈儿回到重庆,不出三天,一位满口沪白,娇滴滴嗲兮兮的女郎,打电话到渝简马路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黄白瑛也包机抵渝请范师长到她寄宿的旅馆,一圆旧梦。
刘航琛和范绍增,不但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二而且,也由于他和刘范二人的友谊,奠定了抗战八年,他变起仓卒,两手空空,居然能在西南后方得心应手,大展鸿猷的基础。
总领病假省六万
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四十四岁,这是他多姿多采,诡奇瑰丽的一生之中,最最绚烂璀灿变化莫测的一段时期。
由于食少事繁,饮食起居无法正常,他的健康情形并不为佳,就外貌上看来他瘦骨麟峋,两肩微耸,清瘦的面容,平顶头,使他的高颧、尖颏、隆眉、阔嘴,和那一对大而厚的招风耳朵,愈加显得突出。为了提神养气,他不得不借重阿芙蓉,但是每天人来客往,川流不息,当年周公一饭三吐哺,如今杜月笙更是难得抽足一筒鸦片烟,往往抽空吸两口提提神,烟枪刚搭上嘴唇,外面又在通报某长某长来也,于是杜月笙唯有丢下烟枪再去会客,在这种情形之下,抽鸦片变成了十万火急急就章,为此,特地把侍候好婆──沈月英母亲抽烟的郁永调得来。郁永馥早年在戏馆里卖鸦肫肝,乖巧伶俐,指法灵活,他能以最快的速度,装好高达一吋的烟泡,无论杜月笙要长抽短吸,都可以肆应裕如,从此郁永馥便专任为杜月笙烧烟泡之责。
如所周知,鸦片烟中的毒质,主要的是吗啡,轻量的吗啡能止痛催眠,重剂可以致人于死。吋把长的鸦片烟泡,通常只给杜月笙抽三两口便拋掉,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使他抽起大烟来不过浅尝辄止,因此他所中的吗啡毒不深,乍看之下,杜月笙决无鸠形鹄面、脸黄肌瘦的烟容。相反的,有空使抽一口,反而使他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杜月笙的鸦片烟抽了一二十年,而并无瘾君子貌者,其故即在于此。
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西捕之中捏第二号卡的萨利,每个月要从杜月笙手里拿两万大洋的俸禄,因为捏二号卡的西捕,管的正是鸦片烟与赌博。萨利在上海多年,赚的洋钱银子着实可观,所以他白相起来,也就无往而不利。上海早年的交际花,或为名门闺秀,或为富家簉室,有艳丽的姿容,优雅的丰度,仪态大方而谈吐脱俗,她们祇是交游广阔,并非纯以色相炫人。最著名的有殷明珠、FF传文豪、SS王汉伦,相同的两个英文字母,显示她们身价之高,声誉之隆。其中如SS曾为比蝴蝶资格更老的影后,垂涎者如想得到她们的青睐,非财势绝伦,俨若王侯者莫办。但是,萨利以一名租界上的包打听,居然能赢得SS的芳心,不仅登堂入室,尚且长期姘居,供应她漫无止境的庞大开销祇此一端,也可以想知萨利在中国搜刮了多少。
一个月吃两万只洋俸禄,萨利拿的是暗盘中的暗盘,而巡捕房里公开的秘密,是总领事范尔迪每个月要收三十万元的「私人津贴」,范尔迪拿这一大笔陋规、贿赂、又分为明里、暗底两部份,暗底下的归他自己落腰包,至于他对远在法国的主管与相关人士,是否需要打点或分润,事实上无人得知,不过据范尔迪私下的解释,这一笔数达十八万的巨额款项并非由他一个子独吞。
另外明里的十二万元,对外当然还是暗盘,祇是捕房中人都晓得,十二万是总领事馆、公董局、会审公廨、巡捕房和其它相当单位的众家外快,但凡是高鼻子绿眼睛的法国人统统有份。祇不过分起钱来大有差等,分配的最高原则,是谁的职掌跟烟与赌有关,谁拿的钱就最多。
民国二十年的下半年,有那么一天,黄杜张三大亨又聚在一起,屏退左右,各人祇带亲信随从,──他们要商量机密大事
黄金荣先生打开话匣,他以消息灵通方面的姿态,告诉两位老把弟:
「我听说,范尔迪个老朋友最近身体不大好,已经向法国外交部请了两个月的病假,等不了几天,就要回巴黎去进医院了。」
「好极!」张啸林高兴的两手一拍:「他那一笔十八万块正好省省了,最近市面越来越不灵,燕子窠里香两筒的价钱,已经跌到了小洋一角,居然还有几家维持不下去,硬叫关了门。赌生意呢,除脱一八一号巡捕房规定下一注不许超过一百块钱市面差到这样,兄弟们出生入死,担惊受吓,各处赚到的铜钿,几乎全部送给外国人了,再这样,大家只有喝西北风。范尔迪请假两个月,我们省下这三十六万,多少可以调剂调剂。」
「这个──」杜月笙是最重面子的人,他难免有点迟疑「恐怕不太妥当吧!」
「有屁个不妥当!妈持个x,」张啸林顿时就反唇相讥:「人在人情在;范尔迪在黄浦滩一天,我们手底下的烟和赌,万一出了事情他该负责。现在他要回法国去,保镳的事体甩手不管,凭点啥?还要我们一个号头孝敬他十八万!」
黄金荣最怕得罪法国人,凡事宁可自己吃点亏,他根本不同意张大帅这个小儿科的办法,一声冷笑说:
「还有消息哩,连费沃里也要辞职回国养老了,是否连他代收的那十二万,也要一齐免了呢?」
张大帅听得出,黄老板话里的意思,分明是不赞成省十八万开销的办法故此拿费沃里经手的那十二万借题发挥;他对黄老板多少还有些忌惮,不敢直淌直的顶过去,于是他陪着笑脸说:
「那十二万当然还是照旧,因为这笔钱究竟不是费沃里一个人拿的,连这一笔也免了法国人跟前一只铜板不给,那他们怎肯善干罢休呢?」
杜月笙在自家弟兄面前,尽管可以从善如流,见风使舵,这里面没有什么难不难为情的问题。但是黄老板又在跟啸林哥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他来在中间便感到左右为难,因此,他很巧妙的想勾起一个打消张啸林意见的因头,他问黄金荣:
「金荣哥,范尔迪请假,费沃里辞职,总归要派代理的人吧!」
「当然要派代理的人。」黄金荣答说:
「代理总领事是从巴黎派来的,听说名字叫甘格林,代理费沃里的还没有决定。」
「那就更加不必送这十八万了。」张大帅振振有词的说:
「送人铜钿不是小事体,至少双方要有够得上的交情。这个甘格林,既然是从巴黎刚调来的,脾气为人还没有摸清,怎可以拿大笔的银两送给他,与其弄僵,我看不如不送!」
杜月笙问两个法国头脑走了以后,有没有代理的人,用意是相帮黄老板说话,同时这也是他自己内心里的想法,──既然有代理的人张啸林的「不管事体干拿钱」的说法,便可以不攻自破,但是他没有想到,张啸林正好利用他这一问,又添了他理直气壮的论据,听了他这不无是处的一说,黄金荣和杜月笙一致嗒然无语,──缄默等于承认张啸林获得了胜利。
法国朋友一一的
黄杜二人当时的默然,除了无词以应,还有一层最大的内在原因,那便是这两位大亨如今在法租界烟赌事业日薄崎嵫,又被张啸林敲响了丧钟的时候,早已意兴阑珊,不大起劲了。再干下去,固可聊资点缀,到手几个钱,供养一批人,果真从以洗手不干,对于黄杜个人而言,恐怕还是利多而害少。
首先,自民国十六年,迄至民国二十年为止,黄杜张三大亨顺便搞搞赌与烟,早已非同于民国七年以后,由他们自家当老板,大力经营,任意操纵,黄金白银,如长江大河般浩浩荡荡的滚来。就利益的观点言,辛勤劳瘁,冒险犯难,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过手财香,充其量,只能图个表面上的好看,并不能派上什么用场。
黄老板既已家财百万,一心悄然归隐,颐养天年,他犯不上为这戋戋之数来伤脑筋,卖交情,凭添许多麻烦。杜月笙呢,他正多方面的着手,向金融工商业进军,他藉由平抑工潮,调解劳资纠纷,使他在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结交了不少朋友,掌握了大量群众,展望前途,光芒万丈。事实上,他比黄老板更犯不上劳神操心,分润这区区的财香。
另一方面,在他左右,阵容坚强,目光远大的智囊团,参谋长,包括陈群,刘志陆,杨志雄,杨管北,陆京士等人,没有一个不在明劝暗讽,请他早早于此一永远不见天日的行当,脱离关系,一刀两断,以便另起炉灶,鸿图大展
尤有甚者,民国十七年蒋总司令复职,北代全面完成,国民政府业已定订长期根绝烟毒的计划,第一步,采取寓禁于征的和缓步骤,将各地鸦片烟的买卖,化私为公,纳入控制之下。由于中央的表现决心至为坚强,各省各县禁烟局,禁烟处普遍设立,禁烟宣传热烈展开,报章杂志,医师戒烟的广告如雨后春笋,形成当时最热门的生意。益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甚嚣尘上,大批的工人学生群众还演为实际行动,跟外国「统治者」不断发生冲突。在民族觉醒的巨浪冲激之下,杜月笙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各地的租界必将收回。─当罪恶的温床根本铲除,烟和赌,又将皮之不存,而毛将焉附?
因此,杜月笙确实是本着他的良知良能,痛下决心,要跟烟赌事业绝缘,进而连根斩断,全面脱离的。他既然在内心中有了这样的决定,虽然看得出来张啸林的意见,无疑自掘烟赌两业的坟墓,他也就──算了吧,乐得促其竟功
范尔迪因为是抱病回国治疗,行前,杜月笙和他见过面,谈过天;濒行,他更曾登轮相送,祇不过,范尔迪精神体力不济,一对异国友人未能深谈,只有依依不舍,互道珍重而别。
费沃里,这位法租界的老总巡,可就不同了,他常说:在中国一住一二十年所交到的好朋友,唯有一个杜月笙。而这一次,他是告老退休,回到他的祖国去乐享天年,他临走的
时候,曾经和杜月笙几度盘桓,几度密谈,他更向杜月笙提出不少意见。
对于杜月笙近年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工商事业方面的全盘锐进,长足发展,费沃里并非毫无所闻,但是,他自认为和杜月生过从、共事多年,相交之深,遂而知之甚稔,在他的心目中,彷佛杜月笙一生一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