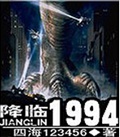密查1938-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朝上数,就应是蒋鼎文一环,只有他能顺当指挥徐、刘任意一环。原本想直接连到军统或者中统,却怎么也跳不过他。就算他护犊,想要保住爱将,但密裁宣侠父不是普通事件,作为老江湖必定知道其巨大影响,肯定和胡宗南一样以抽手为要,可以为人绝不会舍己为人。
密裁指令基本可以肯定不是两统发出,他们根本指挥不了蒋鼎文。假设真是两统贼喊捉贼,但捉贼人必定不选自己。一个暂时脱离了特务机构的人,一个很难控制的人,就算葛寿芝起作用也不行。丁一操作制造的宣侠父押送途中脱逃事件,原本是最好的结果,一手托数家,正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不敢公布,白忙一场。
蒋鼎文是密裁令的源头,几乎也不可能,就算他不怕共产党诘难,却不敢自作主张,他是被驯服的猛虎。能密令大蒋的只有老蒋,他是驯兽师,挑了威风不复当年却更听鞭响的蒋鼎文,没选尚存野性的胡宗南。密裁宣侠父不是好差使,胡宗南还有可能网开一面,也许正是蒋介石的另一种惜爱。
整个链条都理顺了,蒋鼎文的各种表现也趋于合理,保下、自保还要保上,夹在中间十分难受。蒋介石支持密查的态度,符合他的一贯手腕,喜做过分之事,喜看手下争斗,然后坐观虎斗坐收渔利。这正应了组织的要求,要把责任追究到最高,找到震中才罢休。武伯英也明白,所有一切推理都只是推理,需要铁证来办成铁案,不然还是白忙一场。
武伯英想不下去了,也坐不下去了,起身下了黄楼,开车出了新城大院。刚出大门,路边停着的一辆轿车,打火跟在了后面,上任以来第一次被人明目张胆跟踪。对手似乎也意识到了,宣案密查到了最后关头,揭开一切和掩盖一切,好坏分定就在几日之内。武伯英把车开到侦缉大队院门前,停车、下车、锁车,自然而然。跟踪车紧挨巴克车尾靠边停车,根本不怕被发现。武伯英懒得看,走到门口向自卫哨报了身份,目不斜视走了进去。
师应山放心之余只关心所揪心的:“能和刘天章扯上不?就是扯不上,也要把他扯上。”
武伯英知他报仇心切,劝慰道:“他必定难辞其咎,但是要他死,不太可能。”
“我就是光想让他死!”师应山很冲动。
“那你和师孟的关系也就暴露了,而且暴露的,还有你年轻时的冲动。师孔这个名字一叫人知道,很容易就能查出你多年前在陕北的事。陕北,陕北,现在代表忌讳。那你跟着就被打倒在地,翻不起身来,更别提报仇了。”武伯英不知他仍是中共秘密党员,还拿这话来吓唬。
师应山亦不知他的秘密身份,觉得这个老特务掌握了太多秘密,来源渠道根本就想象不出,只能莫名害怕。“那时国共是合作的,打倒军阀。现时国共也是合作的,抗击日本。我从来就没投靠过共产党,年轻时也没有。”
武伯英点头道:“因为我弟弟曾经是共产党,我一直被怀疑。要是你们兄弟的关系被挑明,必遭怀疑。从此你就背上了包袱,一个再也卸不下的包袱。”
师应山点了下头,长叹一声:“咱俩有一样的苦痛,说不出来的苦痛。”
“报仇有几种,实际死不是最好的一种。我一定会让刘天章,把这些年的力气白费了。西安待不下去,调往他处当个喽啰,而且没有再被重用的机会。年轻力壮就开始养老,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比死还难受。”
“你向齐北报仇,就是这个方法,还借机把胡汉良也整下了台。”
武伯英知他反过来用话禁话,威胁让交谈继续不下去,各自无言想心事。隔了一会儿,武伯英转变了话题:“老师,我来你这里途中,被人跟踪了,一直跟到你门口,现在还在。”
师应山非常聪明,立刻明白他要什么,安排手下去门口查看。隔了一会儿,手下回来报告,跟踪人正是升任了军统陕西站行动科长的丁一。“我到车边打招呼,丁科长狂妄得很,说受蒋主任委派,秘密保护武专员。”
武伯英不禁苦笑了起来。“这帖膏药,贴上我了。”
师应山等手下出去了,才感慨说:“我不清楚,密裁宣侠父,是怎样一个过程,是怎样一个授权,是怎样一个行动。但能感觉出来,蒋主任想要保护的人太多了。他羽翼大,所以就劳累。把犯案的、办案的,都想包住,操碎了心。”
武伯英看着窗外不屑笑笑,低眼看看腕表:“也好,让丁一他们,在门口保护着,咱们吃午饭。”
师应山憨笑点头:“不行叫进来一起吃,辛苦得和啥一样。”
糟蹋话说完,二人大笑起来。吃饭时武伯英不顾进餐场合,打听最近城中有无地方传出尸臭。师应山没有这类消息,知道他还在挂念着尸体,估计了一种可能,宣侠父也许并没死。武伯英比他知道得多很多,清楚宣侠父被丁一带走,必死无疑。
饭后略微休息,武伯英就回了黄楼,丁一自然紧跟其后,把车停在了新城大院外头。武伯英把车停在楼下,朝大门外看了两眼,天色阴得更重,空气中充斥着白色的水汽。他竭力压制对丁一的仇恨,王立虽是张向东下了杀心,虽是洪老五捅死的,却是他带到武宅的,就是元凶。从宣侠父起死的六个人,除了洪富娃、师孟是刘天章一手整死,都和丁一有关。估计正是他授意,洪老五才杀红了眼,接连伤了林组长、何金玉、王立三命。张向东之死,虽然没有明确,但必定和丁一有牵连。而宣侠父一命,应是他亲手所取,要不然怎么能拿到金表金表链。他的凶狠手段,就连当年胡汉良也逊色一分,最可怕的是年纪轻轻,已如此歹毒,恐怕再发展几年,将会成为西安城最大的毒蝎子。
武伯英打了一个寒战,如果丁一狗急跳墙,到揪出时必定什么都能做出来。必须为安全计,起码在侯文选大闹武汉消息传来之前,不能再涉险。如果自身有差池,前面努力全部白费,就算蒋鼎文背上骂名,宣案也会不了了之。人身不存,给死人报仇,给组织复命,都无从谈起。自己不畏艰难不怕险阻,但不能不留在最后,把那根隐秘链条公诸于世。给同志亲人报仇事大,却大不过组织使命,唯一解决之人,舍我其谁?
武伯英上了办公楼,赵庸他们四个已被罗子春叫了回来。破反专署又坐在一起开会,赵庸汇报几天的监视情况,没发现军统朝外运东西,倒发现了其他一些秘密,无关紧要。整个短会期间,罗子春心不在焉,不时轻叹一声,武伯英一看他,就连忙掩饰,但是盖不住纠结与忧郁。
武伯英最后开口:“我昨天已经给胡总指挥汇报过了。鉴于目前密查宣案没有进展,我的前途未卜,为了你们四人的前途,决定仍回十七军团效力。”
赵庸等参案以来,确实感到麻烦,加之不受重用,只被当做武力工具,颇为思念军旅生活。几天连着蹲守城墙一无所获,丧气的感觉越发强烈,觉得实属应当。
武伯英把每个人看了一遍:“四位跟我相处时间不长,情谊却不浅薄,以后要用得着武某,还请不吝招呼,一定帮忙。只是军地相隔,难以为诸位出力,只好借着和胡总指挥交好,给你们提了一职。以诸位的能力,在普通连队干连长绰绰有余,再说借调我的破反专署一月,回去没有个动静,难免被人说没有成绩。胡总指挥已经交代一军,给你们每人,安排一个连长的位子,只不过这样一来,今后你们就被分开了。尽管分开了,还在一个部队,因着破反专署这段经历,也要多多团结。”
话没说完四人已变得非常激动,面露感动连连答应,分别起身给他敬了军礼。武伯英不便还礼,坐着不动只是摆手微笑。“好了,你们现在去行营总务处,领取九月的薪水。然后我和骡子,送你们回去,顺道感谢胡总指挥,在专署成立之初,派了干将支持我的工作。”
四人又行一遍军礼,武伯英笑得脸皮都有些抽搐,起身送出了会议室。四个军棍去了总务处,武伯英回来重新坐下,对罗子春交代:“借着送他们,咱俩也在胡那边住两天。今天丁一跟我,跟得很紧,不能不小心。”
罗子春不太相信:“他不敢吧?”
“怎么不敢,要保他自己,杀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侯文选虽然听我安排,但是那人太不可靠,谁知道他们现在掌握了什么。再一个他去武汉,能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也说不来。”
罗子春同意他的看法,却不太同意他的安排:“我就不去了,估计他不会对我下手。我留下,白天在黄楼,看着咱这一片地方。晚上回宅子,看着咱那一片地方。”
武伯英看了一会儿,理解他的心情,还是放不下玲子。想留一点自由,等候未婚妻的消息,在岳父母那里走动,于是就同意了。
四人领薪水回来,还代领了武、罗两人的。武伯英开着车,跟在吉普车后面,一起去了小雁塔司令部。丁一的汽车,不远不近跟在后面,就像夜间乡路上的野狼,只等行人懈怠。天气更加阴沉,光线如同傍晚,似乎衣服表面都凝结了细小水珠,潮乎乎的。到了十七军团司令部,胡宗南正利用部队休整时间召开军事会议,副官悄声报告,他让一个张姓团长出来,安顿四个归队手下。副官陪着武伯英等候散会,说东道西,会议迟迟不散,一直开到晚饭前。
胡宗南一回办公室,就问武伯英:“为什么不要他们了,用起来不顺手吗?”
武伯英站起来答话:“主要的,还是我昨晚吃饭,给您汇报的原因,为了他们的前途,都年轻,不能拖累。”
胡宗南坐下来:“你总是,谦虚过分,担心过度。”
武伯英又坐回了椅子,今天事态发展超出了预计,必须提前给胡宗南透露一些秘密。他坦诚说了担心,害怕跟踪的丁一下手,想要在胡羽翼下躲避。接着把昨夜没报告的诸事也说了出来,包括侯文选已经供认丁一,假逃真走去武汉找戴笠告状。胡宗南眯眼听着,逐渐有点不高兴,旋即明白他的苦衷,不用致歉又恢复常态,原谅了隐瞒。
武伯英真诚道:“我不是想瞒总指挥,只是害怕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一想,我和您都是竭诚为总裁办事,倒是没什么可怕的。目前能保护我的,在武汉在重庆,都离得太远,西安城里就您有这能力。原本我担心把一切告诉,您会惧难而不伸援手。今天总算明白,只有把一切说明,您才会不畏难而庇护我。”
胡宗南冷笑一声:“巧言令色,我是投笔从戎的文人,不用你绕那么多弯子。”
武伯英讪笑点头:“所以总指挥比起其他军人,不光是勇武,而是勇决。”
胡宗南没听他谄媚,回敬似的神秘道:“我也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是戴笠同志告诉我的。”
“什么?”武伯英疑问道,和戴笠有关系的一定是大秘密。
胡宗南故意卖关子,先不回答,拿电话要蒋鼎文办公室,接电话的是勤务兵,说主任已经回家休息。武伯英见他打电话给蒋鼎文,不由紧张起来,真有些怕他出卖自己。胡宗南故意要让他害怕,又让总机把电话转到蒋公馆,终于找到了蒋鼎文。两个大员通了几句话,武伯英才稍稍放下心来,胡宗南的话已经完全接受了他的求救。胡宗南编的理由很巧妙,让人佩服,他说前天武陪自己去渭南视察,看了不少东西,而且文笔之好在政界闻名,想借用几天起草陕东防御报告,向蒋总裁上报。蒋鼎文犹豫片刻就答应了,并说自己愿意放武给胡使用,若要长远最好由胡给军政部打招呼,换掉专员人选。胡宗南解释只是暂时借用,容后再和戴笠等人商议,正式调他到己处供职。
武伯英揪心刚才所说的秘密,等他一放下电话,接着问:“什么秘密?”
胡宗南冷笑着转而言他:“这样吧,你在我司令部待着不方便,这几天你就住在公馆,戒备也很严密,非常安全。”
武伯英还是追问不放:“总指挥,什么秘密?”
胡宗南拍拍椅子扶手,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最关心这个,看你急切的样子。实际也不是秘密,干脆告诉你吧,免得你忐忑。一个星期多以前,我和戴笠同志在武汉会面,商讨一些事情。谈起了宣侠父失踪案,也谈起了你,他突然说宣案的指使人,他已经知道了。”
武伯英不啻听见惊雷:“谁指使?”
胡宗南收住笑:“他没说,为了避嫌,我也没问。既然他都知道了,总裁一定也知道了,或者说总裁先知道了,他才知道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停止你的调查。他说现在骑虎难下,不让你调查,责任就全成了他的。要是纯粹由他指派你,也就叫停了,但起用你和徐恩曾同志也有关系,他不好下令。”
武伯英眯起眼睛,看了胡宗南很久,想了很多,推测很多。胡宗南也看着他,等他的反应,等来的却只是对命运的感叹。“唉,我也是骑虎难下,等人叫停,却一直等不到。不有个结果,责任就会全压在我身上,所以必须走到尽头。”
武伯英躺在胡公馆客床上难以入眠,几个新出的状况,让思考更加凝滞艰涩。他们在无声较量,自己必须智勇相济,才能找到解决的最佳点位。自己就像一个扶夯人,木杆上拴满了绳索,人多力量大,轻易就能拽起石夯。但是每根绳索,想要落下的方向不同,就算几根绳子方向大体一致,但想要落下的地点,却没一个重复。而扶夯的又是哑巴,不能喊号子,只能平衡各个方向的力量,把夯头落在最理想的点上。可想而知这有多么艰难,而且那个最佳点尚不明朗,暂时没有合适位置。但石夯已被提起,很快就要落下,必须在须臾之间,引导石夯砸向那个点位。这样一来,就需要借力打力,制力助力,稍有差错就砸了脚面。
武伯英看看英纳格手表,已经下午两点了,却还是睡意全无。看见手表就想起了蒋宝珍,觉得按照脾气,就算对手有挟持玲子之意,蒋宝珍也决不会做出挟持之事。再想想又不一定,万一蒋鼎文真是幕后主使,她顾及亲情做了此事,一下子就掐住了罗子春的七寸。而罗子春知道的秘密,和自己掌握的差不多相当,更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