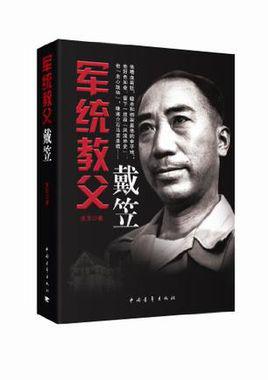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唐纵每周也至少去一趟罗家湾,但办事的风格与老郑大相径庭,凡是过问的事,都要认真研究推敲,说出自己的见解,时时令毛人凤心生佩服。为此,凡是戴笠或自己形成意见的文件,毛一般不让唐纵过目。有些比较难办或是还没有形成意见的材料,就主动地就教于唐纵,落得个公私两利。
郑介民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粗俗有余;唐纵清癯白净,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一派斯文相,两人比之戴笠的悍狠猖狂,毛人凤的隐忍深沉,别具风格。有些喜好评头论足的处长、主任们,私下里议论,说罗家湾里四个头儿,酷肖动物:“老板”肖狗;郑长官肖猪;唐帮办肖白狐狸;毛人凤肖乌龟。
说毛人凤肖乌龟,不乏影射毛夫人向影心招蜂引蝶、让老公戴“绿帽子”等艳闻的含义。但更具想象力的,恐怕还是这段时期他以“柔软”之体,负重在肩的形象。
先说负重在肩。抗战后期,戴笠兼职越来越多,不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长,替戴笠看家的重任,便无可推卸地落到了毛人凤身上。与此相应,权力也伴随着责任的加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42年搞成上海实验区试点并予以推广建立实验区制度以来,整个军统外勤工作的线头,事实上已绝对地捏在了戴笠及其代理人毛人凤的手中。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比方说经理处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尊,已超过了校长对于国父。
总之,乌龟匐匍,重负在肩,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到1946年春戴笠飞机失事,前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毛人凤事实上是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鼎力反共
作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毛人凤除了“内当家”的把持以外,还有哪些成就呢?专门的记载十分有限。这一时期,毛人凤毕竟是个隔着帘子的人物,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然而,结合军统局的主要职能去认真地梳理,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军统局作为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始终是反共的重要工具。抗战初期,民族矛盾曾使侦敌除奸的职能有所突出,但攘外与安内的两手,却没有此起彼落,不同的只是后者更为隐蔽而已。后来(毛人凤荣任“毛座”之际),形势(与抗战初期比)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开始发动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为标志,公然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和人民军队称之为“奸党”、“奸军”和“新式割据”。与此同时,几十万“国军”沿陇海铁路、成榆公路、西兰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一场新的封锁围剿已呈剑拔弩张之态。这时,代替戴笠坐镇罗家湾的毛人凤,深知军统在这方面必须作出的特殊贡献,于是秉承“老板”的遥控指示,鼎助反共,干得颇有声色。
首先,从思想上对属下的数万特工加以控制是第一要务。过去,戴记特工系统以《家风》为主要读物,书报费用的支出预算很少。这一回,毛人凤决定来个突破,动用卡车运输,买下大批的《中国之命运》,基本做到了全体内外勤人员人手一册。与此同时,还在《家风》上,在“总理纪念周”的训话中,广造声势,务求大家加深体会,明确“反共优先”的道理。
其次,在组织与人事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与安排。那位屡闹绯闻、名声不佳的叶翔之,从党政科长的位置上拔擢为局本部第二处的副处长,外兼何应钦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秘书长,集中负责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与此同时,毛人凤还一改局本部不直接指挥基层的惯例,专门成立了两个直辖小组,一个设在重庆水巷子1号,由少将倪超凡任侦察组长,主要任务是对付诸如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之类的中共组织;另一个是名义上附属于重庆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专门对付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商务代表团和塔斯社。
在毛人凤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驻重庆的所有机关,几乎都受到了监视,所有以公开名义活动的中共及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全都被暗中跟踪。毛处事精细,深恐会出现百密一疏的不慎,又特地从第四处抽调出许多业务尖子,在各中共机关的住所附近架设侦收台,抄录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当时,有些职员对这种兴师动众的作法不理解,认为会大大削弱对日伪方面的工作。意见传到毛人凤耳朵里,这位从不在“总理纪念周”上公开训话的“毛座”,竞破天荒地亮了一次相,指责这些人是“头脑糊涂”,没有领会“领袖”著作的真义,不懂得与“奸党”、“奸军”的斗争甚至比抗日更重要!或许是偶尔为之,毛人凤的“精神训话”给特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反共职能的突出,军统局控制的各个机构对中共方面的斗争也逐步从欲盖弥彰的秘密方式转向公开化。以交通检查处为例,过去的重点是检查“资敌(日伪)”,现在转向“通共”。比如去西北的公路上设立青木关检查所,就是专门针对延安的。举凡有投奔进步的青年去延安,他们就竭力阻挠;举凡有从延安出来办事的,他们就百般刁难,制造摩擦,甚至弄点恶作剧也好。有一次,延安方面几个十八集团军的将领通过青木关,适逢大雨,小特务们硬要对方下车接受检查,几位将领被淋得周身湿透。类似这种“小儿科”的下作行为,传到戴笠、毛人凤那里,竟被当作笑料,在他们的怂恿下,特务们愈发猖狂。
不过,大手笔还是落在一个“反”字上,其中往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从事侦伺和破坏工作,毛人凤就干得十分积极。他利用交通检查处的网络,把许多带有介绍信和证件去延安的人扣下来,让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同时,再把扣下来的青年人,分批送进特训班,经过毒化教育后,挑选表现“好”的,派往延安卧底。有时,一些经受不起艰苦生活考验的青年人,从延安跑出来,军统的交检关卡截住后,千方百计地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边区的情况,强迫他们说出进入边区的方法。此外,还利用通商、通邮、宗教等渠道,渗入边区,手法之多真称得上是费尽心机,无孔不入。当时,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有力地抨击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种卑劣行径,他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个“处心积虑,百计并施”,按在毛人风头上,毫不为过。
暗杀,历来是军统机关实施特殊任务的手段之一,也是戴笠被外界视为魔头的重要原因。从1943年开始,毛人凤襄助戴笠,成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于暗杀的勾当染指日深,且主要对象大多是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沈醉有段回忆,可资佐证——“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间休息。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乎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个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谁能具体说明呢?当然是戴笠和毛人凤自己。戴笠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去对付共产党。”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曲线救国
蒋介石全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