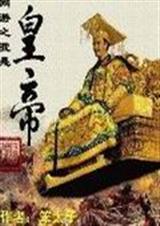中国皇帝全传-第2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三、锐意维新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扶持顽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绪的手段就软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惶惶,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一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产生加紧实施以推进改革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