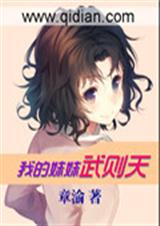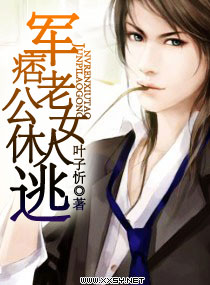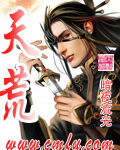������--Ů��֮·-��3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23������ʶΪ�ȵ�����ҩ�ŵĸ��ڻʵ�����10�������ô��ȥ�ˡ�������ˮ�����겻�٣�����������ɱ���ı���С���ˣ��Ѿ���Ϊ���Ƶ۹������Ļʺ��ڻ�������ȴ������Ⱦ�Ű���ɫѪ���ĺ����һ·��ɱ��������Ϊ���յ�ʤ���ߣ�ֻ��Ů�˵��ഺ���Dz����ٻ����ˡ�������Ӧ�����㣬��Ϊ����õ��ģ����Ѿ��õ��ˡ�Ȼ������Ȼ��������ʹ���ɹ��Ĵ���������˸߰�����Ȼʤ�����֣�Ҳ��Ȼ�����ſ�ɬ������4λ���ӵ�ĸ�ף������Ǵ��Ƶ۹��Ĵ�����Ȼ����Ȼ������������������������һ��Ů����С����������ʱ����С����֮������������ʮ�ꡣ
����������á���δ��������ز����ŮӤ��������ĵ������ǵ���ʹ������ΪС�����ոճ������Ȼ������û�����ü����������������κ�һ�㲻�㣬���������������������ϵĺ�λ����СС��Ӥ����Ҳ����ĸ�����ﶨ��Ϊ���������������µ����Ŷ����������㡣���������������˲�ֹ��һ����Ȼ��ֻ��С�������ſ��Զ�ռĸ��ȫ��������ͻںޡ��������£���ΪС����������¡�ص�Ǩ����ʽ���ɽ��еĵ�ҵ��Ǩ����ȸ�Ŷ��ij羴�£�����Ϊ���չ˸��ڵIJ��飬��ȥ��������Ѻ���һ���ƾӶ��ڣ��ѵ���С�����������һ��������������������ʽ��Ϊ������������Ϊ˼�������ַ�����ǰ��Ի˼��������ص��ֺţ�������ĸ���������黳�����������ӵ�֪�����������������������֮�����������Ѹ��ܵ��ʺ��˼Ů֮�顣�������顷���Լ���һ�ʣ�
��î����Ů�ⰲ����������Ի˼����±���Ĵ����������룬��������֮�ƣ��ڵ�ҵ��Ǩ�ڳ羴�¡�
����ר���ᵽ�dz�Ů����Լ��ʱ���д�Ů�����Ǵ���������̫ƽ������ʷ����û������̫ƽ�����ij������£�������¡���꣨��Ԫ681�꣩��Ѧ�ܣ���������14��15��Ļ��䡣�����˷�������������ף���ôһ���������Ԫ������̫ƽ�����Ǻ��п��ܵġ�ʧȥһ��Ů�����ֵû�һ��Ů������������������������Ҳ��Բ���������֪������ô��ģ������˰������������������õ�����������ʼ�ύһ���й�����ĵ�ʿ��Ƶ���ش���������У���̳���������±��¹�����ʤ�淢�������ֲ��������ľ�����������ʤ��
��ʤ����ʮ����������Ӳ�ĺ�̨�ⶥñ��ѹ����Ҳ�������ɣ����ʺ������Ϊ������������˺�λ��������ܲ�֪��Ȼ�������DZ����ܸ棬��һ����ʿ�н���������Ҳ���������Ա�������Ը��ǿ����־��������ʯ�������������������������ʵ�ֶ����������Dz�����ţ�������������²ߣ������ڳ���Ȼ�������������Ե�ʱ����λ���ȹ̣���ʲô������������������ð�������أ�̨��ѧ��������Ϊ�������ʤ�Ķ������Ǹ��ڣ�ֻ��ʱ����Ȩ����ȫ�����ԡ����ڸ��ڣ��������᱿���Լ�˺�ٳ��ڷ�Ʊ����������Ϊ�������dz��ں����ʺ�ͬ����ԭ�����Լ�����У�Ҳ�������Ľ���ֶŮ��
���Ľ�㺫�����ˣ�һֱ������Ⱦ�����������������ֶΣ��Dz����ܺ��κ�һ���˷����ɷ�ģ����ǽ��Ͼ��ǽ�㡣����һ������Ϊ���ܹ���ĸ�ֵܵı�������ݱϾ��е㲻ͬ���������˵��ɷ����Խʯ��Ҳ����������幫�š�������ʱ�ո�����ս���ԺյĺӼ�����Т����Ҳ��һ��Ů�����˺����ҡ�����Խʯ�����������������ĹѸ���������������һ��Ư���ó���Ķ�Ů�����Ӻ�����֮��Ϊ�����dz����������꣬Ů��������Ҳ����������գ�ʷ�ء��й�ɫ���������Ѹ�������������Ů�����빬Է˽����ڣ��������ˣ����ڵ��۾�����Ȼ��Ȼ�ش�ĸ������ת����������ͤͤ��������Ů������θ�ںܺõ�һ��Ц�ɣ���СֶŮ��С����Ϊκ�����ˡ��������ֵ���һ���ʸ��������������˲��þ���ʧ�ˣ���ʲôʱ��ʲôԭ�����ģ�ʷ���ϲ鲻������ļ��أ����һֱ�����DZ�������ģ������ѵõ�֤ʵ��Ψһ����֪������κ�����˶�������ȷ���е��⡣���ڶ������С���˴����Ķ����ģ����㽫����ʽ��Ϊ����������ֱ�����о���֮һ��ֻ�ǰ���κ�����˱Ͼ��ǻʺ������Ů�����ڻ�����ԥ��ο��ڡ��������������Ů��Ϊ�ڼɣ���������Ϊ����ܾ��������ʿ�빬��ʤ��ԭ��
������Ϊ���ֿ����Բ���������Ȼ����ò�����������ֶθ������ȼ�ֱ����һ������ģ��ο����������ĸ�����µ������ʺ�Ҫ�Ը�κ�����˻�����С��һ�����α�ð���д���ʤ֮������Ҫ��ʿ�������ܰ��ģ����Ƿ����ڰ�������Ǩ��ã����п��������ʺ���������Ĺ���Ϊ�����������İ��ɣ�˵����ʿ���������Ҳ��ʶ�����˺�Ϊ���������������������ӱ����£��������������������ں���������Ũ��ʱ�������ɹ���������ʵۻʺ�̩ɽ���룬Ϊ�ۺ�����е�������������һ��˫ʯ������ԧ�첢�ܵ�����ʯ�����������������̩ɽԧ�챮�ˡ����Ԫ�꣬�������ų�ɢ����ﶼξ��ɢְ����ְ�ڶ�������ʱΪ�����ಡ��̫�Ӻ��ҩ�ﲡ����˹����������в��Dz���ԭ�£�������һʱ����һʱ�������»��ڲ࣬�������帮���¶�������в������ӵ�����ʤ���ܱ�֮��Ȼ��ŭ�����̴��������Ϲ����빬���飬����Ľ��������Ҫ�Ϻ�
������������
��1�����ٴ���������Ĺ־����
��2����ȫ����*�����گ��
��3����������*����������
����ʼΪ����ة�ฮǧţ����̫��ʱ�����ԣ������Ծɳ����Ե����ټ�Ϊ��ʷ�������Ǩ˾Ԫ̫������ʱ������Դֱ��Ϊ����䣬�����Ϊ˾��̫�������Ϲ���Ϊ��̨�̼����´���Ϊ̫�����л�����ʮ���ˣ��Ե�������ʾ������ȣ��Զ���л��
��4������������*���帮������
����֪����ʧ�����ݽ��帮�ƣ������䃺�ӡ�Ů���Բ��������������������Ϊ���ڸ���δ�����ԣ���ɽ��ã�������ˡ����帮��Ȼ��ɫ������������Ի����˭����µ��ˣ�����Ի�������������ǣ������������ӵ�Ү�����帮��Ȼ���ⲻ���̣�������ȥ����ע����Ȼ��ָЦ�����ӡ���
��5��������ͨ������201Ǭ��Ԫ�꣺
�����ʹ�Ϊ�����У����������£����帮Թ֮����Ϊ���ݴ�ʷ�����ְټã��ʹ쵱����������ʱδ���У��帮��֮�����ʧ���������������ڣ��������ʷԬ��ʽ����֮���帮ν��ʽԻ�������ܰ��£������١�����ʽ����ν�ʹ�Ի�������볯͢����Ϊ��������Ϊ�ơ����ʹ�Ի�����ʹ쵱�ٲ�ְ�����г��̣����Է���֮��������������ʹ���������Կ���ˣ�����δ�ʣ����˾������š���ʽ���У����Գ����������ϣ��帮������Ի������ն�ʹ죬����л���ա�������Դֱ��Ի�������籩�𣬷����������������������������´Ӿ���Ч���帮�ַ�����Ըʹ��֮����Ը����ɱ��
���Ԫ��ķϺ��¼�����������Ϊ�������Ȩ��ʢ���������ڲ���֮�ʡ�������־��ר����������������Ϊ����Ϊ�����ƣ��ϲ�ʤ��ޡ�����ͨ������˲����Ϻ�֮�����ʤ�ĸ淢ֻ������һ�������߶��ѡ��Ϲ��ǰ��ո���֮����ּ�����뱻���֪̽�Ϲ���һ�֣�����Ϊ�˺����ſ��ı�����ĵij������������Ϲ��������������Ȼ�����ʷ����֮ǰ��û�����רȨŪ��ѹ�Ƹ��ڵļ��أ��ʽ������������ɴ��£���Ϊ���ܵ�ȷ���Ϲ�����Ū�����������顷����һ��Ϊ�����ԭ���طϺ��£�ֻ˵�Ϲ��DZ������ڹ���ɱͷ�����������顷��ͨ�����������Ϲ�����������Ϻ�
�ϴ�ŭ�������������ɡ�ͬ����̨��Ʒ�Ϲ�����֮�������ԣ����ʺ�ר�������������룬���֮������������ΪȻ�������Dz�گ��
��Ϊͨ�����Ԫ�����������������֮���ƣ���˵��Դ�������˱ʼǡ�����������ձ鱻��Ϊ�����Լ��ߡ������߾�δ�Լ��������Ϲ����빬ʱ���зϺ��⣬����ʤ֮˵Ҳ��Ϊ���Σ���ǰ�����������ʱ�ĵ�λʵ��û�б�Ҫ�����ĸ��ˣ�����ֻ���������Ŷ��ѣ����Ϲ��ǵ�������Ҳ���Կ������ڲ���������ԭ���ǡ��ʺ�ר��������ô��ʤ�ܿ��ܾ��������ʺ�����Ī���е������ˡ����淢���Ļ¹�����ʤ���Ϲ���Ҳ��ȷ�Ǿ�ʶ�����Ƕ�����ְ���������з�̫���ҡ�
�����������������������������г������ɵ�֮����Ϊ���ں��������ì�ܣ���ֻ���ڷ���֮��IJ�������Ħ��������ϣ���Ϻ�����������Ϲ��ǡ�������˷������࣬���ܸ������أ�Ϊ�ˡ��Ѳ����ơ���������һ���Ĺ����γ��ˡ����ֹ������ľ��档�Ϲ��������ٳ߸�ͷ������һ�����Ʊ�Ҫ�㵹�ϳ������ڣ��������ڵ�ǿӲ��̨��������ˡ���������Ϊ�����Ԫ��ķϺ��¼������Ϲ��ǻ����㾡ȴ��������������Ľ������Ү��Ү���Ǿ��б�Ҫ�˽�һ���Ϲ��ǵı�����Ϊ���ˡ�
�Ϲ������ƴ���������ֵ��һ�������������������������������ĵ����ԡ����Ϲ��ǿ�ʼ���ƴ��������ķ��ŵ�ʿ������ʿ�ʼ���Σ����ʱ��ֻ��ʵЧ��ʵ�����˲�������ʷ��̨���ƴ�������;����ͨ������Ϳƾ٣��������Ƽ�λͳ���ߵĴ����ᳫ���ƾٳ�ʿ��Ȼ��Ϊ�������صij�����δ�пƾٹ�����Ȼ��������Ϊ�������Ϲ��DZ��ǿƾٳ���ʱѡ�γ����ľ�Ӣ��������Ĺ��飬�IJɱ����������й�֮����������������ʫ���й���ѧʷ��Ҳ��һϯ֮�أ����粴����ģ��ųơ��Ϲ��塱���ƴ�ȡʿ������Ʒò��ȣ����ǵ�ָ��ò������ָ��ֹ�����źʹ����ķ緶���Ϲ��ǵķ�ȣ���˵�ǿ�����������ף�ƮȻ���������ݵġ�ʱ���³�ƽ���Ϲ��ǹ�Ϊ�������࣬�ٹ�֮�ף����賿�볯��Ѳ��ˮ�̣���������һ�ס��볯��̲��¡����������㴨�������������ޡ�ȵ��ɽ�������Ұ�����ʫ��Ӻ���ŵ����������ʣ�����ˮ������ʾ�ʵ۶��Լ������Σ���ȵ�ɱ�ϲ��������̫ƽ������¶���Լ��ж������������ִ�����������ǡ����ij����е����Ϲ�������ƮƮ��üĿ���ʣ�ֱ���������ɣ������˷��ȥ��һ��ͬ�Ŷ����ô��ˣ�����֮�������ɡ�����6�������պ��㵹��Ұ�IJ�Ů�Ϲ�������ϣ���ϡ��������Ϲ��ǵ���ķ��ˡ����Գ�Ϊ��ѧ��������Σ�����Ӧ������ѧ���꣩����������������û��˿���ĵֿ��������Խ������Ϊ��̨�̼���һ·����ֱ�϶����࣬������������������빬����ר��ھ�������Ǽ�������֮��Ψһһλ�������ٵĴ��������Ͽ����Ϲ��ǿ�ν���ڵ��ĸ������Ը��Ͽ���Ҳ�ǵ��͵������Ը����Ѳ����ƣ�Ϊ�������������������Ļ�������Ͻ�����Ϊ���һ���ʱ�䣬˵�����������ݺ������Щ����˼�顣���ڵ��Ը��г嶯��һ�棬ǰ���������߾���������֤����������Ϸ������꣬�Ѿ�ʧȥ���ʸУ�����Լ�����Ҳ���õ�λ�ȹ̣�����������ǰ��ô��������ʱ���������£�����̫�࣬�����ø��ڸо����졣�쳤�վã���Թ���ͻȻ�������������зϺ�֮�⡣�Ϲ��ǵ�Ȼ��֮���ã������������⣬���ʺ�ר�������ƣ��˻���ӳ���ۣ������������������Խ���ᶨ�������Ϲ��Dz�گ�������������ɣ�����������ޣ�Ҳ���������߳���֮�����ο��ʺ�ķ��������ʱ��û�з����ʡ����ӵȹ�ʧ������û�б���ץס�ѱ��Ĺ�ʧ�����ԾͰ��е�ʿ�빬�����ʤ���Դ���Ϊ�Ϻ�Ľ�ڰɡ�
�����Ĺؼ�ʱ�̣������֯�ĺ��鱨����һ�ξ������������������������ʺ�����������ߵ��ˣ�Ϊ������ռ���Ϣ�������ڸ�������Ҳû�ٰ������֣��������顷�á����ұ������˵�������ߵĸ�ЧѸ�ݡ�����Ȼ����Ѱ��Ů�������ͻ����������֮�֣���û���˷�̫���ʱ����ԥ���DZ�����������ȷ��ѡ����������ȥ�����ڡ��Ϻ��گ�黹�������ϣ���û���͵�����ʡ���������Ǹ����˴���ľ��������
������������������һ���Ը�����ˣ����������ȫ���������Ľ�֣����㱾��û���¶����ĵĶ��п���Ϊ��ά���������϶��Ϻ����������Ǹ��ڡ���ǻ��ŭ���ڻʺ������������ǰ������ɢ���Ͼ���Ϊ��������Ů��Ů�ˣ�̫�ӵ���ĸ��С��Ů����ѽѽѧ����ĺ��̣��ο�����������ʲô���˵������أ��������������ݹ����帮���Լ��ѿ��ˣ����Ͼ�Ҳû�ж����ı�������λ�購��Ϊ��һ���С�º�����˵�������������㺾�Ҫ�ϻʺ���֮�����ľ���̫��֮λ������������ҡ��ǣ��ʵ��̫���ˡ�
���˻ڣ��ֺֿ�Թ������Ի�����Ϲ��ǽ��ҡ�������������ǡ�������������*�Ϲ��Ǵ���
����ͷ��ܴ�β�ͣ�ȴ�׳����Ϲ�����ΪƽϢ����ŭ�����������������ӳ������Ϲ���ʧ�����ǵ��߳����ŵ�ʱ���Ѿ�Ԥ�ϵ����������Լ���Ȼ���١���ν�ľ����纣��ʥ����Ũ��ԭ��������Ц��һ�������ʹ��紵���ѣ�ֻʣ���ij��ǵĺ���
���ı����ܿ����٣����ã�������ϣּ�ϱ������Ϲ��ǡ�����ʤ���·�̫����Ϊ�ɣ�ָ���˰��й���ı�����ң����ɴ�ն����̫����ԭΪ���ʺ�����ӣ�����ʱֻ��14�꣬�ķ���������������֪��������Խ�࣬�־�Խ������衣��������Ů�˵��·���˯���������ط����Է����̿ͣ������αض�ռ�����Լ��ף��÷�ʦ�����������ȵȡ�������־����������ֳ������쳣��Ϊ�����������˿�ʵ������˽�����ˣ������������������ں������ɽ��ˮ�����ã�����һλ�������ҵĸ��˰�����ר��ǰ�����ܣ��������ʵ�����DZ���Ϊ���ˣ������ǭ�ݡ���������۳���̫�ӳ�Ǭ���ʵĵط���Ҳ�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