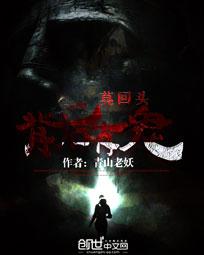圆珠与箭头-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杜道周
顾影自怜的顾影。
顾影。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人。
乘火车赶到广州,我顺利地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训练与学习都很苦,但我都熬下来了,并于一年后顺利地毕业。由于在校时表现算得上良好,所以我一出来就是中尉。
自从当了军官后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杜府里见到的军官并不是所有军官的样子,他们是老一辈军官,地位都是真刀实枪的打出来的,所以身上的匪气与杀气都很重,而现在这些军官大多是系统学习与训练出来的,比较起来要斯文很多,不过这些都是还没有上过战场的状态。
三年后我们都全面参加了战争,那时候我已经是上尉,与战友一同出生入死,受过伤也见过别人死,说真的一开始会很怕,怕到吐,怕到一整天手都还在发抖,后来就麻木了。
不是麻木于杀人这件事,而是麻木于生命的消逝。
我们都不愿意多杀一个人,但对于死亡已经能够坦然接受。
战争越来越激烈,我很幸运地依然活着,用流血换了少校的头衔。有一次师团驻军的地方离家乡很近,我特地请假回去一趟,不是为了回杜府,而是想见一见顾影。
看多了生死,再回头看以前在杜府发生的事就觉得自己从前的想法太过孩子气了。如果还想着回去耀舞扬威的话,那简直就像拿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的生命在开玩笑一样,我不敢为。过去就随它去吧,什么恨都早就淡了。
但很奇怪,我对顾影的反而有了执念。
在校时觉得苦了会想起他独自一人在戏台上唱戏的样子,真正踏足战场后身染鲜血时会想起与他面对面时他一身的狼狈,如今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会想起分别时仰首低唱的他……
仿佛我受过的他都受过一样,而他却还能出手帮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还能够带着笑容面对。顾影身上有我渴求的温柔,我想他的时候越来越多了,甚至开始去听戏。虽然我并不懂得欣赏,但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听一听。然后闭眼回想那时候的顾影是怎么唱的,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很婉转缠绵。
我想要见他一见,问一问他当初是怎样唱的,我得记熟了,方便以后回忆。这个想法很强烈,所以难得离故乡近我就向上级告假跑了一趟。
只是,我没有找到顾影。我们相遇的地方早就不是一个戏馆子,如今是一家茶馆,生意还不怎么好。
那日我打听了很久才打听到原来顾影所在的戏班散了,而他人也不知道去哪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顾影,你在哪?
军情越来越急,每一次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上战场,上去了又会不会还有机会下来?一切皆无常,我不畏惧,毕竟为着家国天下,但终究有些遗憾。
我曾说过要报答顾影,但如今都没有这个机会,有时候我想起他时会担忧,怕他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更怕他被牵连身死,这种怕与当年藏在茶几下的感受一样,即使已成铮铮汉子,我依然会这样怕着。
打了有三年仗了吧,我升了中校,人变得更稳重了,再不是当年的野孩子,但话也变少了,总觉得少了些对活着的激动。
我们团最近都在驻扎,等待着上级的调动。我每天就是跟上级一起研究大势,晚点读一读书,渐渐连顾影都很少想了,不过听戏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听过那晚会睡得更好。
春夏交接,树上有正在梳羽的鸟儿,我看着它不着调地哼两句,忽然就有人往我边上过来。我的警觉性被锻炼得很高,但没有转头去看,因为凭对方那个乍乎劲我就能认出来是手下的小张。
他跟我报告说遇到一个会唱京剧的人。我奇了,马上随他去看。
这几年随军到处走但到过的地方大多都是中部比较偏南的,戏听了不少,可是基本都是地方戏种。京剧也只有那次离家乡近了的时候听过,不过因为寻不着顾影消沉了好多天,所以总共也没听几次。现在我们的位置虽然也是长江以北,但还是比较接近江南一带,所以能遇到会唱京剧的人确实有些奇。
不是一个人,而是俩,一男一女。
男的很瘦,应该是好久没吃饱造成的,衣服洗得泛白而且有不少补丁但一点也不显邋遢。女的被护在他身后,低着头看不见长相,但光身形来看比起男的要有肉一点,似乎被照顾得挺好。
虽然干瘦,但在我看来,那男的要比女的更吸引人。他一双眼睛镶在瘦得两颊凹进去的脸上显得特别大,而且特别亮,跟顾影的眼睛一样像会说话似的,只不过这个人的眼睛表达出来的情绪是冷漠的,跟所有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
我问:“你会唱京剧?”
他说:“不会。”
我看了小张一眼,小张急道:“我明明听了你唱的。”
他说:“你听错了。”
我说:“不唱就算了。”
小张还要争辩,我已经走开。
我想那个人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因为这几天我只要往外走远一点偶尔也能够见到他。而且小张没说错,这人是会唱京剧的,我撞见过,他也发现了我,竟然还能很坦然地与我对视。
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说不会唱,他的回答很有力。他说:“凭什么要告诉你?”
那一刻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
我说:“我不会强迫你唱的。我只是喜欢听而已,虽然我不懂得欣赏。”
他笑了,虽然瘦脱了型笑起来还是好看,我想他原先肯定长得非常俊。他嘲笑道:“你们哪个听戏的懂欣赏了。”
别人我不知道,但我是承认的,所以不在意他在嘲讽。
我说:“我只是想怀念一下那种腔调。”可能因为难得遇到一个会唱京剧的,所以我总觉得从他身上能找到一点顾影的影子,所以闲话也多了起来。
他说了一个很文气的词,令我笑了出来。
他说:“哦,你是北平那头的人吧,觉得故土难离?”
我笑着摇头,如今对于我来说国家即是故土,不纠结于哪一方水土。
他追问,表情很倔,眼神里藏有刀锋,应该比我当年更甚。
我说:“那是一个人给我最深的印象。”
他不说话了,我还以为以他性格会揶揄我一顿,于是我侧过头看他。他发现我在看他了,回看我,目光像淬了毒。他鄙夷地说:“养戏子是吧,哈,没想到你还是个长情的。”
我皱起了眉头,他转身就走。
我说:“我与他只是一面之缘。”
他嗤声:“一见钟情?我看你是色迷心窍,两个男的?别笑死我了,你们就是一群吃饱了撑的。”
我被他的话震住数秒,回味过来摇头说:“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没有别的什么念头。”
他扫了我一眼,嘴角冷冷地笑开。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之后与他碰到也再没有交谈。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很快我们就分别了,因为我团被指派到别的地方,大概又是一场生死战争在等着我们。
后来多次想起他的话总会觉得好笑。
什么一见钟情,我与顾影都是男的,怎么可能啊。只是他与我相遇的时候太好,正是我需要帮助时,我受他恩惠,也感受到他的温柔,于是我很想要跟他做朋友,可以一生的朋友。他很特别,或者只是对我来说很特别,所以我才会念念不忘。事情只是如此简单。
已经连着赶了好多天的路了,大家都疲累,天还下起了雷雨,前路昏暗难辨,更是让人寸步难行。幸好我们遇到了一个村庄,看起来很破落,我们以为又是一个被战火破坏的家园,正准备打算直接住进去,没想到走近了能够看到三两点火光,看来是有人住的。我们派了最多话的小张去跟村里人借个方便,很快小张就回来,报告说村里人不反对,不过希望我们能够住在村子外围的屋里。
这种做法我们都理解,这年头军匪难分,平头百姓只能尽量小心,尽量远离。
各自安顿好,小张来找我闲聊,聊到他刚才在村里听到有人唱戏,而且还是京剧。他说他肯定不会听错。
看来小张对于之前那人说他听错了的事有些介怀。
有人唱京剧吗?
小张说就刚刚,那人可能还在唱呢。
我想了想将刚脱下的斗笠蓑衣再穿上就往小张指的方向去了。
雨很大,耳边只有哗啦的雨声和偶尔的响雷声,其它什么也听不到。
不得不说,我有些失望,但不死心又往深处走了一点。终于让我听到一点声音,依稀是在唱着什么,可是不是很清晰。
但已经足够了,事隔这么久我终于又听到了这种熟悉的腔调。
我越走越急,声音也就越来越清楚。
面前是一间旧屋,门虚掩。多么熟悉的一幕,画面与记忆开始重叠,原以为已经淡忘的人事一下子全勾了回来。
我将门轻轻推开,没有戏台,也没有白面红妆的人,只有一个背对着门口坐在矮竹椅上弯腰低头不知道在摆弄着什么的人。
我无声苦笑,不敢打扰对方,倚在门边闭目倾听。
雨未停,人声就先停了下来。我睁眼,屋里坐着的人回身看我,是个很瘦弱的人,一双眼睛独有神彩,似吸进了白天的阳光,此时尚有淡金暖意。
人与人的缘分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教人毫无准备,或者这样才值得往后数十年的回味。
此时此刻,我觉得非常平静,静得连心脏都不会跳了。
我长吸口气,又缓慢吐尽,然后低声唤面前的人:“顾影。”
☆、顾影
我向村里人说了来意,他们虽然奇怪也愿意让我留下,还说没人住的房子随便挑个住下就行。
这个村子原本应该是挺大的,但如今已经败落到只剩不足二十户人家了,而且大多都是老人与孩子,连妇人都不多。后来听老人说青壮的都投身战争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妇女大多往城里逃了,剩下的都是舍不得根的老人。
我说孩子呢?
老人的眼神透着难过,他说那些孩子大多可怜,已经是家里唯一活着的了。
原来都是些遗孤。我见他们的脸总是少有笑意,眼神也带着戒备,原来竟是这样的原因。
村子里的生活确实艰苦,但这是跟以前比的,战争年代我这种穷人在城里和在这里没什么区别。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将食物简单的煮熟,还学会打补丁,就是线脚不平整还经常会露出线头罢了。
渐渐我与村里人也熟络起来,他们都是很质朴的人,只是这样的时世让人变得充满戒心而已。可能因为我是外人,也是城里来的,那些小孩倒是愿意与我亲近,其实就是想听听城里的事儿。
他们还太小,离开这里的次数屈指可数,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即使是食不裹腹也阻挡不了他们对美好的向往。我也爱跟他们说话,不过都挑好的说,说说城里当年的盛况,说说才子佳人的风流,或者说说那些新奇的西洋玩意。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戏。像我这样的,学戏唱戏用了二十多年,要说摆脱它还真是难的,至少我不行。平日闲来没事我就会哼几句,被某几个话多的小鬼头听到了,缠着我非要说要听,我也就顺了他们的意唱几句,最后就变成了村里人都知道这事了,也都爱听。
但因为他们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我就给他们讲戏文,讲那些故事。村里人跟城里人不同,他们更爱那些英勇忠贞的戏,而不是缠绵悱恻的。
这样看起来我与村里人都过得很好,很快乐安逸。事实却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力去农耕,粮食根本不够吃饱,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去挖山上和荒地里的野菜,天冷了连野菜也没有的时候只能挖树根。
有时候会有些队伍经过村子,有军队也有流民,我们不管是哪种都避让。有一些见这里屋漏墙倒,人也是老弱病残,会给我们留口吃的,有一些则相反,抢了能找到的可以食用的东西离开。
幸好,我们的命都还在。
直到有一年,好不容易存到的一些吃的被抢走了,天已经见冷,地上草都是黄的,能果腹的东西还能有吗?每天我们都很努力的去寻找能吃的东西,甚至连小孩都出动了,但能找到的却越来越少。
有次跟老人上山,他指着地上的土跟我说:“这东西叫观音土,不能随便吃。”
我说:“土还能吃?”
他皱着脸说:“能饱肚啊。”说完他挖了一块出来,轻轻地放到我的手心,“你拿着吧,只是不到受不了千万不要吃。”
我问:“为什么?”
他弓着腰给自己挖了几块装在衣兜里,才转过来对我说:“吃了会死的。”
吃了会死为什么还吃?我没问,因为他先一步回答我了。
他拍着肚皮说:“至少不用当饿死鬼啊。”
我捏着手心的那块心里滋味万千。
这里是南北交接的地方,春夏景致特别好,但一入了冬,雨雪霏霏寒气怎样也挡不住,就像附在了骨头上一样。
我们吃不饱,身体弱很容易就会生病,一生病就意味着要死了。尽管大人有心关照小孩,吃的给他们多分一点,但终究他们还是更弱小一些,这个冬天才过半已经死了好几个。
四个小孩一个老人。
老人是给我观音土那一位,他不是病死的,而是吃观音土吃死的。或许是觉得自己老了多活无用,或许是为了省口粮,又或许是真不想活了,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知道人是死了。
每死一个我都很伤心,因为我与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特别是那些小孩,所以我更留意着他们。
因为冬天难过所以我们都挤在一个屋里睡,这样能省些柴火,靠着也能暖和一些。
某天夜里,二丫挪到我身边说冷,我将她抱到怀里。
她不冷,一点都不冷,浑身都是烫的,像个暖和的手炉,但她一直哆嗦着说冷。我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低声在她耳边说话安抚。听说人在死前会有感觉,我想是的,因为二丫似乎感觉到了,她很不安,两只小手攥紧了我胸前衣衫。她在啜泣,但听起来有气无力。
我抚着她的后脑,低声说:“没事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