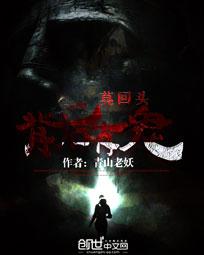圆珠与箭头-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时他还在轻轻笑,我开始细细瞧。
他的两道眉毛浓但不粗,眼睛低垂着能清楚地看到眼尾往上挑的弧度,鼻头圆润,双唇没了口红不再给人娇艳的错觉,而是薄薄的两片抿着,有隐忍之感,我想这应该是他原本清秀的脸上难得的一点男子气质。最令我欣赏的是他整个人给我的感觉,气质非常温和,无论是脸部线条还是骨骼身形都有种温润圆滑的感觉,我并不是说他胖,他一点都不胖,甚至是瘦削的,但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温柔是我唯一能够用来准确形容他的词。
随着他的低头,没有上蜡的额发向下滑,挡住了眉眼。
我似乎更难过了,轻声问:“你怎样的人?”
他抬头,神色有些讶异:“你听了我唱戏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原来他是唱戏的。
我没有听过戏所以并不知道,我向他如实解释。
他不计较。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他当我不存在似的自斟自饮。我发现他的酒量确实好,似乎都不会醉一样,我就这样看着他饮酒,也看着他两颊漫上红霞。
时间在这样的无言中过去,我终于忍不住地说:“今天你帮了我,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叫杜道周。”我郑重地报出名字,渴望与他结识。
他举杯的动作停了下来,猛地转头看我,原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杜道周?是‘有杕之杜,生于道周’的杜道周?”
爹曾对我说过我名字就是出于“有杕之杜,生于道周”这一句,他说这是求贤之诚,他说我该有贤能,我只当他附庸风雅。只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也会知道?
我点头。
他看我的眼神忽然就不对了,变得非常冷漠。他问:“既是杜府孙少爷,他们为什么还要抓你?”
这些私事本不用回答,但我好像不想惹他不高兴,所以解释了起来:“我要离开杜府,我不要待在那里。”
然后他疯了似的狂笑,我依稀见到他嘴角的伤口再次裂开渗出血丝。
“哈哈哈哈,做得好!”
这句话是在夸我吗?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
不知道笑了多久,他终于停了下来,嘴角因为伤口裂开而令周边有些红肿,但他一点疼也感觉不到似的,眼睛透亮地盯着我。我被他这样瞧得心跳加速。
又过了一阵他才收回视线,给自己斟了杯酒一口饮尽,然后才满足地对我说:“我疯了,高兴疯了。”
到这里,我发现他很讨厌杜府,跟我一样讨厌,或者比我更讨厌。
“虽然只是这城里的势力,但杜府人脉还是有的,你要跑就得跑远一点。”他又饮了杯酒说。
“我要去广州,考军校。”
他拿着酒杯的手抖了下,洒了小半杯到桌面上,用带着一丝惊慌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竟然喜欢当那种杀人的人。”
听到“杀人”二字我的心也颤了下,低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值得为了威压杜府而去当一个刽子手吗?当然不值得!可当军人必定是要举枪的吧,有什么值得我举枪杀人?锄强扶弱?用拳头就行了。保家卫国?太伟大了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抬头,他正在看我,眼神里藏有戒备。
这是在害怕吗?为什么害怕我?我即使有了枪也绝不会用来指着他的,甚至还能够保护他,为什么?
突然我想通了那个问题。
我站了起来,与他对视,很严肃地说:“因为那样才能让该死的人伏诛,才能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他怔怔望着我,好一会弯着眼睛笑了:“小小年纪比我想得透彻。”
其实都是受他启发,所以我有些不好意思,站着更是显得无措,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摆才好,最后本能略偏开头搔着耳后。
他也站了起来,意外地倒了两杯酒,端起一杯在另一杯的边沿轻敲了下。我留意到他的手指细长白皙,比起杜大夫人来竟然只觉得是长了点,然后我看着他仰头饮尽。他笑着说:“打仗是个危险事,我祝你平安。”接着伸手将另一杯也拿了起来,“不过你不会喝酒,所以你的那杯我也替你喝了。”
一句平安让我眼眶都热了,夺过他手上的酒杯,也学着他的样子仰头倒进嘴里。火辣的感觉从舌尖一直蔓延到胃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像拿火灼烧,但我觉得这一口酒很暖。
他笑着扶呛得直不起腰的我坐下。
从来没有沾过酒的我很快我就开始晕乎起来,无力地趴在桌上半眯着眼看他喝酒,渐渐就没了意识。
☆、顾影
杜道周,也就是我帮了的那个少年人,竟原来是杜大少的儿子,而且他竟然说要摆脱杜府,我听了实在是高兴极了。
该啊,该他的儿子嫌弃他。
因为开怀我饮了很多酒,带过来的几乎全喝光了,但也只是半醉,这是多年练出来的成果,毕竟有意识才不会教人随便摆弄了去。而旁边的杜道周早已经醉倒,趴在桌上呼呼睡了起来。这样看起来他的确在眉眼间与杜大少爷颇为相像,但两人的眼神却是大相径庭的。杜道周给我的感觉是耿直,而他爹杜大少的心思却需我费心揣摩。
真是怪异的传承。
我避开伤口托腮看他,越看越觉得他很好,倔强坚毅,与我大不相同。
我总觉得人生来都是带着棱角的,像一粒砂子。亿万的砂子堆出世界,我们在岁月中被风刮着前进,与其它砂子碰撞,不断地碰撞。有一些最终会被磨成圆滚的珠子,方能更好地借着风势朝前滚去,而有一些却会被磨成锋利的箭头,在漫漫长路上破空而去。
这些年来我终成一颗珠子。我想,杜道周会是个箭头,他能够走得更远。
真好啊。
我感叹一阵,替他捡来已经落到地上的西装外套披上,然后回到戏台上。
最终,只有这里才是属于我的。
不,是我属于这里,我对它连所有权都没有。
尽管我还有意识,但是毕竟喝了不少酒,脚步有些虚浮,身上也在发热,于是我坐在了戏台上的太师椅上。我将头往后枕在靠背上,双手置于扶手处。我想在别人看来这个动作肯定很古怪,像一个端坐的人忽然失去了生气。
但我只是觉得这样很舒服。
我想唱点什么,但闭眼想起的就是当年,我想这应该是受到杜道周的影响。
最终我还真的唱起了《西厢记》,但我已不是当年的小红娘,我早已当上了崔莺莺。可是诚如戴玉润以前说的,小姐也不比红娘好啊。
我闭着眼轻声地唱。由于被掐过喉咙疼,所以我唱得很慢,字是一个一个地吐出来的。
正唱到《哭宴》中张生与崔莺莺离别赴京考状元的地方,忽然就听到杜道周的声音。
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缓慢睁了眼,如大梦初醒。他已经站到戏台下方正中,与我是面对面的方向。我停了唱词,说:“他们都叫我顾影。”
他还问:“哪个顾哪个影?”
我停顿一下,自嘲道:“顾影自怜的顾影。”
他说:“我会回来的,我会报答你的。”
我笑:“好啊,我等着。”
其实我想的是,离开了又何必回来?
杜道周走后我开始留意杜府的消息,丢了孙儿这事他们掩盖得很好,不过我是知情人还是看得出些端倪来,比如杜大少的脸色非常差。我远远见过一次,立马心里就畅快得很,觉得很解恨。后来还有一个消息,听说杜老太爷给杜小少爷物色了一房媳妇,是邻城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政府官员的独女。
这事成了真,婚礼极尽豪华,我按着自己的意愿想这肯定比杜大少当年的婚事更风光。
后来我经常特地走近杜府,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碰上一次杜大少出门,我便怀着落井下石的心思上去攀谈。
“杜大少。”我还是一如当年的唤他。近看他更显老了,我想他此时心里肯定难受得要命,一个没了继承人的继承人,哈哈。
他看了我两眼才恍然,沉着脸说:“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
我的心一阵刺痛,他果然从来没有喜爱过我,竟然不能一眼认出我来。而他即便化了灰我都觉得我都能够认得,这种轻视实在太可恨了!
但我还在笑:“我是来向杜大少道喜的。”
看着杜大少爷因为我的话而神色顿变,我发现我已经不怕了,怎么招人怒都敢,我只要这一瞬间的解恨。
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哼一声就转身上车离开。
我站在杜府门外傻乐了好一阵才打算离开,才走出去两步就见到有辆车载了杜小少爷回来。我见了他就想到当年如谶语般的那句“下九流”,恨恨地向他招呼了一声:“杜小少爷。”
他茫然地看着我。
我笑着说:“杜小少爷可是不记得当年总是被你欺负的那个小男孩了?”
他这才认出我来,但一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尴尬表现,而是非常爽朗地说:“原来是你啊,真是好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跟当年一样瘦瘦弱弱的。才上了几年学就没学下去了,现在过得还好?”
不好!
我很想吼他这一句,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些犯糊涂,方才的快意刹那全没了,甚至连恨都消失不见,瞬间不知道这么多年埋在心里的那些不平事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转身就走,完全不理会身后杜小少爷的叫唤。
为什么他可以将如尖刺扎在我心上的事情如此轻巧地抹过去?原来这世上有好多事情只有自己在意,对别人来说那不过是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或者随意做的一件小事,压根不值一提,但于自己却是无法磨灭的伤痛。找他们理论去?呵……这样只会发现自己的不自量力,连恨都恨得微不足道。
这样的恨一辈子都解不了,包括我对杜大少的恨,我以为方才是解恨了,原来并不是的,因为他再不好过也掩盖不了他对我的不在乎,他的痛恨也好麻烦也好全不由我而起,我的所谓解恨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我的恨,戴玉润的恨,全是没法子解的,会跟我们一辈子直到带入黄土。
我不想要这样,这样让我极度难过。
可又能如何?我解不了也放不下啊。
我更消沉了。
一年后戏班发生了一件大事,是源于柳宵月的。他趁夜盗了钱老爷的珠宝银钱逃了,钱老爷找不到他人就带了一班子打手和佣人将戏班的人压送到警察局里讨公道。钱老爷家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但判下来的价格着实可怕。
我们自然是骂冤枉,但一个小戏班怎样斗得过有钱的老爷们?戏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不算富裕,这么一折腾便倒了。为此班主甚至连院子都卖了,可谓赔尽了一生积蓄。
这是我们能够呆的最后一天了。班主没什么钱分给大家,只好跟大家说院里还有什么能带走还有用的细软都拿走吧。
我抓了包袱站在院中细细打量这里的一砖一瓦,小时候住的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倒是这里像个家一样,而现在我连它都要失去了。
班主站到我身边,也一同看着这个院子。
他说:“有什么打算?”
我说:“再找个戏班吧,除了唱戏我还能做什么?”
他说:“这个不能一辈子的。”
我说:“不能唱再打算吧。”
他叹气:“还是你老实啊,那个柳宵月真是个没心肝的,我对他多好你们也是看到的,他倒好,这样回报于我,简直就是白眼狼。”
虽然班主的话也没错,但我心里是有些佩服柳宵月这个做法的,果然还是跟我有些不同,他确实带着刺儿。
班主又呸道:“他逃?逃得掉吗,现在什么时世,这么安逸的城里不待那是找死,他就是在找死。死了干净。”
我没有回应,又看了一会就离开了,也没有招呼一声,想着班主这时候也不想被人打扰。
好不容易我找到了一个草台班子,住的地方很小,吃的也总是有一顿没一顿,加上后来爆发了全面战争,前线紧张,后方城里生活就越发的不好,那便更没人听戏了,即使是要听也不听我们这种戏班。但戏除了自己开堂子唱,还有唱红事和白事的。红事轮不到我们这种小戏班唱,但是白事总归是有的,特别是这种时世。
生前富贵不了,死后也想热闹一场,这是百姓普遍的想法。
有时候是在人家里唱,有时候是在郊外唱。头几回在郊外唱我怕得要死,站在那个竹搭的台子上腿都是抖的,后来多唱了几次也麻木了,我甚至会想给人唱与给鬼唱有什么不同?
百姓越来越穷,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少,戏班里的人都饿得要上山挖野菜了,我偷摸着拿些以前的头面去换钱来帮补自己的生计,也不敢吃多,生怕别人发现我有吃的。人饿疯了穷疯了会干出些什么事来谁也预计不到,我得防范着些。后来拿去当的头面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我就不卖了,都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若要贱卖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十天半月没一顿饱,我瘦得面黄肌瘦,有次唱完回去卸妆经过镜子的时候差点儿被自己的样子吓到,整一个无常鬼似的。
原来我每次都是顶着个鬼样给鬼唱戏吗?那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同类勾了我的命去?
那夜我没睡着,想了一宿,最终我决定不唱了。
我决定要离开这座城。
临行前我到城外庙里走了一趟,算是向戴玉润告别。我与他说往后我再也不能来看他了,我问他会怕寂寞吗?离开时我在门边回头看了很久,其实会孤独寂寞的是我,往后连个熟悉人说话都没有了,我有些舍不得他。
不过我还是独自走了,跟在我身边他怕是连口香火都没,何必呢。
火车票的钱我掏不出,只能靠自己走了,只是战争年代我怎敢一个人到处走动?还好让我找到个南下的商队,求了许久才得了随队的许可,不过吃还是得自己管自己。我们一路南下,在经过一个寥落的村子时我选择了留下。
就这里吧,我想,从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杜道周
顾影自怜的顾影。
顾影。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人。
乘火车赶到广州,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