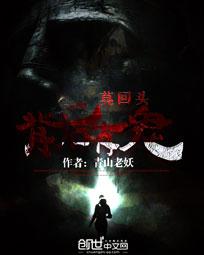圆珠与箭头-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恶啊,竟然要找到我了,竟然在这种时候。
之前并没有好好地打量过馆子,这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转头四周快速看了遍,有窗!但跳窗肯定也会让在外面的他们发现,要怎么办?
我紧张得全身崩紧。
到底还有没有出口?有没有?
我还在四处张望。
有了!
我终于发现台子左侧有个供人进出的地方,我不知道它通向哪里,但我想至少能够缓一缓。
撑着台子边沿跳了上去,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往那个地方走去。我还记着台上那人,即使两人擦肩而过是那样匆匆还特地转头望了一眼。紧张的时刻我还在想那人的眉毛竟与我鼻尖位置持平,比我认为的要高不少。
外面的声音更大了,我想他们下一步就要闯进来,而我还有心情关心他们会不会打扰到台上这人。
但我只能加紧了脚步。
已经近在咫尺。
☆、顾影
经过那夜,我似有感触,原以为像我这样懦弱的人才会那样,没曾想像柳宵月那样带刺儿的人也是这样。到底是他一直装作坚强,还是我们这种人的命运本就无法扭转?
我自然是想不通,更不敢想,没有能力的人多想无益。
日复一日,我如常地过,只是更沉迷于戏中世界。
有时候我会很感叹老百姓的念旧,瞧着我这样的人在台上唱作念这么多年,竟然还会来捧场子,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我总感觉他们是真的喜欢戏里的故事,所以我唱得投入,希望能够叫他们尽兴。
这样做竟比以前什么时候都让我宽怀。
人前的柳宵月还是那样光彩夺目,他过得也张扬,生这个字用在他身上显得最灿烂。这样一对比我就显得逊色许多了,不是着疯地唱戏就是沉默地过活,我习惯了倒不觉得怎么样,反正怎样过不是过?我怕死,但或许也希望这一生快点过完。但有些人总是热忱,譬如戏班的李婶,总爱在我落单的时候劝说我成家,她说有了家一切都好了。
我觉得她是真的关心我,因为她总不在人前提这事,免了我的尴尬。说来她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多年来她的亲近与关怀宛如母爱,所以当她不知第几次与我说要给我介绍姑娘的时候我终于答应了下来。
听李婶说是个城外村里的姑娘,单纯踏实。
我还没见着人,于是开始想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想着想着不知为何就想到了我娘,那个楚楚可怜的美丽妇人。这使我无来由地产生了恐惧。嫁娶不见得两情相悦,各取所需到头来哪个好过了?
于是我问李婶:“那姑娘知道我做什么吗?”
她说:“知道,姑娘不挑的。”
她这么一说我更忐忑了。
她又说:“你放心,跟城里人不同,实诚着呢。”
终于见到了人,李婶的眼光很好,姑娘长得挺好看,年轻丰润。她说话的声音大且亮,是与我娘完全不同的女性,瞧起来很乐观的样子。与她相比,倒显得我很柔弱似的。
我们分开后,我还是对李婶了说不合适。不是对方不好,而是我出了问题。我害怕她看着我的目光,总觉里头的明亮把我照得无所遁形。过去那些不光彩让我心虚得很,而且我的潦倒也不必让别人陪着分担,日子久了终是会互相埋怨,那样好的姑娘被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不敢想象。
想到这些我觉得很无助,我对爱竟提不起兴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错了。
后来李婶又给我介绍了几位姑娘,但都被我婉拒了,而她叹气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阵暖和。不过没多久她的媳妇给她家添了孙子后,她也没空理我了,虽说这样免了不少麻烦,但我多少还是有些失落。
那年夏天来得早,闷热难耐,戏班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柳宵月性子急,这种天气更是受不了,撒了通脾气说明天不唱了要休息。班主惯他,只好写了牌子放到馆子外说休息一天。
这样大撒脾气本是很招人怨的,不过这回给了大家一个休息日,大家也就乐于接受,还高高兴兴的谢了柳宵月。
我在院里闲了一个早上觉得实在无趣,也就往馆子去了,真正的戏台会让我更自在些。
眼前是没有人声的馆子。
我扯着嘴角笑了下,嘲笑自己的多愁善感。
进馆后我没有拴上门,仅虚掩着。我想要是有人戏瘾来了跑过来要听戏却发现今天不开锣倒也能进来听我胡唱一通,如此他们大概也不至于太过难过吧。
这个理由特别好,归根到底只是因为我懒散罢了。说句老实话我除了唱戏什么也不干,也基本不怎么会干,所以养成了这样懒散的脾性。我也从不觉得懒散不好,以前不会,以后更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懒让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过这些就是后话了。
我到了后头画脸戴假发,镜里的人连个笑容都不给我。这天确实热,我脱了长衫马褂拿着有些厚的戏服时开始犹豫,最后将它放下了。长衫马褂脱的时候被我放到了梳妆台上,我看了眼衣衫又看了看镜中自己现在的样子。
镜中人身上穿的是方便行动的中衣中裤,这样最简单的样式配着完整的头面妆容,倒有点趣味。
我索性就这个样子登上了戏台,不看台下,只专注于戏里的世界,这样就不会因为没有观众而觉得失落。
刚开始我还是很认真地唱的,后来就胡乱地唱了,东一段西一段不知道都拼出了些什么故事来。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感觉很自由。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突然冲了个人进来,不是见惯的平民样,穿着西装,不过我仍当他是个来听戏的,所以没理。
很快我就重新进入到戏文里的世界,不过因为有人听我便再不胡唱了,希望他听得高兴。
一段戏尚未唱完,他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往台上冲了上来,还是从我身边蹿过去的。我一时没反应不过来,待反应过来却看到有一堆人闹哄哄地走了进来。
我不敢多事,继续唱着,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算了。
可是别人不放过我,喝道:“有一个年轻少爷进来过吗?”
不好惹的人。
我心底叹了口气,边唱着边向他们作了个摇首的动作。为什么我不供那人出来?我想可能是唱太久人糊涂了,但也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帮一个认真听我唱戏的人?
现在看来是缘份作怪吧。
那时我觉得自己干了蠢事,心里紧张得很,毕竟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信了我的。
果不其然,站在中间的那个人站了出来,怪声怪气地说道:“这不是顾老板吗?”
我看了他一眼,努力想了想才认出来是谁。在我跟在杜大少身边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人,几面之缘。原来要抓人的是杜府的人吗?
瞬间我就对自己刚才的行为很满意了。
那人见我没理他,往前几步,直走到戏台边沿位置。他笑着,但我觉得满脸横肉的很是狰狞。他又说:“顾老板现在是更风光了,不认得我杜府人了?”
呸。
只是我不敢表现出来,停下动作不唱了,向他们笑了笑作个揖。
才抬头,见那个人竟已经跳上了戏台,与我只有三四步的距离。
他说:“几年没见,顾老板越来越好看了。”
下面的人哄笑起来。他往我的方向走,步伐很大但慢,好像在戏弄什么似的。
我紧张地说:“我刚刚没见过外人。”
他已经来到我身前了,我只好往后退。他似乎满怀恶意地也跟着往前步,一边还说:“听到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搜一搜的。”说完,他挥挥手,台下的人就开始分散四处找人。
看来竟然还是个小头目,更不好与他作对了。
我心急,退后的步伐更快,忽然被东西拌了下,就跌坐下去了。那是放在台上装饰用的太师椅,两椅一几放在戏台正中,因为没开锣所以都用绣花黄布分别罩着。
他低头看着我,嘿嘿笑了两声,伸手拽我的假发,又掐我的脖子。我敢肯定这人是个粗人,因为他的手劲实在是大,我想他要是再多掐一会我就该死掉了。
但是他没有,玩儿似的,一会掐下,一会摸下,还给了我个巴掌。我扭着身子要躲,当然是躲不过,但也咬紧了牙不喊疼。
疯子。
其余人哪里都搜过了,包括后台,没有找到人,此时都站在台下看戏。
最后他揪着我的衣领说:“真贱。”
我怔住,连他松手了也不知道,摔倒在椅脚边,额头还磕到了戏台上。
“咚”的一声在脑海里久久回响,恍惚中我想起了杜大少爷砸我的那个茶壶,茫然地左右看下,没有满地的碎片心才安定下来。
我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却来辱骂我,与他何干?真是好笑!
他们都走了,带着嬉笑,我却连回骂都是在心里不敢声张。
我觉得很累,趴了一阵才站起来,拍了拍太师椅边上的茶几,说:“都走了。”
☆、杜道周
我没有藏到戏台后面的房间去,因为我跳到戏台上看到两椅一几后福至心灵的决定藏到里面去,毕竟后面的房间到底有没有可逃跑的地方也不知道,要是没有就只能被瓮中抓鳖了。而且在杜府的这些年里我从来只有逃没有藏,我想他们有可能想不到我会蜷缩在一张茶几之下。
于是我果断地掀了黄绸布钻进去。
外面传来了很多声音,每一次都像锤子砸在我的胸口,我的手攥紧了案腿。我很紧张,为那人可能会将我指出来,也为那人如果不指出我来会被刁难。那是一种复杂矛盾到我无法理解的情绪。
终于那些难听的话语都停了,而我也终于能够顺利呼吸了。只是我迟迟没有听到那人的声音,整颗心再次被吊了起来。之前我就为这个陌生人担足了心,但那人按住了茶几,用的力道算不上重,可是我不敢掀了它走出来。
只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感受到的唯一的温柔。
外面到底什么情况?眼前一片黑,耳边只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声,我几乎要为这样的寂静而窒息。
在我快要忍耐不住时终于听到了那人低声说:“都走了。”
那刻我一定很激动,所以手上的力道重了。整张茶几连同盖在上面的黄绸布都被掀倒地上,而我也跟着狼狈地跌了出去。
黄绸布一掀才看得出来原来太师椅与茶几的样子非常简单,腿部纤细,而且这个茶几比一般的高一些宽一些,以至于个头挺高的我能够藏进去,虽然十分逼仄。
我快速地站起来。
这是我与那人的正式见面,但是我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心里不免有点懊恼。
我低着头装作不在意地拍拍身上的尘土,说:“谢谢你帮了我。”我抬眼,再慢慢抬头看那人。
那人比我还狼狈,衣衫皱得不成样子,头上假发歪了,油彩之下右边脸肿起一片,嘴角也破了,最令我不忍直视的是脖子,其上指痕明显,我不敢想象这是多大力度造成的。很多话哽在喉头,我盯着那人的衣领处,在衣衫遮挡的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伤痕?拳头被捏得死紧,我看不到自己的神情,但我想我的眼神必定凶狠。
我胸腔里满是怒意。
应该是因为嘴角破了的关系,那人说话很慢,显得温吞低缓:“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折返,你还是快走吧。”
是我连累了他,我不应该再连累他第二次的,但是我摇头,很肯定地摇头。
那人看了我一眼,距离近以至于我都能够看得出那双眼里的瞳仁不是纯黑的,有琥珀的色泽,表面一层潋滟水光,是我见过最清澈的。那人说随便我,然后转身就往戏台右侧的出口走去。
眼看人要离去,我伸手抓住了其手腕,说:“你去哪?”
那人不得不回头,眉头稍微皱了起来:“放心,我要是会出卖你刚才就不会帮你了。”
见被误会了,我急得手上用了劲:“那些都是杜大夫人手下的人,他们不会尽心找我的。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
“我疼。”那人说。
“啊?”我想我肯定是在茶几下闷久了导致头脑发昏,所以此时在那人面前总有种慌乱与无措。
“你的手抓得我很疼。”
“对不起,我……”我收回手,脸上有点发热。实在是太尴尬了。
“真是个粗鲁的孩子。”那人如此评价,我听了有些不是滋味,有点想要开辩又听到那人开口说话,甚至看到那人的嘴角好像上扬了那么一点,“不过粗鲁些好,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了去。”
说完,那人就再次转身要走。我还是那句:“你去哪?”
那人回头似乎无奈地解释:“我总不能一直这个样子与你说话吧。”
这么看来确实是我无理取闹。
看着他走到后面的房间,我默默地等待,早忘了我该离开,似乎等待才是我需要做的事。那人没有出来,而是唤了我进去。
一个极温柔的男人。
这是我走进后面房间见到的人。我呆了。我没有想过那个柔媚的人会是个他,但那些伤我不会认错,那人就是他。我对于这个事实不能适应,心里难过,但我不知道我为了什么难过。
“你……”
“来,渴吗?”他先坐下,再招呼我,不过他摇了摇小桌上的茶壶又说:“连点隔夜的茶水都没了,我自己只带了酒。”
他用带着询问的目光看向我。
“我不喝酒。”我坐到他旁边的凳子上说,说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过于冷硬,于是又说:“酒会误事。”
听了这句,他转首看我:“是了,你这么粗鲁的小鬼头当然还是少喝的好,免得醉酒闹起来伤了人。确实误事儿。”我以为他在记恨刚才的事,但接着又听到他低头轻声笑着说:“不过我这样的人啊,不喝酒才误事儿,得多喝点儿的。”
这话给我的感觉很怪。他明明笑着说,我却听出了点难过的感觉来。我向他看去。
说来奇怪,这人我之前一直盯着看,进来这里后竟然就不敢看了,好像在赌气,可是他压根没给我气受。
此时他还在轻轻笑,我开始细细瞧。
他的两道眉毛浓但不粗,眼睛低垂着能清楚地看到眼尾往上挑的弧度,鼻头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