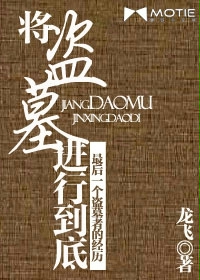离婚进行式by呻吟(现代 破镜重圆)-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耶?」昕胤歪了歪头,虽然闭著眼睛,但他毫无干扰的动作,让我不由得感到好奇,「先生,什麽意思是,漂亮?」
「啊……」我手忙脚乱的想著措词,看了看一旁事不关己的教授,「教授你讲一下啦!」
「孽徒。」教授开朗的笑了,开始和昕胤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大概是西藏语吧,其实大学的时候无聊修过这门课,但最後我只学会了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的鬼画符签名,而且每一次签的样子都不一样。
「是这样啊……」昕胤似乎明白了美丽的意思,「可是先生,又有谁不美丽呢?」
我又一次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就这样僵在那儿,我这时才想起来昕胤大概算是沙弥?但他整个人散发的气息,都不像是单纯的沙弥,可外貌又是这样的年轻,年轻到我都怀疑他根本没有成年了。
「先生,先生?」昕胤呼唤著我的名字,我顿时从思绪中抽离,昕胤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先生,我没有受戒,所以我和你一样,都只是一般的人。」
我不解的看著他,「啊?」
昕胤淡淡的笑了,在他那始终平静的表情之中,我却闻到了一丝丝的寂静,就像是全然的孤独一样,「我是异端,不能受戒的。」
他伸出了他纤细的手,我视线随著往下望,看见了的是──他少了一根手指头。
「生下来就是如此了,但对我并没什麽差别,这应该是我的业障。」昕胤伸回了他的手,我不可否认有些惊讶,毕竟在生活中太少遇到这样写实的事情,「先生,你怎麽又悲伤了呢?」
看著他始终紧闭的双眼,我疑惑了,「你为什麽一直闭著眼睛呢?」
「我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我想,那便是佛祖吧,他和我说。他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这世界,因为这世界还不值得你张开双眼。」昕胤再次抚摸上我的脸,而这一次我比较不像起初那麽惊讶,「於是我便不看了,这并没有什麽差别的,我还是能看到先生的脸。」
「张良,看来你已经摆脱糜烂的日子了?」一直不发一语的教授,突然插话,我吓了一跳,连忙低下身子,「教授,我一时太好奇了。」
「算了,你这些日子就和昕胤一起过吧。」教授想了想,「跟著他,你也还是可以学习什麽是死亡的。」
「是!」
我的天啊,我第一次这麽感谢老天爷,还以为教授要说我们现在就到寺庙里头剃度守戒,这样一来我就没机会继续认识昕胤了。
「那我先去找朋友了。」
教授对昕胤挥了挥手,昕胤轻轻的点了点头,我看著昕胤应对如流的态度,心中的好奇愈来愈浓烈了,究竟一个始终闭著双眼的人,要怎麽克制住自己想要看见太阳的渴望?
每一个人都是向光的,有些是心,有些是身体。因为光代表的是生命,是生命在世界运行流转的最基本物件,光代表的是永恒,只要光存在的一天,生命便不会消失。
「先生,那麽,我们去看天空吧。」
昕胤转过身子,轻盈的步伐踏在崎岖的地面,一点儿也没有被干扰到的感觉,反观我,好手好脚好眼睛,却一直跌跌撞撞的。
所以说,有没有听到佛祖说话,真的差很多吗?
「先生。」昕胤挑了个位置坐下,随後我也找了个比较平坦的地方,不知道为什麽,明明才第一次见面,在他身边我原本什麽都无所谓了的低迷心情,就有了起色,「我和你很有缘呢。」
不用说,我的脸一定又红了,「为什麽?」
「怎麽说呢……这样怎样表达才好……」昕胤低著头,似乎正在思考著用词,「是风和我说的。」
我更不明白了,「什麽?」
「先生,你听不到吗?风的声音。」昕胤指了指四周冰凉的冷风,「它们说,你和我,从好几世以前就认识了,不是常常有人说,一次相逢,可能是累积了千世的瞥望吗?」
「可是如果是这样,那你和每一个人不都很有缘吗?」我不解的问道,「我不太相信什麽前世今生的。」
「先生,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昕胤笑了,那笑如春风出沐,使人目眩神迷,「对我来说,是没有前世今生的,我只有一生,从好几百年前,就只有这一世而已。」
我愈听愈不懂了,大概我没有什麽慧根吧,想到这不禁感到挫折,好不容易,对一个人有这麽小鹿乱撞的感觉,就像是圣诞老公公的麋鹿都在我心里跳舞一样。
想到这,我才忽然记起,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昕胤一起度过这天,但那时候我大概就已经回到台湾了吧。
「不管什麽轮回今生今世,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不是吗?」我摇了摇头,抛去方才突来的惆怅,也不明白究竟我对一个才刚见面的人,产生如此浓烈的熟悉感是什麽原因。
突然,昕胤转过身子,抚摸了我的轮廓,「先生,先生,可是你又知道多少,属於你的过往?」
× × ×
我对著镜中帅气的自己,露出一个微笑,试图表达和自己心中完全搭不上的情绪。
莫道圣诞叮叮当,只有寒冬扑鼻来。我真搞不懂圣诞节究竟是谁决定要变成这样阖家欢喜的节日,这种日子摆明了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尤其现在人总喜欢把圣诞节当成情人节,情人节当成清明节,清明节当成过年,根本就乱乱来。
如果可以,我多想要就窝在家里,度过一个难得的星期六假期,然而到底是谁说员工有周休二日的权利?快叫他出来面对!
我拖著疲乏的身子,走出了大门,还是充满了对於假日也要上班这件事情的绝望,虽然广播这行业本来就是你担到哪个时段你就只能认命。
在公司这一年多,我看了很多名主持人的百态,有好的有坏的,无论如何,总是让自己进步的好方法,从一个小小的职员做起,现在我已经偶尔能在一些主持人的节目中插上一两句话,也算是很大的创举了。
虽然这三年,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回到西藏,回到那年的高山青草原,和昕胤一起躺在草地上,感受著大自然的气息,那一个礼拜,真的是我到了目前为止,最轻松的时光了。
但想到了我离开之前,昕胤的那一番话,我就像是被扔进了什麽冰桶里一样,整颗心都冻僵了,我明白他想要告诉我的事情,但情感上就是不能接受。
明明他也是喜欢的啊……
「喂,张良,你是睡著了?」
我从迷乱的情绪中回过神,看到一旁正在喝著咖啡的任久,难得有机会访问到杂志的大编辑,我竟然还恍神……虽然我们是同学。
「啊,才没有,我只是想到快圣诞节了,又一个人过很讨厌。」我叹了口气,「才不像你,就算没了益晨还有益晴。」
我的头被狠狠的敲了一下,任久一脸就像是刚刚打我的是外星人不是他的手一样,「快问,我很忙,我还要睡觉。」
「啧。」我按下了录音键,这次的访问因为主持人临时有事情不在,所以由我来帮忙录制,「那麽请问一下,任大编辑对於圣诞节的看法是?」
「无聊。」任久晃了晃手中的杂志,「收音机前面的女人听著,圣诞节不是你们用来当成情人节的日子,这世界才没有每天都情人节,你有看过有人每天都吃巧克力不会腻的吗?」
「但这个节日对很多情侣而言都非常重要不是吗?」
「重要是重要,但男人在这一天不外乎就是要把你拐上床,如果你真如他的意,那你过的就不是圣诞节,而是交配节了。」任久喝了口咖啡,「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跟你男朋友都是那种做爱机器,一天不做爱就像是全身长满了虫一样,那我就不反对。」
「那请问你是怎样和情人过圣诞节的呢?」
「我啊,忘了。」
任久轻描淡写的回避著问题,天知道他会忘了,他怎麽可能会忘了!益晨那家伙,只要是节日,都看重得像是自己的命一样,怎麽可能让任久随便过,但在录音中我又不方便多说什麽。
他做了个结论,「总之,圣诞节要过得开心,但不要总是顺了你男人的意。」
我按掉了录音,马上笑了出来,任久一脸不耐烦的看著我,我好不容易才忍住自己的笑意,「你这人,真的太好笑了!」
任久白了我一眼,「白痴。」
突然,录音室的门开了,我本来以为是前辈忙完事情回来,但却看到了益晨毫无表情的站在门口,我回头瞥了任久,他那表情活像是偷吃被抓到的猫,正努力在假装自己刚刚没有做什麽不该做的。
益晨缓缓的走了过来,不是我要说,他还真有当军人的气质,举手投足都像是站在指挥线指挥别人去死的将军,充满了莫名的霸气,「你刚刚说了什麽?」
任久心虚的转过头,「没、没什麽。」
「那走了。」
益晨没有多说什麽,转过身後便走出了大门,任久见状只好收拾收拾,向我挥了挥手致意後,便急忙跟著他离开了。
我看著任久追出去的背影,不禁叹了口气,如果今天是昕胤站在我面前,这样潇洒的转身离去,我想,我大概也会这样追著出去吧。
喝了一口咖啡,即使是在录音间,冰冷的空气也一直窜入,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条细缝穿进来的。
我剪辑著要播放的片段,算著前辈回来的时间,心不在焉的东弄弄西弄弄。
好啦,我承认,我对圣诞节就是抱持著类似去死去死团的冲动,这一点儿也不像是人在过的节日啊,没人陪就算了,身边还是一大堆常常出问题的机器。
更何况,想到前辈的事情是为了陪女朋友出门逛街,我心中的不满就更加扩大了,女朋友?女朋友?女朋友是什麽,能吃吗?
工作比较重要吧!
我无奈的叹了口气,想到了自己这样悲凉的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圣诞节、跨年、情人节,唯一比较热闹的大概是清明节,这样子的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可怜了?
可是我就是,忘不掉,忘不掉那在梦中一直出现,美丽深邃的,蔚蓝大海。
上帝爸爸说,他关了你的窗户,一定会记得帮你开门。我常常觉得这句话根本是话唬烂,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把我的窗户关了之後还把钥匙给吞了,根本没有什麽门啊地道啊连狗洞都没有。
可是这句话套在昕胤,几乎是百分之百吻合,虽然在身体上,昕胤有小小的缺陷,更不用提他那我到现在依旧不明白的,不用双眼看看这世界的坚持,但上帝爸爸给了他,非常优雅的一扇门。
那是纯净。
就像是世俗的一切都沾染不到他的身上一样,他的一切,就如同洁净无够的水,太透明了,透明到你看进了他那双湛蓝的双眼,一瞬间,你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心一样。
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都是光赋予的,而在海洋中孵化成形,对我而言,昕胤的双眼就像是最初的大海,那儿没有纷纷扰扰,没有悲伤,没有喜悦,只是平淡的,平淡的,温柔的包覆住你最脆弱的心。
只看了那麽几秒,我却像是耽溺在其中数百年一样的久,也不知道是为什麽。
或许,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安排吧。
虽然我没有信仰,但和昕胤相处的那些日子,也稍微的体会到了他所谓的「一生」和「佛祖」的意思,既然昕胤那时候说,自己和他是有缘的,那麽,就当作是冥冥之中,真的有所安排吧。
「先生,先生,可是你又知道多少,属於你的过往?」
第一天昕胤和我说的话,我到了现在依旧不明白其中的涵义,究竟他是知道了我的什麽过往,还是单纯的一句疑问呢?
好多好多关於昕胤的疑问,悬在半空中,像是在钓鱼一样,而我的回忆便是最容易上钩的笨蛋,明明知道咬住了鱼钩就是死亡,却依旧傻傻的,傻傻的跃出水面。
我不相信一见锺情,更不相信什麽历久弥新,但当我想到了昕胤那双眼时,我全部的不相信,最後都只能坦然相信了。
× × ×
过了下午,前辈终於回来了,带著一大堆的甜点和莫名其妙的春风得意,终於我有些忍受不了,找个藉口先离开,以免到时候自己真的崩溃。
对於这样习惯逃避的自己,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麽。
走在大街上,明明才下午,却已经冷得不像话了,我不懂最近的上帝爸爸是不是心情也和我一样不太好,不然总是这样阴晴不定,可能是又偷腥被上帝妈妈抓到吧。
感受著冷风吹袭著我的脸,那些微冰冷的感觉,和西藏的气息极为不同,太湿了,究竟是因为台湾处於海岛,还是台湾的神明都太多愁善感了呢?总感觉天气之间充斥著眼泪,也不知道是谁哭出来的泪滴。
伸出手,想要拉紧围巾,希望自己不要因为这一点冷风而感冒,然而这个动作却悬在半空中,我想到了那一天,昕胤替我调整围巾时,平静的脸。
而思绪从一个点,就这麽,拉成了一个面。
和昕胤认识的第一天晚上,我和他睡了。
如果你现在的脑袋想到的是我们如何翻云覆雨有了今朝彷佛没有明日,那麽就证明你的脑袋太成人了,贴上标签大概可以贴到十九禁。
我躺在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