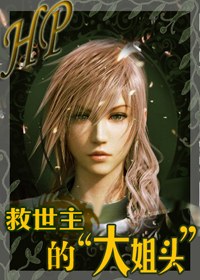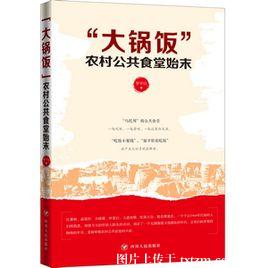"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一位著名诗人为“吃饭不要钱”特地赋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说:“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 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 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 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 ,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提倡“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最支持。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正如前面说及的江阴县马镇公社的尹积福那样,开始虽怀疑,接着是惊喜,最后是欢呼称颂。他们既是这一制度的最坚决拥护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填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可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比过去成倍地增长,根本没有放开肚皮吃的条件。所以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到了这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农民也就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极为丰富,多得吃不完这一因素外,还与主观地认为实行供给制后农民觉悟将有极大的提高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这年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也是最先在农村中提出的。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显得比农村落后,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表现还没有农民兄弟们出色。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和农村在中国社会变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进入共产主义,走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长时间是党工作的重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十分顺利,这就使得相当多的干部,不但熟悉农村,处理农村问题感到得心应手。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么从何处着手来实现这个变革呢?于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问题在于,一则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二则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的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对于一部分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民家庭来说,虽然他们从供给制中得到了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得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仅是笼而统之地说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这话自然也不错,也很堂皇,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不好好劳动就对不起共产党,反而觉得共产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民家庭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所以,不论是得好处的一方还是吃亏的一方,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放开肚皮吃饭”(4)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1)
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也同时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各地公共食堂创办之时,无场地、无锅、无灶、无生活必需品,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食堂的遍地开花。那么,办公共食堂所需的各种物品从何而来?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共产风”一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首次使用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该归社的,如大部分的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是由28个农业社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农业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则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这样,原来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
湖南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人民公社好,可惜搞大了。富社与穷社,分别很不少,我社粮食产得多,他社粮食产得少,要想提高生产力,粮食不可平均吃。”可见,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对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表示了不满。
办人民公社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同时也要使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社成立之时,不但要将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农具、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尚未分配的农产品、农业积累的资金,甚至劳动力的使用和调拨,全部转为公社所有,而且还将社员的部分生活资料由公社统一使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河南省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规定:农业社转并为人民公社时,一切公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转社时,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果园和大中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社所有。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公社化后社员的小家畜家禽,可留为社员所有。社员占有的多余的房屋,公社有统一调配权,不得再收房租。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一律归社员所有,公社如有需要,在取得社员本人同意后,可暂时借用。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社化后社员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地全都要交给公社,部分生活资料名义上可以留给个人,但公社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这就为各地刮“共产风”开了方便之门。
公共食堂与刮“共产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办食堂之初,公社除了掌握一定的粮食外,可谓一无所有。食堂办起来后,一方面,所需的锅碗瓢盆、蔬菜食油等等,食堂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使用。不少公社是一夜之间办起的,食堂也是如此,所需之物全部取之于社员个人。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一方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普遍存在可“共”别人的“产”而不可“共”自己的“产”的心理。食堂办起来之后,他们并不会自愿地将家里的东西交给食堂,那时的办法是,趁社员出工之际,由社、队干部到社员家搜查,将发现的粮、油等物品全数收去交给食堂。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判斗争、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在一些地方,为了强迫社员到食堂吃饭,强行将社员的锅砸烂,把碗、盆拿走。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留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在食堂吃饭。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2)
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刮“共产风”的情况,便足以说明“共产风”的厉害。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投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辩论、斗争,并且打人。古云高级社(当时分社还没有建立)就有近20户收到了要钱的条子,被打的有10个人,其中5个是中农,5个是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抢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家家落锁,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由此可见当时刮“共产风”的程度。
公社化后“共产风”有增无减。这年8月15日,石潭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