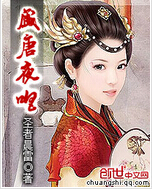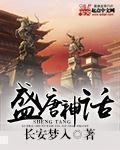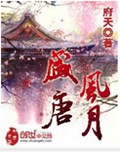印象盛唐-唐才子评传-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送送多穷路, 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 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 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 俱是梦中人。
诗境凄凄惨惨,和上面的诗大不一样,有判若两人的感觉。其实,才子词人的命运凄惨的时候应该更多些。
记得看过一个电影,是说王勃的事情,大概是叫《王勃之死》。剧情当然对王勃的事迹做了很多的改动和自己的想象,还给王勃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但总体来说,电影中的形象是符合人们对于王勃的印象的---少年才俊,风流倜傥。
辣笔诗僧王梵志
初唐时期有一位诗僧,叫做王梵志。上一篇《初唐才俊说王勃》中江湖夜雨说过像寒山、拾得这些诗僧诗虽然也不错,但佛家说教气太浓,人情味却太少。但这个王梵志却不大一样。
王梵志的诗,俚俗如话,在唐诗中可谓别具一格。像什么“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好像现在雪村的“翠花上酸菜”的风格一样,特别独特。说起来,这诗不怕写的俚俗,但如果俚俗中能见到诸多的深意,那就不叫俚俗了,反而是一种比较难得的风格。但比如像传说中韩复榘做的诗:“趵突泉,泉暴突,三个眼来一般粗,突突突突突突。”还有“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蛤蟆一捶一蹦达。”之类,只是一味的老俗话,这就不叫诗了,所以成为大家的笑柄。
又如文革时王铁人写的“牛吃草,马吃豆,死皮流氓吃酒肉,苏联出了大老修,苏联人民把苦受。”之类的诗也差不多,顶多算个顺口溜。再有我们家乡附近的一个名人--武训。他在为修“义学”乞讨时也编了好多此类的顺口溜,像什么:“缠线蛋,结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还有”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等之类,虽然武训先生精神可嘉,但江湖夜雨还是觉得他说的这些不能称之为诗,诗贵含蓄,要有深意才好,不能一览无余,平直如大白话。
王梵志这些诗,虽然多数好像一眼望去也是大白话,和武训的口号差不多,但仔细一品,就大不一样了。王梵志的诗中有深意,有辛辣的讽刺,绝对不能当一般俚俗之作来看。比如王梵志有一诗深刻地揭示了当时贫富的差别,看这首诗写富家人的生活: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横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
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肥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
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
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大概是原文中缺字,王梵志的诗现在看到的,均出土于敦煌残卷,想必有缺失。)
俗话说“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什么差役啦,打官司啦,有钱都好办呀。“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这和“可怜衣上身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情况可大不一样。呵呵,这倒像现在有些炒楼盘的富豪们,才不怕房价上涨呢,反而盼着房地产泡沫吹得更大些。富人对于官司科差是不怕的,不见“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就像现在也是,很有钱的人多生几个孩子,街上撞了人,打了人,无非赔几个钱嘛。官家富户往往在一起形成如生物学上“共生”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都这样。
而穷人家又是一番景象: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两穷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
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
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怒骂,啾唧搦头灰。
里正把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陪。
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
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铁钵淹乾饭,同伙共分诤。
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遣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
富家有钱,这科差劳役都落到了穷人身上,看穷人过的什么日子:“ 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出门就挨里正的打,官府的打,回家还有“丑妇来怒骂”,更有“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以至于这个穷人痛苦到觉得生不如死的地步:“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贫富之分,犹如天堂地狱之分呀。
王梵志可能生于社会低层,有着最深切的体会。其他唐朝诗人,最少也有个官职什么的,也就说最少是个公务员身份,在旧时有了公务员身份,很多劳役之类的就不用服了。像是《石壕吏》中抓走了老太太,却没有抓杜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他人即便如杜甫也没有写出这样惨痛的诗句。
王梵志这一首诗讽刺了只看钱不重情的女人:
吾富有钱时, 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 与吾叠袍袄。
吾出经求去, 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 见吾满面笑。
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貌哨”,指脸色难看)
人有七贫时, 七富还相报。图财不顾人, 且看来时道。
这个说来也是常有的事,苏秦当年去秦国“找工作”失败,回来“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都不答理他,不拿他当亲人了。其实,就算现在,好多女人不也是老公挣了大钱就满心欢喜地甜言蜜语,老公要是倒了霉,没了钱,马上甩脸子给他看。希望女人们也不要太势利了,这样最伤男人的心啦。
江湖夜雨觉得王梵志最为振聋发聩的是《城外土馒头》这首诗: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二十个字,字字平易,但却使人警醒,发人深思。城外一个个坟墓,犹如一个个土馒头,“馅”却在城里,不管城里人是不是嫌它没滋味,都肯定要吃上一个。这首诗中的比喻也新奇无比,大有匪夷所思之感,将坟喻为土馒头,而埋在里面的人自然就是“馅”了(唐宋时的馒头也有馅,像《水浒》中孙二娘那儿的人肉馒头)。像有些评书中骂老头时常说是“棺材瓤子”,倒和这个比喻类似。但评书中常用来写老而不死是为贼的那类人,而这首诗却推广到每一人。其实说来确实是人人都逃不了的。所以这一首诗,不亚于晴天霹雳,当头棒喝。实在是发人警醒,富贵而骄者看到这诗,想必就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一般,打一个冷战。宋代范成大将之化用为“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曹雪芹《红楼梦》中妙玉那样眼高于顶的人,都说这是古往今来的仅有的佳句。虽然这和妙玉的孤僻性情有关,但这诗确实词句警人,非同一般。
王梵志由于不是“公务员”身份,可能也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家世、生平皆不见於史籍。但文人的笔记小说常提到他。冯翊的《桂苑丛谈》说: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今河南浚县)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剥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7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呵,这王梵志倒和孙悟空有一比,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这王梵志是从木头疙瘩里剥出来的。这当然是过于神话了,不可信。
王梵志何时出家?出家后有过什么活动?现在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曾经写过许多通俗诗。他的通俗诗,唐宋时还很流行的。不然范成大如何化用那个“土馒头”的诗句。可是,到了明清以后,王梵志诗却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一首也没有收录王梵志诗,连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的王梵志诗也不收录,幸好本世纪初于敦煌佛窟出土了20多种唐宋时期的王梵志诗手抄写本残卷,经过整理、校辑,共得诗336首。以上我们看到了那几篇好诗也重见天日。
王梵志的诗虽然没有其他唐朝诗人的华贵、典雅、工整、清丽,但他的诗深刻、通俗、辛辣、幽默,在唐诗独树一帜,实在难得。
摇笔云飞看婉儿
大唐盛世中,是中国历史上女人们比较有地位的一个朝代。唐朝时的公主、贵妇很多,而且很大胆开放,并且参与政事,权力很大。所以在唐代的一些传奇故事中常有“后土夫人”、“太阴夫人”之类贵妇人纳漂亮男生的这种故事,其实故事都是取材于生活的,正是反映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这篇,我们来看一个一生接近于最高权力中心的美貌才女,她曾像神话中的文魁星一样掌管着天下文宗,让我的思维追到千年以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巍峨富丽的宫室中,奇珍美酒的盛宴前,一群人正搜尽枯肠、搔短头发来吟诗作赋。他们可不是寻常的文人,他们或是文臣,或是昭文阁的饱学之士,但在这九五之尊的御宴之前,还是不免有些紧张,有些人更是“战战惶惶,汗出如浆”。而怡然高坐,美艳高华的那位美人居然是评判他们的文章的最权威的“评委”。她,就是上官婉儿,后人称之为上官昭容。
这昭容,本是宫中的“职称”,据史料载:“宫中位号十有四品。昭仪、昭容、昭华、保香、保芳、保衣、安宸、安跸、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士大夫。”而在唐朝上官婉儿那时候,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的女皇帝武则天当年就是昭仪,所以昭仪这个封号可能当时就暂时不用了(仿佛国民党中孙中山称总理后,其他人不再称总理一样)。所以这昭容可能已是宫中职位的极品。
上官婉儿入宫的情况也很有传奇性,上官婉儿家学渊博,乃是上官仪的孙女。这上官爷爷的诗虽然江湖夜雨一样不甚喜欢,但上官爷爷毕竟也是一代文坛人物。但也正因为这样,上官仪被武则天所恶(据说是上官仪被武则天的老公李治召来让他起草废掉武后的诏书,估计武后的耳目极多,武后突然就及时出现了,脓包皇帝李治吓得魂不附体,就说全是上官仪的主意),下狱被杀。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一同被籍没入宫为奴。当时上官婉儿只是个小小婴儿。据说当年她母亲怀她的时候梦见神人送来一杆大秤,占梦的说这预示着上官婉儿将掌握大权衡量天下大事。(《刘宾客佳话录》:(婉儿)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汝耶?”呕哑应曰:“是。”)
到了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已出落成了一个美貌如花、才华出众的才女。上官婉儿这一年被武则天召见宫中,当场命题,让其依题着文。上官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武则天看后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分,让其掌管宫中诏命。据说当年高宗李治宴群臣(想必武后肯定也在),赏双头牡丹诗,上官婉儿一联云:“势如连璧友,情若臭兰人。”(这里臭兰,其实是香味,大家可不要以为是臭味哦,呵呵。语出《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应该说写得很不错。
后来上官婉儿少年气盛,又因违忤旨意,罪犯死刑,但武则天又加以宽恕。此后婉儿算是活明白了,可能人生观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后上官婉儿就精心伺奉,曲意迎合,深得武则天欢心。更被武则天提拔为贴身秘书,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呵呵,这能够上达天听,接近至尊的角色往往不可小看呀,在一言九鼎的至尊面前,说上一句好话和说点坏话,那可天差地别。原来腐儒的经书里说什么“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铖”,其实在吹牛,《春秋》那东西无所谓,后人足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本领。而在当时婉儿在武则天面前的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贬,确实可当此说。呵呵,想必当时给婉儿送礼巴结的也不在少数。
当然,武则天是什么样的人物,权柄也不会全由上官婉儿把持。说起来上官婉儿在武则天面前地位还是很低的,不是说有一次,武则天和婉儿及武则天的“男妃子”张昌宗、张易之一起饮宴。要说二张也是经过全国选美挑出来的,当然也是极品帅哥。武则天不是赞过“莲花似六郎”(六郎指张昌宗)嘛。婉儿也是个有情有欲的女儿身,不禁贪婪地多看了几眼,大有垂涎之意。武则天眼里可不揉砂子,瞧见婉儿的这种神情就当场大怒,拔下一枚玉簪就掷向婉儿,正中婉儿天目穴(呵呵,这里说的武侠化了,就是两眉中间),婉儿当然敢怒不敢言,眉间落下了个伤疤,婉儿就剪了花瓣贴住,后来反而成为宫中的一种时髦打扮,有的宫妃眉间没有伤痕,也贴上个花。
也许是压抑的太厉害,等到武则天死后,上官婉儿大大地“性解放”了一番。她先是和唐中宗有了关系,又与武三思淫乱(当然,也有记载说武三思是武则天指配的)。说起来,上官婉儿的情形也很特殊,原来职位就是宫中嫔妃,但当时武则天称帝,她不是男人,这嫔妃当的徒有虚名。中宗即位后,宫里的女人像婉儿等就照单全收了,而且上一任皇帝是他的老妈并非老爹,也不存在子占父妾的问题,这上官婉儿居然却乐得“身兼两职”。而且让人惊奇的是,唐中宗的皇后韦后也和武三思不清不楚地淫乱,我靠,这简直是皇宫里的一个换妻俱乐部。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当然也是个有名的“小太妹”,本来是嫁武三思之子武崇训,但安乐公主不喜欢他,倒泡上了他那堂弟--漂亮的小白脸武延秀。有记载甚至说安乐公主甚至还有时把武延秀“孝敬”给她母亲韦后玩玩。靠,唐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