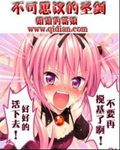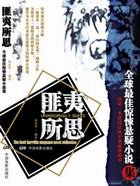马克思-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871年夏天,得以回到伦敦的公社社员欧仁·鲍狄埃,随身带着一首在流亡期间写下的诗。一年以后,这首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赞歌,成了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账!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既要从事紧张的理论创作活动,一面校订《资本论》法译文版,一面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积极作准备,他还要负担繁重的国际领导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国际领导工作:除了出席总委会每周在拉脱本广场举行的例行会议,为总委起草文件、宣言外,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答复大量的来信,参加在自己家里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的总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有时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开就是9个小时。为了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早日实现国际组织期待的《资本论》全部面世,他在恩格斯搬来伦敦后,主动把国际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恩格斯身上,并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辞去了国际领导职务。国际总委会也从伦敦迁往纽约。
海牙会议,马克思54岁,恩格斯52岁了,德国工人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其他许多先锋战士却把他们俩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方面德高望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位“老人”,并常把他俩尊称为“二老”。
长期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这位54岁的伦敦“老人”也确实早见衰老了,乌黑的头发和鬓须明显花白了,只有上唇胡须还依然乌光发亮而显出其?烁精神来。
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1873年底,马克思脸部等处又长了许多痈,动了手术;不久,原先没有痊愈的肝病又急性发作,使马克思几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坚持要马克思到离伦敦较远的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去疗养,因为那里的矿泉水对马克思恢复肝的功能和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会有疗效。
卡尔斯巴德是一个景色幽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它的城保山街,有一座较豪华的旅馆“日尔曼尼亚旅馆”。1874年8月19日,在旅馆登记簿上,出现了一个“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为了迷惑奥地利警察而用的化名。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了“显贵的外表”。尽管如此,十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为反动派知晓。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马克思按计划在卡尔斯巴德疗养了一个多月。他与爱琳娜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生活制度,每天定时起床,定时到各自的矿泉去喝矿泉水,定时进餐、散步、就寝。生活有规律,玩得也愉快。马克思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每到一个新游览的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与他同路人见到的更生动。
经过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5年和1876年,马克思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每次疗养都能收到一定疗效,对健康的恢复有所帮助。1877年他本来打算再去一次,但听说奥地利政府可能不让他在境内停留,这样他就可能白花旅费,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国家工联会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信。获悉国际总委会迁往纽约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和巴枯宁分子从内部搞分裂,这个作为欧美工人运动首脑机关的作用在日趋减弱。
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已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组织中退下来成为了真正的“伦敦老人”,但他在国际的威望已无须组织职务形式上的附加影响,他依然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国际,马克思回答说:“这种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宣告解散。宣言说:“由于现代欧洲政局所引起的种种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组织虽然解散,组织的原则却已得到整个文明世界进步工人的承认和拥护。让我们给我们的欧洲工人同志一些时间来加强他们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拆除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
在国际解散之后,伦敦“二老”始终同革命运动连结在一起,他们“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组织:1875年,葡萄牙着手筹建社会党;1876年,美国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1877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比利时、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先后建立起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也是“二老”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十周年时断定,俄国革命的发展,“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马克思还虽然只能经历那个由巴黎公社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然而,“二老”已看到了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内生根。这些思想已开始被群众所掌握而变成一种物质和精神合力,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权能够忽视它。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的画像同朱泽培、加里波第及维克多、雨果的肖像一起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自己不争名,可是你毕竟逐渐地成了‘当今的英雄’。”
第29章 晚年·最后的岁月(3)
1872年,为了德国的需要,必须准备出《资本论》的修订再版了,计划印3000册。人们对《资本论》的兴趣在不断地增长。1871年4月,马克思又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德国全国各地都在根据你的《资本论》作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工作日问题上将进行一次群众运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消息,使马克思和燕妮深深感到,他没有白费气力,她也没有白白过了多少年贫穷日子,工人们在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时正学着把《资本论》当做进攻武器……“老人”的心真是得到了最高的奖赏。
朋友们一再催促马克思快点完成《资本论》的后面几卷。这虽然符合他本人的心愿,但是却困难重重。校订工作是不能不做的,更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的指导。
马克思病情日趋恶化。他在1872年以后的几年里顶住疾病的侵扰,还断断续续地撰写《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只要感觉到自己一有点好转就把精力用于《资本论》的研究上。
在晚年,马克思研究的科目之多和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2立方米。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学方面的所有重要现象,此外他还研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
直至1878年,马克思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学习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年起至逝世前,他专心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了拉克鲁瓦、麦克曾林、欧勒、波茨的论文,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札记。
他还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继续探讨60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阅读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研究了并摘录了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等人的著作。
80年代初,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论文。这时恩格斯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为此马克思把《论微分》献给了恩格斯,他在存放手稿的袋封上写着:“给弗雷德”。
恩格斯看了马克思写的论文和札记,发现他数学方面也很“精通”,也有其“独到的发现”。
马克思除了撰写《资本论》二三卷的初稿外,70年代、80年代的著作、书信及谈话始终贯串为人民民主权力、为民主德国共和国而斗争的一条红线。伦敦“二老”身居异国念念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人民的最后解放,德国工人民主党领袖与晚年的马克思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在1871年8月,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新生的儿子就起名“卡尔”以纪念马克思这位“伦敦老人”。对此,两名身处祖国内外的德国工人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也共同承担了对“卡尔”的辅导之责。当时的李卜克内西和伦敦“二老”谁都没想到这个男孩有一天会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
燕妮病了,病了很久,年轻的丰润、漂亮瘦得只能依靠想象了,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确诊。1880年以来常卧床不起,怀疑是肝癌。
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的矿泉疗养地被反动政府切断了。1878年以后,身体也经常出毛病。完成《资本论》二三卷才真正成为这对老夫妻的医病“良药”。
马克思的头发已白过了胫窝的发梢,连在鬓发和下巴胡须上,孙子们也再找不出一根黑丝来,上唇的胡须也开始花白。马克思更加“黑”、“白”分明了,但从外表的刚毅、顽强,丝毫还看不出这位“雷公神”老人身上包裹着多种病痛。
那头上雪白的一朵云,又匆匆飘去了英国博物馆……
一天,天色昏暗,燕妮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琳蘅坐在她的床头,给自己宠爱的“外孙”织小袜子,她一针一线、一心一意无私地为这个圣洁的家庭编织着欢快,从不留意和后悔自己已苍苍白发。这时她编织的是同恩格斯和这一家大小一样的为燕妮的焦虑和不安。她替燕妮病情难过,更为燕妮一旦不测担心会给马克思这位国际首脑人带来绝望。
燕妮在沉思遐想,脸上的颧骨让她脱了美貌,然而病痛也掩饰不住她不时漾出的轻盈、温柔的微笑。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尼姆?”
“想的是早日恢复健康呗。”琳蘅回答她。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便又大声地咳嗽起来。
“不,琳蘅,咱们还有什么可以互相哄骗的呢。难道你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吗?你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但还要更加坚强。当我不在了的时候,你应该去扶助可怜的摩尔。他在许多日常琐事方面,不是简直像个大孩子吗?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考验哪。我非常担心他是否能经得住。你和恩格斯要帮他坚持下去。唉,不要这样大声的擤鼻涕啦。我们不谈后事了。你知道,琳蘅,我今天一直在回想摩尔以前赠给我的诗。他从来不是个好诗人,不过,他把多少真挚的情感倾注在诗句里啊!”
“他过去和现在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琳蘅说。“我也是这样,我亲爱的燕妮,不过我倒很想见着一个竟连马克思夫人这样的妇女都不爱的人呢!”
“这就是瞎说了。好了,好了,别生气,卡尔还需要我,你和孩子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需要我,我绝不想死。绝不。我要活下去,你相信我吧。”
这时,燕妮从枕下拿出手抄诗的小本子,琳蘅把床头柜上的灯挪近一些,她俩就又像年轻时又在威斯特华伦家读起19岁的青年马克思献给燕妮的几首十四行诗来——
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取笑这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歌初作。
“粗糙的作品。演说术式的、软弱无力的论说。”马克思谈到自己的诗时,总是这样说。
“然而,这里面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爱啊!”燕妮又在心中暗自反驳他的看法。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的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像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