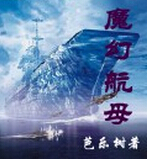航母:十万火急!-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夏一琼不禁笑出声来,“你刚四十多岁就称自己为朽木,言之过谦吧。”
瓦西里紧皱眉头,耷拉下眼皮,做出一副衰老俏皮的模样,说:“我是圣诞老人……”
夏一琼看了,笑得更响了。
瓦西里问:“一琼,今天晚上快乐吗?”
夏一琼真诚地点点头,“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
几天后,夏一琼走进了瓦西里居住的小别墅。
这是一个幽静的晚上,瓦西里把客厅里的电唱机打开,播放着《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俄罗斯歌曲。茶几上摆放着香蕉、苹果、鸭梨等水果,两个人在长沙发上谈笑风生。
客厅的正面有一架黑色泛亮的钢琴,西侧有两个书架,摆放着有关航空方面的书籍。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铜版画,画面上是彼得堡的冬宫。
夏一琼说:“你这屋里陈设太简单,我可以帮你布置一下。”
瓦西里翘着二郎腿说:“我的苏联的家居布置就是这么简单朴素,不像你们中国。墙上一般不挂什么东西,都是白墙,家具也很简单。”
夏一琼说:“应当中西结合,我以后给你拿一些剪纸、年画过来,对,跟我舅舅求一副钟馗画儿,挂在客厅,驱魔辟邪!”
“你说的钟馗就是那个瞪着眼睛,满面大胡子的家伙,我看着可有些害怕……”
“那你肯定心里有鬼了!”夏一琼纵声大笑。
夏一琼走进瓦西里的卧室,只见被褥凌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大衣柜,地上堆着几个书箱。
她走进卫生间,只见浴缸里堆着一撂瓦西里穿过的衣物,像小山那么高。她不由分说,把衣物拿到洗衣池里,拿过肥皂,洗起来。
瓦西里闻讯赶来,脸色飞红,急忙说:“真是不好意思,整天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
夏一琼说:“再忙这些衣服也要及时洗出来,不然该有味了。”
瓦西里红着脸,在那些衣物中摸索着。
夏一琼转过身来,问:“找什么呢?不会有卢布吧?”
瓦西里揪出自己的内裤和袜子,扔到旁边的一个盒里,“这些你不能洗,让我处理吧。”
夏一琼看到他一副尴尬的样子,觉得很开心。
转眼到了夏天,这天是星期日,瓦西里、夏一琼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
上午10时许,他们来到昆明湖南岸,许多人正在湖里嬉游,花花绿绿的游泳衣让人眼花缭乱;游船在不远处穿梭,阳光照耀下,湖面上泛着鱼鳞般的波纹。远处,玉泉山巍峨的宝塔隐约可见,十七孔桥像一条白虹历历在目。
瓦西里和夏一琼换上泳装跳了下去。瓦西里游蛙泳,夏一琼游蝶泳,两个人像两尾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行。
夏一琼望着绿树掩映的金碧辉煌的佛香阁,非常惬意,她奋力朝佛香阁游去。
瓦西里大声叫道:“别往那里游,危险,那边水深……”
话音未落,夏一琼沉了下去,转瞬不见踪影。
瓦西里一见,顿时慌了。
“一琼!”他奋力向她下沉的地方游去。
瓦西里血液沸腾,全身都在颤抖,他有一种不祥之感,用自由式泳法奋不顾身游着。
瓦西里正游间,忽然触到了一个软软的物体,那物体像白鸟一样在水里浮动着。他拼力抱住了她,游出水面。
夏一琼双眼朦胧,就像失去了知觉,她的头发披散开来,像一道瀑布,她温热的身体紧紧贴住瓦西里宽厚的身体。
一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在瓦西里全身浸染着,几乎渗透了每一根神经。每一颗细胞;多少年来,这位俄罗斯汉子一直渴望着这种感觉,他兴奋地几乎晕厥……
游到岸边时,夏一琼才努力睁开清澈的大眼睛,“瓦西里,谢谢你,我的脚抽筋了……”她用双臂紧紧地搂定了他。
晚上,在瓦西里居住的小别墅里,在那宽大的皮沙发上,瓦西里眼里噙着热泪,对夏一琼说:“一琼,我们能不能发展到比同志和朋友更进一步的关系?……”
夏一琼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扑到他的怀里,喃喃地说:“我们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我甘愿把我的一生都托付给你……”
瓦西里泪如雨下,与她吻如雨下。他就像一头咆哮的雄狮,撕却她身上的一切衣物,把她彻底地驾驭了,让她真正地做了一次女人……
当瓦西里醒过来时,看到精赤条条的夏一琼,正扬起红艳艳的瓜子脸,朝他微笑。他一低头,看到床单上有一团湿湿的红迹。
“怎么?你26岁了,还是一个处女?”他惊得张大了嘴巴。
她点点头,就像一个见到稀世古玩的收藏家,笑吟吟地欣赏着他褐色石雕一般的雄壮胴体。
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夏一琼把瓦西里带进了舅舅秋千素的家。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画家秋千素住在西厢的两间房内,门口栽种着几棵向日葵,还有一株石榴树。
秋千素和他的妻子、中学音乐老师梁素音见到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男人,一下怔住了。
“这是我们所里的苏联专家……”夏一琼把瓦西里推进屋里。
第5章 专家死了(3)
北京的夏天炎热,有时连一丝风也没有,房屋里的角落里有一台旧电扇旋转着,送来一阵阵风。
“对,老大哥,老大哥……”遇到秋千素夫妇迟疑的目光,瓦西里显得有些紧张,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他会说中国话吗?”秋千素问夏一琼。
“会说一点,我来翻译。”夏一琼回答。
瓦西里在藤椅上坐下来,梁素音端来暖壶,沏了北京花茶,她把一个茶杯放到瓦西里面前。
“我知道,你们欧洲人都喜欢喝咖啡,我这里没有咖啡,只好用北京的花茶招待您了。”她呐呐地说。
当夏一琼把这段话翻译成俄语对瓦西里说后,瓦西里笑了,他说:“我很喜欢喝中国的茶水,中国茶是一种神奇的树叶,世界闻名!”
夏一琼也笑了,“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是带着大批中国的茶叶盒丝绸运往中东和东非,换回许多那里的特产。”
秋千素说:“中国福建许多地方整日雾气环绕,适宜盛产茶叶,像大红袍、碧螺春、六安瓜片、信阳毛尖、黄山毛尖等。”
瓦西里吟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
秋千素说:“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是吃翠花楼,还是吃东来顺?”
夏一琼连忙摇手说:“不用,不用,就在家里吃舅妈做的老北京炸酱面。”
瓦西里也点点头,说:“对,炸酱面!炸酱面!”他听得懂“炸酱面”3个字。
梁素音火急火燎地上街买面条和黄酱去了。
屋里的3个人叙了一会儿,夏一琼忽然想起什么,“舅舅,能不能送瓦西里一幅你画的钟馗画儿?镇宅用。”
秋千素点点头,“可以,但是按照老规矩,佛道人物都要请,请则灵。瓦西里也不用送什么钱了,下次再来给我带一刀安徽泾县产的四尺生宣宣纸就成了。”
夏一琼说:“没有问题。”
秋千素领他们走进里面那间卧室,只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儿和一幅书法,画儿的画面是孔子和老子盘膝而坐品茗叙话,题款是:孔子和老子——两个圣人的心灵对话。是秋千素写的行书,旁边还有他写的一首五言诗:风急寒舍深,古栈锁白雪。飞流泻千尺,一步一失魂。
夏一琼问:“舅舅,你怎么没有挂钟馗的画儿?”
秋千素笑道:“你舅妈说,整天看钟馗,她害怕。”
秋千素从墙角一个竹篓里抽出一幅轴画,展开了,只见画面上的钟馗手持宝剑,精神抖擞,横眉竖目,正气凛然。
“把这幅送给你。”他把画儿卷好递到瓦西里手里。
瓦西里不迭声地说:“谢谢,谢谢。”
瓦西里到外屋喝茶,秋千素把夏一琼扯到里屋,小声说:“我看他跟你关系不一般,已经超过一般关系……”
“怎么了?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
“他可是苏联人呀!外国人!”
“苏联人也是人,爱情没有国度,不分地域!”
秋千素神色变得严肃,“你可要慎重一些,你父母去世早,我可要对你负责。他比你大那么多……”
夏一琼眼睛里闪出火花,“爱情也不论年龄,燕妮比马克思还大呢,他比我大20岁,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舅舅,你希望你的外甥女得到幸福吗?我和他在一起很幸福,我终于找到了这种感觉,我会为爱做出全部牺牲,我不管那么多闲言碎语,世俗之见!爱情不朽!”
夏一琼愈说愈激动,脸涨得通红。
梁素音提着菜篮子回来了,秋千素急忙拉着夏一琼走出里屋。
梁素音炸酱的手艺果然不错,她切的小萝卜丝更是细腻齐整。瓦西里吃了两大碗面条,还喝了一大碗面汤。
回南苑的路上,瓦西里余兴不减,一边驾车,一边唱起俄罗斯歌曲《三套车》。
夏一琼坐在他的旁边,“什么‘这匹可怜的老马’,你换一首抒情些的歌曲。”
“好,我唱《卡秋莎》……”说着他又唱起了这首寓于浪漫的歌曲。
车到南苑,一进瓦西里的小别墅,瓦西里兴奋难禁,就把夏一琼扑倒在地板上。
“一琼,嫁给我吧!”他恳切地说。
“可是你是有家室的人……”夏一琼呼吸急迫,高耸的胸脯一起一伏。
“我跟她离婚……”
“可是人家不跟你离……”
“不离也得离,我和她之间没有爱情,这是不道德的婚姻……”
夏一琼眼睛盯着天花板,“我不在乎婚姻,那只是一张白纸,我讨厌家庭。我们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就够了。从身体到灵魂,从外表到内心;你现在是我的情人,将来还是我的情人,我们永远是情人!没有家庭的束缚,没有国界的障碍,没有语言的隔阂,我们永远是幸福的!”
“对,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要把爱情的种子,插进你的身体!……”瓦西里喘息着,战栗着,颤抖着,他用尽全力,疯狂地剥脱夏一琼的衣裙……
人的一生,有幸福,亦有痛苦;有欢乐,亦有忧愁;有清醒,亦有困惑;有顺利,亦有挫折。
1957年的夏天,夏一琼发现了一桩令他十分羞辱的事情。
研究所新调来一个党支部副书记,他叫王树城,高高的个子,肤色黝黑,满脸的青春疙瘩,戴着一副眼镜,约有三十多岁。他平时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夏一琼透过他薄薄的镜片,发现他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总在她的身上游动。
王树城经常溜进医务室,与夏一琼搭讪,找她“看病”。
这天下午,王树城一脸痛苦地神情,神秘兮兮地推开了夏一琼工作室的房门。
“王书记,哪里不舒服?”夏一琼放下手里的听诊器问道。
“难以启齿……”他呿嚅着说。
“对医生有什么保密的。”
他指指下身,“我这里肿了。”
“把裤子脱了,上床,我看看。”
王树城听了,喜出望外,一骨碌上了床,脱下裤子。
他的阳具直挺挺地矗立着,有些红肿。
“怎么搞的?”夏一琼问。
“我也不知道,你给看看。”
夏一琼戴上软胶手套,仔细端详着。
“涂点消肿药吧,这几天就尽量别沾水了,防止感染。”
“那我撒尿怎么办?”
“该尿就尿,尽量别沾水。”
夏一琼给他的阳物涂了一些消肿药膏。
“现在看来还不够严重,如果严重了再打针。”
王树城心满意足地走了。
原来他故意用辣椒水洗了自己的阳具,因此红肿。
研究所的公厕在院子里,左为男厕,右为女厕,坑位之间用木板搭成,中间有墙壁相隔,下面粪便和尿液相通。
一次,夏一琼在如厕时,发觉下面有镜子的反光,她有些恐惧,又觉得奇怪;于是把这一情形告诉了瓦西里,瓦西里也感到奇怪。
这天中午饭后,夏一琼又走进女厕如厕。
忽然,她听到旁边男厕内瓦西里一声大吼:“你在干什么?”
一会儿,听到王树城哀求的声音:“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替我保密,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瓦西里吼道:“你这个流氓,你竟敢照我女人的屁股!……”
夏一琼听到几声扇耳光的声音。
只听王树城说:“我叫你爷爷了,千万别给我说出去。我是党支部副书记,在农村还有70岁老母亲,还有媳妇和孩子。您多体量,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我实在是饥渴呀!……”
“混账东西,以后再让我撞见,我把你的屌子割下来!”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当晚,在瓦西里的房间里,他向她叙述了白日看到的情景。
原来在夏一琼走进女厕后,在附近走廊拐角处,瓦西里看到王树城从另一处也尾随进了男厕。瓦西里立即跟随进了男厕,只见王树城一只手扒住坑位旁边的踏板,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的一头有一面小镜子,他全神贯注,头都伸到坑位下面。
瓦西里明白了,他正用小镜子看对面女厕内夏一琼的私处……
他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揪住了王树城,把他摔倒在地上……
夏一琼听了,羞得满脸通红,心“砰砰”乱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
“瓦西里,我已经不纯洁了,那么宝贵的地方让那个流氓的眼睛玷污了,我对不起你……”她泣不成声。
“我已经惩罚他了,他再也不敢冒犯你了。”瓦西里抱紧她,在她的脸上印了几个吻。
“瓦西里,你太善良了,就这么便宜了这家只色狼!”夏一琼恨得咬牙切齿。
“还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不然,他连饭碗也没有了,何况他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妻小……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但是夏一琼的命运并没有应验“善有善报”的许诺。1958年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一场“反右”斗争开始了。根据当时的方针,右派人数有指标。研究所的这个指标,由王树城提议给了正直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