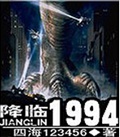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大队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12'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共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令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13'对共产党方面的反应,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17'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20'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22'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