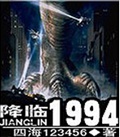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完结】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每个人却生存在自己的际遇里,它游离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视线之外,却真实无疑地发生着。《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就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人写真,它栩栩如生地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等人定格,交叉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复杂心态,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立体的图景。
目录
序
影响近代史的出版家:张元济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金融巨子:陈光甫
两党争夺的对象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诗人、革命家:柳亚子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无事忙”贾宝玉
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
离开浙大,决不去台湾广州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武汉大学怎样了?”
浩然一儒者:梁漱溟
“只发言,不行动”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一代词宗:夏承焘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人生五十是开端”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从“地下”走到“地上”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胡风
一生“甜美的高峰”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
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
序
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固然也在杨刚、子冈、浦熙修她们激扬文字的通讯中,在李普他们笔墨饱满的报道中,在胡风等澎湃的诗行中,但这些当年公开的文字呈现的只是大时代兴奋、激动、热烈、欢呼的一面,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身处大时代的人们,他们个人内心的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以及命运的起伏,看不到他们私下的评判。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
写一本关于1949年的书,我最初生发这个念头,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刚读了蒋经国1949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这是失败者私下的记录、心灵的独白,与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辩白、言不由衷的对外言说不一样,这里有失败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有他在政权覆灭之际的痛苦,有对故土铭心刻骨的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告别,有对权力浮沉的反省,有对败亡原因的思索与探究……特别是4月25日蒋氏一家泪别故乡溪口时的情景,在蒋经国的日记里有生动的记录: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卢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每次读到这段日记,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中曾出现过的一个镜头,蒋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岛的军舰上,蒋介石的孙子背诵李煜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那一刻,萦回在蒋氏家人脑海里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词句,至少符合他们内心的真实。我没有见到过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从他儿子的日记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踪,更可以看出其心情,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之雾。
与此相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没有日记,但有他留下的书信和诗词为证,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天安们城楼上挥手的姿态、与“毛主席万岁”遥相呼应的“同志们万岁”一同汇入了历史的洪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陆续读到了胜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记,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陈赓日记》中有他1949年3月11日到6月16日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儒将从河南漯河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军旅生涯,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4月25日,“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以扫其兴。尤其沿途敌人遗弃之辎重、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这样的文字超越了文学的想象的,如非亲身经历绝对写不出来。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有他1949年的日记,一直到10月1日为止。作为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个转折的年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比如4月27日,游玩了一天颐和园之后,他在日记中说:“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可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后来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7月7日,谢觉哉给周谷城回信,因为“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他复信表示“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杨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显要,记录的都是胜利一方的决策内情、高层迎来送往的动态等等,比如1月12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后秩序井然,就是一个重要细节。比如1月20日华北局、华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说话内容还好,表示与我党之间无距离。”杨刚、吴晗、楚图南、胡愈之等发言,“一般政治态度均好,表示愿与我们一致,把革命进行到底,警惕蒋美阴谋,在革命阵营中搞反对派。”可惜他1949年的日记只到3月31日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
在失败、流亡的阵营中,王世杰1938年之后的日记比较完整,台湾也出版过影印手稿本,遗憾的是1949年这一年他却没有日记。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国在华人士的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6期曾刊载司徒雷登1949年的“百日日记”,从4月23日南京易手到8月2日他飞离南京止,这100天间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通过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特殊关系与胜券在握的中共有过接触、沟通,他的日记与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相互参证,可以揭开当年的许多外交秘闻。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年到1949年间正在北京访学,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见证了大时代的风云,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的“走向中国丛书”收入了他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写一本1949年的书,透过不同的人所记的日记复原时代的记忆,书名就叫做《1949:日记中的中国》。大约几年前的春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西湖边的苏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说出了这个想法,朋友认为很好,值得去做。之后,我便继续留意收集有关的日记,前后大约找到了二三十种。到了2002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写一本全面反映1949年变化的书,凭现有的准备和占有的材料是不够的。
“究竟有多少人对新政权依旧抱有敌对态度?这一点当然无从得知。我所能说的就是最近我所听到的对政府的公开批评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应邀出席了一次豪华的宴席,在座的还有七八位老学者。丰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来,席间的交谈却是一阵接一阵的牢骚和批评。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被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可是在宴会上却能听到对他们的讽刺,‘机会主义者’这个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间被提及。新的左派学者更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某某人的风格不够高雅;某某人的学识太浅薄,等等。”
当我在德克…博迪1949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段话,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写一本《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毕竟留下日记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们在巨变中的心态意绪,他们在新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选择,他们对自身和对时代的认识……都是饶有趣味的题目。
最后我选定了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的15个知识分子,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对我,这只是一个尝试,如果能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那我就很满足了。我将永远感谢读者、出版者和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没有你们,或许世上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影响近代史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底,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 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为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3'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