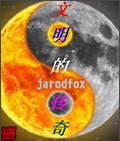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标新立异,而是前人的道理不能苟同;相同或不同,不能以古今区别,唯一的原则是要看是否正确。这样,刘勰对古今的成说,蓖梳剔抉,取精用宏,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批判,在前人基础上,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和灵感问题,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首次触及,这在文学批评史上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但陆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刻、条理,用刘勰的话说就是:陆机《文赋》,讲得虽然巧妙,但有琐碎杂乱之嫌。刘勰就在《文赋》的基础上引申发挥,结合前人的创作经验加以系统化,写成《神思》篇,作为他论述创作问题的总论。
对于一门学问,确定明确的研究对象,拿出精湛深刻、令人信服的见解或结论,固然是重要的;建立这门学问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则更为重要。
没有一个理论的体系,就是有许多至理名言,也还不能说建立了一门学问,也不可能吸收容纳前人的优秀成果;没有一套研究方法,也难以推导出深刻的结论。这正如制造精美的产品必须有精致的工具,打胜仗需要有精良的武器。理论方法,就是工具,就是武器。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真是至理名言。《文心雕龙》所以能够“为世楷式”,除了它“弥纶群言”以外,还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而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它以后的众多文学理论著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或问题上有更加精辟独到的研究,但就体系的宏大、完整、严密而言,都不能与它相比拟。
《文心雕龙》全书包括50篇文章,共三万七千余字,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全书体系的大框架分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五篇,讲贯彻全书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总论,作者称之为“文之枢纽”。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各类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是文体论。这一部分包括从第6 篇《明诗》至第25篇《书记》,共20篇。前十篇讲有韵的文体,后十篇讲无韵的文体。南朝时通常把众多的
文体归纳为两大类:有韵之文称为“文”,无韵之文称为“笔”。所以,作者把这一部分称为“论文叙笔”。在这一部分中,分别讨论了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4种文体。若再加《辨骚》篇中的骚体,共35种。第三部分,包括从第26篇《神思》至第44篇《总术》及第46篇《物色》,共20篇,专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是创作论。在这一部分当中,涉及到艺术构思问题,客观外物与情感、语言三者间的关系问题,艺术风格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熔意与裁辞问题,用典问题,比兴问题,夸张问题,声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情(内容)”与“采(形式)”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作者把这一部分称为“剖情析采”。第四部分,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从文学的演变历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几个方面讲文学评论,可以称为批评论。第五部分就是最后一篇的《序志》,是全书的总序。古人著书,总序放在卷末,如司马迁的《史记。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便是这样。《序志》中说明了作者创作《文心雕龙》的用意和全书的体系结构。
在上述那样一个大的体系框架当中,《文心雕龙》的每个部分,及每部分当中对每个问题的研究,也各自都有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体系结构;换句话说,对它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建立和阐释了一套理论的概念和范畴。除体与性、风与骨、通与变、体与势、情与采、熔与裁、隐与秀等对立统一的范畴作为重大问题专篇讨论以外,在讲到风格时,就提出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而且解释了每种风格形成的原因和构成的因素;在讲构思时提出了神与物、言与意的范畴;讲文体的新变问题时,提出奇与正的范畴;讲夸张问题,又将夸张概括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与“夸过其理,名实两乖”两种,等等。这样众多理论概念和大小范畴的建立,使全书每个微观局部显得“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从而也给读者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法或工具。如果你精心观察一些著名的建筑物,譬如北京的雍和宫和其他许多殿堂楼阁,你会觉得,这些建筑物外观宏伟,其内部每一根梁、柱、檩、椽不仅配搭得和谐美观,而在其力学结构上又是多么合理,多么不可缺少,你会为设计者的匠心而惊讶。
同样,当你剖析《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你会感到“体大虑周”这四个字的评语是何等的恰如其分!篇幅所限,仅举两例以观其布局结构的匠心。
如,文体论部分当中,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一律都遵循四条基本纲领进行:1。“原始以表末”,即追溯该文体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2。“释名以章义”,即说明这种体裁名称的来源和意义;3。“选文以定篇”,即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评论;4。“敷理以举统”,即在前三项的基础上,阐述其写作道理,总结出它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这样,使文体论各篇不仅是讨论某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规律,同时又具备了各体文学史的性质,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再如,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自古就是个大问题。俗话说“知音难逢”,正像一个人真正被别人理解或真正理解别人,都是不容易的。文学批评史上常有“竞今疏古”或“贵古贱今”的风气,更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批评者的爱憎好恶、品德修养、学识高低、阅历浅深,各不相同,而文学作品又是各式各样,变化万千,不可能有全能的作家。所以刘勰认为,这都使
文学批评很难做到恰如其分,正如常有错把凤凰说成野鸡、把珠玉视为碎石、把麒麟当作獐子的现象一样。如班固和傅毅是同代人,作品水平差不多,而班固却讥笑傅毅“下笔不能自休”;陈琳与丁廣各有千秋,而曹植却贬低陈琳,赞赏丁廣。 像楼护信口雌黄,竟说司马迁是学习东方朔,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又认为,混乱的批评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被埋没,刘歆担心扬雄的《太玄》会被人们拿去盖酱坛子,实在不是多余的忧虑。对此,刘勰深为感慨和惆怅。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知音》篇,提出正确的文学批评,首先要客观地反映作品实际,不能怀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的偏见,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第二,批评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说:“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第三、应当做到“六观”,即从六个方面去观察分析作品:“一观位体”,即看作品的内容、思想、情感与其选择的体裁是否恰当:“二观置辞”,即看文辞在表达思想情感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即看其对前人的优秀创作是否有所继承和创新:“四观奇正”,即看其在文体的新变问题上,是一味追求新奇,还是既新颖而又不违背正常法度:“五观事义”,即看其举例或运用典故是否恰当:“六观宫商”,即看其音韵声律是否谐美。刘勰提出按上述六个方面进行文学评论,是否已经全面而深刻,可以另作别论;仅就其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方法而言,就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进步。
珍宝不朽反而愈辉《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对它以前的文学发展历史、创作经验、理论成果的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这一体系中所包涵的理论概念、范畴,有许多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文学或美学的理论语汇当中,如文思、意象、风骨、情性、文采、壮丽、新奇等。我们今天有些术语由《文心雕龙》术语的变化和发展而来,如《熔裁》篇“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辞谓之裁”。这里说的“熔”,就是今天所说的“提炼主题”,或“提炼中心论点”;这里说的“裁”,就是今天说的“剪裁”,区别处在于,这里只是“剪裁浮辞”,而今天则是包括内容上的取舍。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刘勰论述得相当精辟,至今不能认为是陈旧无用的。略述几点如下: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与作家主观感情相互作用的产物。他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是说,“物”是客观存在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所具备的,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于是发而为文辞,形成文学作品,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各种事物时刻都在触动着人们的情感,有谁能无动于衷呢?他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又要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他不满意那种一味描绘山水风光而没有深情远志的作品,他批评“近代以来,文贵形似”,“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的创作倾向。可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刘勰的思想既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又排斥纯客观的自然主义,充分重视了文学要表达思想情感的特质。
他的论述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公式:物(客观现实)——情(作家思想感情)——文(文学作品)。更为可贵地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建安文学悲歌苍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文学作品要做到内容形式的统一,不可偏废。他打比喻说:水有虚柔易动的本性,才能泛起波纹;树木有坚实的树干,才能开出茂盛的花朵,这就好像形式依附内容而存在,受内容决定;虎豹身上要是没有花纹,它的皮子就与狗皮羊皮一样不漂亮、不贵重;犀牛皮质地坚韧,可作战甲,只有涂上红、黑油漆花纹图案,才能漂亮而贵重,这就好像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但刘勰并不把二者等同看待。他认为,文章的美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正如涂脂抹粉只可起一些装饰作用,真正的漂亮还在于眼睛和脸形生得好看。他批评南朝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
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学要不断创新,要“日新其业”,永远老一套,就没有可能超过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变不一定变得好,也可能越变越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如何保证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变?他主张处理好“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看清文坛的发展趋势,来创作动人的作品;同时也要参考古人的优秀作品,来确定写作的法则。他认为,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持久,只有善于继承才不会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鼓励作家要有“趋时(适应时代要求)必果,乘机(抓住时机)无怯”的变革精神,并说:古来作家,一代接一代,“莫不参五(错杂)以相变,因(继承)革(革新)以为功。”这些论述表现了刘勰辩证的发展的文学观念。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刘勰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貌,要求作家加强学习以形成优美的风格。他把作家的个性归结为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分别有庸(平凡)与俊(杰出)、刚与柔、浅与深、雅(正)与郑(邪)的不同。刘勰认为正是作家个性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才形成了文坛上变化万千。
他说:作品中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与作者的才华一致;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与作者的气质一致;作品所写事件及其意义的浅陋或精深,不会与作者的学识相反;作品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与作者的习惯不同。总之,“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又认为,作家个性中的才华和气质是各人的先天禀赋,学识和习惯是后天陶冶学习而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他说:天赋是有的,但开头时的学习方向很重要,这正像凿木染丝,决定于开初要凿个什么样子,染什么颜色,一旦凿成染成,要再改变,可就困难了。他时时提醒作家要重视学习:“积学(积累学识)以储宝,酌理(辨明事理)以富才“,”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写作者无疑是有益的教诲。
《文心雕龙》可供今日继承或借鉴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而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份古老的文学理论遗产,它不是像蜡烛一样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渐趋熄灭,不是像钟声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大而渐趋微弱,而是像奇珍异宝一样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自从九世纪初,《文心雕龙》越出国界传到日本,19世纪传到欧洲,至今国外不仅已有许多译本,专供研究用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及其历史贡献,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注目。据统计,从沈约至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或品评、或采摘、或引证、或考订的历代著名学者,达80多人。章太炎以后,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则难于统计,仅1962年全国报刊登载的研究论文就有四百多篇。当时学术界称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