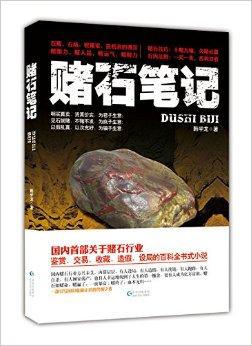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住它。但历史却吊诡地要剥夺他的生命,由此可证,胜利者单方书写的历史纯然是谬论。
回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记忆却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军部的轰炸,三月总参成员的形同陌路,四月达姆斯塔特人烟稠密的战俘营,五月的去留定夺。那是破灭的时代,1946年则在记忆中被抹去了,我无法记住任何逻辑线索断裂、毫无意义的琐碎事件,它们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虚无一物。
我曾做过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时在沙滩上堆房子。没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会被水波冲毁,但人们在童年时眼见此景,心里却带着欢愉。为何我现在悲伤不已?也许悲哀只是来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这无非是一种锱铢必较。考虑到人终将死去,计较于20岁时的劳而无功实为小器的心理作祟。时间会让所有的塔化成沙,绞刑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死是不能被判决的
获知死刑后反而感到安稳,它和任何一种被确定下的安排并无不同,符合我对于确凿的要求。人们从异邦人的法庭上回来,互相恭贺,用这种不乏虚无主义的乐观连结彼此。我们曾在同一面旗帜下生活,现在又为相同的原因而死,这种联系让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单位的。
同生共死诚然只是虚构,然而当自由被几道高墙隔离,它就变成切近身体发肤的幻觉。派普说“我真正的团伙在瓦哈拉”时,整个死牢都沸腾起来。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独在中世纪横行于世,也是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在他们生存着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无论如何,我们甘愿成为“瓦哈拉团伙”的共谋,在那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歌,风华正茂——在东欧平原湿润的泥土下,在奥德河畔粉碎的建筑残骸下,在柏林业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亚绵延的、化为灰烬的美丽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够与之合葬,我颇有些欣欣然。少年时代四月欧石楠新开的时候,我们牵着挚友的手,跨过火堆,举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里走上十几公里,听着内卡河的水声,从书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致的曼海姆。那时我们和帝国都还年轻,而今天则都走到了尽头。青春年少转瞬化为灰烬,而我们的生命永远留在它当中。
我不感到悲戚,毕竟它只是事实。此刻我想的是怎样和“我真正的团伙”排好队,免得叫开瓦哈拉大门时显得像一帮法国兵,或怎样在放风时抢到被太阳光烘热的那块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梦。
因为死是不能被判决的,能判决的仅是死刑,它打扰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弹都没有动摇我们决心——尽管它已经碎灭了。走上绞架前,我是个叫海因茨的金发小子,之后是一具尸体,两者都和他们加于我的罪名无关,无涉军人的荣耀。
1947年1月6日
☆、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耻辱,而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时空不可逆转,人的经历就无可更改。
但是回忆录赋予记忆另一种面貌,有人借它来为自己的事迹涂脂抹粉,有人借以脱罪。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背叛了。人们在这里揭露同僚的罪愆,从而企望自己能被从轻发落。另一些人把德国的秘密泄露给外国。
我指的是那些反人道罪行的证据以外,依照保密条款应当被保护的国家机密。盟军的《纽伦堡法》里有一条被写漏了:如果你作为德国人而叛国,你就不是战争犯。人们因此在祖国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十二年前,希特勒的《纽伦堡法》让这种选择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现在曾经卫戍着德意志的土地与精神的帝国军人也变得和犹太一般无二。这些人是在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时才对祖国背信弃义的,我不想过多的非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国家机密作为嫁妆,倒向盟国的怀抱时,我听到了日耳曼民族瓦解的骨骼碎裂声。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
☆、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让我想起人们用以回忆的东西:发黄的信纸,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监狱广场的另一侧,穿着谈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民观察家报》的年轻记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着走遍世界的风衣走进周末舞场,总有三五个姑娘拥上来。
现在他那么朴素,近乎憔悴。
我惊讶的并非他的憔悴,这是所有困守兰斯贝格的人们的日常。你当然会在最高傲的人那里看见最深的苦难,因为他早已迈过普通的坎坷。我惊讶的是他在这里,一件红马甲昭示他的命运。
卖字为生的人或许真的比卖力为生的人要高贵,即使从未杀过人的纳粹记者也会被“历史”判罚。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窃为之喜,因为只要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判罚的一方,他们就也无偿地不朽了。
这只是一个死囚的狂言。来到兰斯贝格后我时常感到一种死后的轻松,或说从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为帝国情报官的我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见伊利亚斯,却觉得自己会活下去。死牢既然施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用来推翻它的统治。
顺带一提,盟军在两年前的今天进占维也纳,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编者注】
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是前《人民观察家报》第二版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发表反犹言论而获罪,投入兰斯贝格监狱等待死刑。这天加兰与他相遇,几乎交肩而过却让二人心绪难平。他们在柏林相识,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为朋友,各奔东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罗特写于狱中的《兰斯贝格的日落》里,同样留下了名为《加兰,以及人生的断片》的一篇。其更为详尽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隐喻。
他们对死亡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加兰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亚斯用游历世界的方式证言生命的热力。帝国覆灭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长眠的棺材,却让后者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在狱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学意味。
我在后来的调查里得知,加兰在这次相遇后一改常态,开始暗中联系从前被他拒绝的一些人,包括三个月前试图让她写“赎身状”的美国OSS菜鸟办事员。当时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经更名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国的代理——盖伦组织。
此后的事或许都在这条隐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亚斯在1948年获释,不久后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兰走出监狱,旋即参与BND(联邦德国情报局)的组建。带着这些假设,这本笔记里的《纪念720》《相逢》《国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味。
“他不会让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为信仰的一般等价物。”伊利亚斯这样评价加兰,但我想,他或许会为一个新的国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录伊利亚斯写在同一天的日记。我在萃集这本笔记时,已经无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为我年幼时撒欢膝下的人,我妄揣这位亲切的长者会宽恕我的冒昧。
http://。jjwxc/onebook。php?novelid=672072&chapterid=15
☆、纪念720
晚饭后,人们聚在读报栏下盯着到处开天窗的报纸(盟国向在押战犯有选择地提供报刊信息,凡不适合提供的即行剪辑——编者注),报端上日期写着7月20日,我是这样想起三年前的刺杀元首事件的。
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弹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离现场,爆炸时已经走在通往政变的路上。一群预备役军官想颠覆政府,但众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我正在东线外军处,接到调遣令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后我回到安全局,却接到了对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国官员戴着手铐走进自己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我被隔离审查数日,幸而获得信任,进而参与这件事的审理。
那时施陶芬堡已经死去,涉案人员大都押送安全局,余下的正由四处(秘密警察——编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侦探冲进五处(刑事警察——编者注)的大小部门,由于五处长奈比已是叛国嫌犯,这些意法联军迫不及待地鲸吞同僚留下的势力空洞。
那位独目断臂的伯爵则死得大事化小。比起这位现在被奉为大英雄的人,其党羽引发的帝国军政界洗牌更令人焦头烂额。“据传,缪勒(四处长——编者注)也抓到了卡纳里斯的把柄。”我板着脸对我的上司施伦堡汇报。国防军谍报局和我处同样署理国外情报,是一对欢喜冤家,缪勒对军谍局局长下手,难免要顺藤摸瓜,给他的死对头施伦堡下个绊。
施伦堡摇着半杯兑了伏特加的威士忌,若无其事,但烈酒实是他减压的办法。几天后卡纳里斯的案子神鬼不知地移行六处,大量文件在搬迁中仗着盟军的高爆弹付之一炬,我们甚至把军谍局也接管了过来。
“总不能为了捉几只蟑螂,把房子给拆了。”他扑闪着明亮的眼镜耸耸肩。可是在美军压到了西墙(德国西境的军事防御系统——编者注)的节骨眼上搞垮军谍局,我们和刺杀国家元首的施陶芬堡们有什么不同。
他玩味颇深地看着我,“您会知道有什么不同。”随即把我也关了起来。
“眼下几十个将军尚未受审,以你的少校军衔,甚至还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他倚在禁闭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