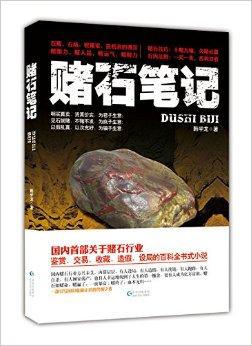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作任何的谈判。”
他把嘴紧紧合上,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眼神也能显得坚决。
我看过太多死亡,有罪或无辜,有的出自我手,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您是否想过,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
“为何?”
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即使两国交战,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
他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
他开始讲课,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如此滔滔不绝。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而身为游击队长,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
“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您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
“那么您的正义呢!用毒气虐杀犹太人,迫害不同政见者,使欧洲陷入战争?!”他猛然站了起来,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
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我沉默地与他对视。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
“请坐吧,”我对他说,“您的腿不适宜站立,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
我的朋友两手交叠在方向盘上,沉默不语。法国抵抗者里昂总部在1944年春被破获,其魁首马克?布洛赫成为殉道者。他写有一部享誉学界的《封建社会》,但有的人无法在书斋和外部世界里同时保持睿智。
“你杀了他。”
是的。当时我想看看这位人文主义者对我这个德匪有多大的仇恨。“如果您出狱后仍然要对德军进行恐怖袭击,不妨先在这里表个态。”我这样说,把配枪交给他,他焦灼的眼睛里涌起震惊和愤怒,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生于法兰西,啜饮于她的文化长河,她的过往铭刻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
他用祷告似的语调说完上述一番话,然后涌起不可遏止的愤怒,向我扣下扳机。
但是,我藏在袖中的另一把枪已经打在他的膝盖上。
我不与他争论历史哲学,他却试图和我比试枪法。于是“危险的敌对者”布洛赫教授被转交回盖世太保审讯,他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死在里昂郊区的荒地上,后颈开枪是德国人的行刑方式。
“现在你想和我说些什么?”我看着眼前衰草起伏的荒地,我的朋友的面容疲惫。布洛赫是他所尊敬的师友,因为相似的主张而成为地下抵抗阵线的伙伴。
但他遏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们都是欧洲人,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此刻我明白的却是布洛赫教授的遗言,切换字句后恰如其分。我生于德意志,他的尊严践行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我对他说,现在我的枪也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开枪或放我走,但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说罢拉开车门向荒地走去。
“和当时一样,你另有一把枪。”身后的人有一口汉诺威的小舌音,我的朋友喊出我的名字,“海因茨加兰!单对单。”我猝然转身,小口径的警用手枪指向我的眉心,而这个狡猾的特工也举枪相向,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
我身携一份秘信赶回柏林,准备谋划阿登反击战,我的朋友不知其内容,但猜准了我们立场相左。他扣下扳机前先示意我拔枪,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
现在三年过去,“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的朋友,我们会有一番怎样的交谈。
1947年12月21日
【编者注】
1944年11月下旬法军攻打阿尔萨斯,马尔罗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参加作战。这支游击队虽然武器装备不全,但作为法军的增援参与了多场战斗。其后驻守斯特拉斯堡,并于次年1月与阿登反击战的德军对峙,最终守城成功。
这段小插曲注定要被诺曼底登陆或攻克柏林一类更具战略意义的历史淹没,但并没有逃出文人的笔墨。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作家、小说家、记者或其他文字工作者,马尔罗更是一位撰写传奇的好手,早年曾以一部真实性堪忧的亚洲革命纪行扬名文坛。后来解放斯特拉斯堡成为法国光复的经典战例,阿尔萨斯—洛林旅名噪一时。
加兰先生的挚友伊萨?罗森斯坦因也参与了马尔罗的战斗。这位前党卫队成员在1941年被发现犹太血统,他们再次在德法边境相遇时已各为其主。“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身为法国游击队员、斯特拉斯堡守军的罗森斯坦因对加兰举枪相向,后者还以同样的决绝。
多年后我把这则日记放在罗森斯坦因面前时,他说,“真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一名剧作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谈论这件事时加兰先生已经去世,罗森斯坦因则在法国监狱里,但看上去一派优容。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收紧下颌以使自己不那么像在吹牛。“他可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补充道,“御用文人不也是文人的一种嘛?”
那天他把雪铁龙开到阿尔萨斯一处无名荒地上,试图说服加兰与之合作。“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而我也没有制服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打算,”罗森斯坦因望着前方略高的地方,人们在陷入回忆时是很难撒谎的,“所以我踩下油门,准备把车开到十米外的河里去,反正我们都不太会游泳,如果老天站在我这边,兴许结局会令我满意。”
“不,这跟大义凛然丝毫不沾边,我只是信任老天会眷顾我,”他摆摆手,“可是那小子差点把我手腕都拧脱臼了。结果我们只是在车里打了一架。”
“但愿您这位文人没有被揍得很惨。”我同情地看着他。
他顿了顿,旋即笑了起来,“实际上是你爹被搞得很窘。噢不,我不能对我的教子说这些,我改变主意了。”
不得不重申我没有什么教父,虽然这会遭来“一个男孩怎么也那么看重名分”一类的调侃。我那一星半点的贫嘴大概都是跟这位大叔练的,现在我好奇他到底对我老爹耍了什么滑头。
“你知道,即使打架也有一些禁忌部位,”他停顿了一下,看见我皱眉后更加好整以暇,“所以我就——噢,当然不会违背骑士精神,事实上我正要发扬骑士精神,像浪漫小说里那样。”
我真的后悔自己的好奇心了,为什么我的父辈从来没给我树立一点正面的榜样。
据称老爹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好友一记头槌。所以当他逃出雪铁龙时,两个人都眼冒金星。他们各自拔出枪,“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上帝知道他们都在瞄准哪里。
一切细节都是信仰的绞刑师,还是来讲述更为宏大的历史吧。他们骑士般的友谊并未因此破裂,但两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血河。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爆发,德军重新攻打该地。阿尔萨斯—洛林旅奉命死守斯特拉斯堡,这支传奇般的游击队抵挡住了德国人的背水一战,最终让战争惨淡收场。
这是史实还是史诗?二者正如这对挚友对他们相遇的说法那样各执一端。在本文作者看来,阿尔萨斯的解放仅仅是德军的战略性撤退的结果,而阿登反击战是由于燃油等后勤补给的沉疴而崩殂。似乎只要给坦克灌满汽油,德军就能再次越过斯特拉斯堡,直抵巴黎。
☆、新年
死囚们筹办在监狱里的第三个新年,圣歌在火鸡肉的香气里飘来,不同的教派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我拿着一只未发酵的面包,看着桌子对面与我一样年轻的笑脸,大口咬下去。
景象和在警卫旗时一般无二,只是这里有一道高墙阻隔了外界,但那时我们也没想过兵营外的世界。1938年的圣诞礼物用普通军袜包裹着的酒芯糖,缩微的巧克力酒瓶就像玩具。塞普老爹反对年轻人吸烟喝酒,这癖好后来沿袭到党卫军青年师的配给上。
那时人们成长得更快。战争末期我们还不满三十,已经在比我们年幼的人身上唏嘘自己的过往。我们这些一零年后出生的人有幸遵循自己的意愿,走上如今的道路。1933年纳粹上台时我十八岁,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生于二十年代的人自幼便在纳粹笼罩下,尚未懂得人生的正道,就被狂热宣言驱使到战场上。这些仅比我们年幼十年的后辈自来被灌输一整套纳粹理念,我们便身负指引他们避开毁灭的责任。
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少年的死亡,很多人死在战场上,现在由于不堪忍受刑讯,十八岁的孩子死在监狱里:几位党卫军士兵的□破损,几个人用裤子挂在窗上结束生命。活着的人无法为之鸣枪敬礼。
残存的人布置起圣诞晚会的会堂。没有圣诞树,但是有圣餐,取代帝国时的烛火和煞白的百合,假装成一个简朴农家的新年礼。我们喝咖啡代替酒类,统一的囚服使我们像一家人。我看着故友重逢:身份改换,面容渐老,笑容是苦中作乐,但经年的友谊是真实的。就像在瓦哈拉,只是这里的英灵不享有永恒的殊荣罢了。
自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即使在监狱里,生活的片刻温暖也让人沉醉。于是我扭头看向窗外的高墙和铁丝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实。
新年快乐。
1948年1月1日
☆、死亡
死前的记忆总是特别清晰,往事根据它们在我骨骼里的深浅而先后来到,回忆所用的时长也以此为据。这就是记忆的力量。人为了实现价值而生,而记忆就在人所经历的各向同性的物理时空之中,把某些经历赋予更高的价值。
死刑因此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人道。假设安排后事是每个人生命里最后的愿望,那么在监狱里等待可以预期的死亡,就拥有了思考在余生中做些什么的权利。
遗憾的是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美国人令人失望。两年前我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我仍然这里,看着太阳从高墙的一头爬起,又落到墙的另一头。
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被剪除了重要新闻的报纸外不被允许接受外界信息,除了无关痛痒的书籍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时间变成纯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