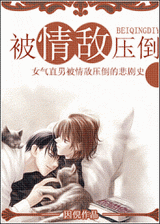情敌情友-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同伙,那又如何?”雷怒透着不耐烦。
“听他说完,雷怒。”又是罗景辉打的圆场。
胡来学理了理思路,试图让思维的火花点燃语言的香烟,他哑着嗓子,分析道:“阿青是个赌徒,他有不少赌债缠身的赌友。我猜,不,肯定他的同伙就是那些人。我知道那个地下赌场在什么地方,那里的赌徒大多是常客,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找出阿青的同伙……就是跟阿青常玩一起比较亲近的那些人,其中欠着赌债无力偿还的,这些天都没出现在赌场的人。”
他顿了一顿,凝视着雷怒,继续道:“无论如何,绑架需要有安全隐蔽的地方来藏匿人质,我清楚阿青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囚禁小余的地方!”
雷怒的眼睛一亮,但马上又暗淡下去,他沉吟道:“倒不是不可行,只是时间耗费太多,恐怕……”
“报警吗?”谢天诚建议道。
“警察介入的话,地下赌场会配合吗?没有闻风而逃就不错了吧。”
对于雷怒的顾虑,罗景辉踌躇不定,他瞥一眼谢天诚,他问胡来学:“你说说看,那个地下赌场在什么地方?”
胡来学报出地址后,罗景辉听后,右手食指抵住了下颏,沉吟不语。
雷怒几乎跳起:“景辉!”
罗景辉没有应答,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谢天诚。
谢天诚扯出笑容,略略举了举手,表示投降:“好啦,好啦,我又不是警察,也不是正义超人,你不用顾忌我。”
虽是在这等急迫的环境下,众人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罗景辉则掏出了手机开始拨电话。
二十分钟后,对方传回了消息,符合条件的人少得出奇,只有三个。而胡来学一下就报出其中两个人是近期与廖青火热到连他也听闻其名。
“下一步则报警吧,去搜索这两个人的消息,找地方。”罗景辉道。
时机也是掐得极好,刚刚报完警,雷怒的手机便即响起,从他接听电话瞬间一沉的脸色,任谁都能猜中来电者。
余下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雷怒,胡来学拼命按捺着上前抢过手机的冲动,他真的想对着廖青用肺叶爆裂的音量吼上几句。
雷怒合上手机,脸色阴沉地像地狱归来。手机上提示接收到短信的脆响抢在了人声之前,雷怒看向手机,有几秒的时间僵立不动,继而攥紧了手机。
“那混蛋!”
胡来学勉强咽下口唾沫,小心翼翼地问道:“他……他要很多钱吗?”
“不是钱的问题!他……”雷怒暴喝,但仿佛被哽住了一般咬住牙,深深吸了口气,恢复了冷静,“说这些没用。景辉,他们要三百万,下午两点到海岛乐园,具体地点到时再通知。”
众人皆不由自主地抬腕看表,一点十五分。
时间已是无多,雷怒涩然笑道:“三百万就能这么折腾,他们实在也太客气了。”
胡来学抿抿唇,他竟然可以明白,不贪心不过是因为廖青认为现金过多累赘不小。
为什么连这种事他也可以跟那个人心有灵犀呢?
************************************************
她深信廖青的举动绝不是出于什么同情或义愤,她再傻也能看懂那人眼神中闪烁的戏谑。
五脏六腑都在燃烧,她确定她的脸庞上一定激荡着火花,为保留最后自尊的防线,必须挤出一丝笑容。
如今私密空间只剩下她独自来回,困兽的焦躁与攻击性牢牢地控制着她,她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电脑的屏幕亮地刺眼——不,是她的神经线和眼睛变得敏感脆弱罢了。
她的手指优美地在键盘上舞动,输入一行一行悲愤交加的文字,践踏了她自尊的人非但安然无恙,还逍遥自在!
必须找个地方来发泄她的怒火,理智燃烧殆尽,化作了烟灰。
帖子的题目并不是那么耸人听闻,至少她是认为她道出了实情与真相。
这故事委实令人作呕,她瞟见照片上两个相拥的男人就反胃不已,妒火中烧。
她文思如泉涌,将前夫无能,前男友导致她离婚的故事发挥地淋漓尽致。
第五十七章、
警方的计划,是让雷怒依约而行,交赎金。据说绑架案中,绑匪取赎金的时候便会步入天罗地网,插翅难飞。
胡来学提出的可以从拘禁人质地点着手的建议被无视,警方认为这样间接而繁琐,耗时不菲。
尽管心存疑虑,雷怒还是同意了警方的意见。幸好罗景辉也在,不消十分钟,现金便筹备妥当,按照对方的指示,装入一个标着某某旅行社的红色旅行袋中。
当雷怒按时来到海岛乐园,眼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景让他心中升腾起不详,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天正是乐园的新年游园会,恰好在欢乐大**。
仿佛是全城的孩子都集中在了这里。
雷怒听从手机里的吩咐,将旅行袋放在一个公共电话亭内,离开时心情跟脚步一样沉重。
压城乌云状的感觉挥之不去。
对方显然是看多了警匪片的,每次来电只言片语,根本无法追踪信号。
重新聚首,都失了谈话的兴致,惴惴不安地等待消息。
一个小时之后,传来的却是噩耗。
警方的歉意此时苍白无力到了极点,可当事人却连愤怒的情绪都被冻结。
失手的理由实在简单,绑匪找了个十来岁的毫不起眼的男孩去取旅行袋,男孩得手之后一头扎进了欢乐的人群,消失的速度足可媲美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彩带。警察们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找不到男孩的踪影,而那袋子跟袋子里的钱,也从游乐场蒸发。
雷怒深吸口气,压制住中烧的怒火,瞟向旁边脸色惨败的胡来学,笑道:“还好,我们准备的全部是真钞。”
胡来学只觉出生至今从未有这么冷过,胸口疼痛蔓延到了四肢百骸,他想要吐。
看向雷怒,他恍恍惚惚地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让我想想……”
****************
余多也痛,有生以来,首次在肉体上感受到连呼吸都几欲不能的锐痛。
意识渐渐远去,眼前的所有都蒙上了一层模糊的血雾,血雾愈发浓厚,他清楚,自己很快又要昏迷过去了。
也许会这样死去吧。
有关系吗?也没关系的。
至少知道幸幸已经平安无事了,所以即便谁也不作告别,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轻轻飘飘地离去,也该是被允许的。
睡吧,心底有个声音说,睡着了就不会痛了。
可是还是有人会悲伤吧。
意识的深处,微弱的抵抗在坚持着:你并不是无牵无挂了,轻而易举地离开,你甘心吗?
有人需要你……
可是质疑与反驳的声音却更加响亮——真的吗?这般愚蠢、无用的我……
四十分钟前,当余多发现,看守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并且那人不时用下流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他时,他决意冒险。
强忍着羞耻,余多试图引诱那人,他恳求说,他愿意让那人享受到快乐,只要能够得知孩子的现状。
那人踌躇时,余多扭动着身体蜷靠过去,由于被反绑了双手,他只能用力抬头,张嘴用舌头与牙齿摸索那人的皮带。
余多的主动挑起了那人的□,他思忖着,这般柔弱的青年,该不会有什么威胁,便放胆地让余多紧贴自己。
为了更加方便享受,那人在快感的冲动中解开了余多双手的束缚,当他紧紧地拽住余多的头发,在余多讨好的呻吟,巧妙的哀求中,喃喃道出孩子早已被释放的事情。
余多颤声确认,那人倍感不耐地将余多翻过身来,想要抬起他的双腿。
电光火石之间,余多用尽全力地朝那人的胸膛踢去,那人惨叫着倒地,余多跳起身来,直扑门口——
手抓住了门把,奋力一拉,却发现门已从外面上锁,他本能地回头,试图搜索到钥匙。
刹那间,于怪叫声中,一股力量猛然击中了他,他撞向门板,滚倒在地。
眩晕中摇晃着起来,余多一扑而上压住那人,攥紧拳头狠狠地砸向对方的眼睛。
负痛的头颅弹起,如石头般顶向余多的鼻梁。
余多侧身躲过,却也失去了平衡,那人趁机将余多掀翻在地,骑压上去,余多伸手抵挡,然而一阵剧痛却让他顿时失神。
好一会儿,才朦胧地看清,那人的右手高举着一把匕首,刀身已全赤,尖峰处连续不短地滴落着红色的液体。
加害者的恐慌犹胜于受害者,若非疼痛让余多的肌肉麻痹得不受控制,他一定忍不住要为那人的滑稽表情而大笑起来。
那人如丢烫手山芋一般甩掉匕首,慌慌张张地掏出钥匙,夺路而逃。
却不忘重新关门锁上。
余多渐渐模糊的意识里,苦笑连连。
他并不晓得自己受伤有多重,唯疼痛让他周身无力,举手艰难。
而在另一方面,他不由深深地懊悔自己的莽撞与失措,若他真就这么离去,必是周身血污,甚至残留着与他人交好之后的证据。
这么不堪入目的自己,无可避免地要被那个人看到。
他会怎么想?
余多笑自己无聊,但这种锐痛甚至超过了肉体的痛楚,一寸一寸凌迟着心脏。
上天终于仁慈地将昏迷赐给了他。
***********************************
当周芸得知,她与廖青的交往所引发的一串恶果之后,她如遭雷击,无法动弹了好一阵。
她点下的星星之火,在网络上燎原地一发不可收拾。
最初,周芸看到首个声援她的回帖,痛斥男人的变态与不义时,她感受到了正义的快慰。
然而失控的局面却让她瞠目结舌,就连她以发帖人之名希望平息事态,也难力挽狂澜。
有人号召了“人肉搜索”,好事者希望负心人能够淹死在义愤填膺的唾沫星子里。
周芸稀里糊涂地意识到大事有些不妙。
她的初衷很简单,不过泄愤而已,谁会料到如此一呼百应,她的确也暗地里希冀有不知名的义愤者出面揪出那两个男人,狠狠地伤害他们一把。
但是,她完全不希望自己也被拉到光天化日之下被指指点点,况,如今事情峰回路转,廖青外逃,幸幸也曾遭到绑架,这一切的肇因,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她……
思前想后,周芸决定,无论如何,硬着头皮也要找雷怒,凭她一己之力,根本没有能耐去解决此事。
雷怒最初拒绝见她,这也是周芸意料之中,她忍泪恳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无法分心照顾幸幸,就交给我好不好?孩子跟我,总比外人好吧……”
电话的那头,沉默中渗出一股软化,周芸趁胜追击:“雷怒,你和余多的事我知道了。我不会怎样,更不会带走孩子,你让我帮帮忙,好么……”
他打断了她的话:“中心医院旁边有个咖啡馆,半个小时后在那里见吧。”
“好。”周芸忙不迭地答应,她迟疑着要问多一句——
然而听筒里却只剩下忙音。
第五十八章、
胡来学默默地看著病床左面的滴注袋与静脉注射泵,管子蜿蜒曲折,伸至床上那人的胳膊。
他不太敢凝神去看那张惨白的脸,眉宇之间蹙出点点痛楚,每丝每毫,都在悄悄碾磨他的心脏。
为什麽会这样?
自问千万次,没有答案。
胡来学把脸埋入手掌中,不幸中的万幸,尽管曾经危在旦夕,甚至连医生都要以为余多没救了,生命却固执地顽强著。
一叶肺衰弱了,上过人工呼吸器,他终於在昏迷了六天之後苏醒──让胡来学泪流满面的奇迹。
原是打算在余多脱险之後便销声匿迹,然而他却发现他怎麽也迈不开离去的脚步。
似乎还欠著余多什麽,且从今往後,何去何从?
几日来寸步不离余多的雷怒今天找上了他,请求他帮忙照看一阵。
胡来学二话不说地答应,抬眼看雷怒时泪光闪烁。
雷怒苦笑,轻叹:“不管怎麽说,他把你当朋友。”
有此一句,足让胡来学死心塌地,哪怕守候余多到天荒地老。
床上的余多什麽时候睁开的眼睛,胡来学毫无所知。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余多的下颌,清洁光溜的程度显示出看护的细心周到。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人?胡来学想著,视线上移,骤然间与余多若有所思的视线撞个正著。
“嗨。”他有些慌乱,勉强挤出笑容的同时语无伦次信口开河,“你……还好吗?痛不痛?那个,你看,事情跟电影里真的有很大区别,如果是电影,警察一定会在钞票里放什麽微型电子追踪器的,这样即使歹徒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一网打尽……你说是不是……”
胡来学说不下去了,余多看他的眼神里,关怀与悲凉的重量让人难以承受。
“我听说,是你找到我的。”
不知道该怎麽回应,胡来学只能低头不语。
你差点就死了啊,只要晚上那麽一点。
在警察实施下一个计划之前,胡来学领著众人找了几处地方,最终还是找到了关押余多的房子,然而当他们赶到时,已经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余多了。
没有告诉任何人,其实在那之後,胡来学接到了廖青打来的电话,他说了再见,说了余多的下落──只是,为时已晚。
余多伸出手,却在中途无力地落下。
“阿学,”他显得疲惫不堪,“我知道不该在你面前说,可是我……我恨他。”
胡来学闻言霍然抬头,凝视著余多。
“他用一种我无法原谅的方式伤害了我。”余多说,身体的疼痛让他皱起了眉,声音也失去了平衡,“我死里逃生了,可却不觉得侥幸。”
“小余……”胡来学声音发颤,他战栗著,撑在病床的床头,呻吟地低呼,“天啊!”
“我……我不敢跟他说这些。”余多的目中泛起了泪。
话语中的“他”无需挑明,两人都清楚地很。
胡来学轻轻地抚摩上余多的手臂,力道不大,与言语搭配在一起重似千钧:“你可以跟我说,没关系的。”
余多闭起眼睛,他似乎成功地克制住了泪水,嗓音仍是沙哑:


![情敌变夫夫[全息]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41/417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