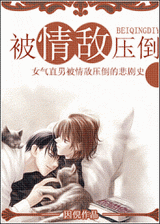�������-��2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t���Ц������������ŭ����˼���Dz�����ָ؟��ֻ�Ǹ��V�����Ⱦ��c���n�����o�a��
������ĬĬ�ذ�������ŭ����߅���鲻��Ҫ�Z�ԵĽ������Ŀڰl�C��
������ŭ�˕r�����������ֱ���Ц�������㲻�Ó��ģ��ұ��C�ǂ���������Ǐ���Ƭ����ʲô������¡���
��������ʲô�������Ҋ�R�^������ֶΣ�������¡�
�������ܺ��Ρ��@����һ�c��̎������С����ҿ϶��������ҡ���߀�������ҵĵף�������ô�p���Єӵġ��������Ǵ����������ײʯ�^���u��������ŭ��������p�ɵ�գ�٩���������ľo����
�������գ��գ�۾�����߀��̫�܉����T��ŭ��ЦԒ��
�����@��ŭЦ���������G�_������ס��࣬�����������ȥ��
�������ؑ����@���ǣ��X���Ѕs�����������c��ŭ�g�IJ�࣬�ƺ����ǿ���һ�����͵ġ�
�������㲻���ġ�����ŭ��Թ�ˡ�
��������ֻ�����룬�����������ŭ��Ę��Ц��������ʲô�r���������һ�ӳ����أ���
���������죿���J�����ѽ�������ˡ���
����ֱ����ŭ�ĵڶ��������£������������䌍�Ǵ����R�ε���˼�����ɵ�Ц�R��һ����ȥ��ģ���
��������������������������������������
���������һ��ϣ������W�x�_���ࡣ
�������r����WҲ���@ô����ġ�
����Ȼ���������㿂�������㣬�����f����Щ�����ƺ���������ע���ġ�
����������h����Լ���Ϥ�o�ȵĹ�Ԣ���g������ľ�Ȼ�ǘO�ޭh��
�������ƺ�����һ��������Փ�ĕ����ᵽ����������w�Ķ��x��������˂��Ƀ�����������y�c��罻���ķ�飧ϵ�y�ɣ����Ǖ����e������߀ӛ�á�
����ij�����ܼ�ͥ�����ċDŮ����Ҳ�x���_�ǂ�ʹ��ļ�ͥ�������������L���@���ǂ����͵ĘO�ޭh��
��������������ԇ�D�����@�ӵļ�ͥ�r�����ܱ����ċDŮ߀�����Լ����ɷ��q�o��
��������W����ʲô�ܱ����ֺ��ċDŮ�����@�r�����X���Լ������������ͬ�ӵĘO�ޭh�У��x�_�ěQ��һ���������@����飧ϵ�y�ķ������D�r�͟�����ɢ�ˡ�
�������c���࣬�����@��ϵ�y���X݆�뉺�����l���B�ˡ�
������ʲô�����@�����ӣ�����W�治���ס�
���������˵������У������l�F�˱˴ˣ�ҕ������Ψһ���䌚���������������������lչ��������������֮�ϵ����w�Pϵ����Ҳ���^�������_���˴ː����һ�N��ʽ��
�����ԣ������ǎ����������ԣ����푪ԓ�nj��������˸��o�ܵ�ϵ��һ��ģ�Ȼ��������ʲô�oՓ����߀�����࣬�ƺ����o�����еõ��κο옷��
��������ֹһ�ε������ˣ���߀������������ԇ�^��������������ıƽ��r������ϣ�����c����ܻ�����
�����������������
��������W�@�˿ښ⣬Ҳ�S����̫��������Ĉ������c�Լ��ġ���
�����@�r���T�_�ˣ�����Wֹͣ�˺�˼�y�룬�������������Đ�ŭ�c��������е�����ԓ���ģ����࣬���@���쵰����
��������ʮ�¡�
�������죬ֻ���^���졣
�������������Ԟ鳣���Ƶġ�
�������ಣ����ۣ����_�ⲻ�������ز�̤������W�ĸ�����
�������ĉ��ȸ�����W���ס����������Ȼ�������nj����@�ӎ��������Ե��e�ӣ�Ҳ�����������W�������⡣
���������ƺ��ܿ����������_���S����ǣ�Ц������������̲�סҲ����Pϵ������ �f�����Ϊ����ڼ��еĹ������S�ر���ġ������������į�ɣ����f�أ���
��������W������һ�ۣ�����ش�
������ֵ��ǣ�����˼�D���������ط�ȥ�r��ԭ�������Q�̵����ⷴ���p����Щ��
�������^����߀�Ƕ����m�ɶ�ֹ�������ٞ��y����W�����_�����������W�Єӵ��K�ӣ�����һ�l��·��
��������W���ɴ��⣬�w���M������
������Q��������������Ҋ�������ڽo�����������p�Ͽ�����
����Ҋ����W������������ҫ�Ƅ����Ƶ؛_���Pһ�P����Ę����¶���������ɫ��
��������W��֮һ�ϣ�Ĭ�������������������߅���������Q�꿇�������L�L�@�˿ښ⣺���㵽���Ǵ�����ʲô����
��������ǰ����������Ԣ�Һ���W��
��������W̹�ʵظ��V���࣬���ѽ��ѹ����o�ˣ��@Щ�춼�ڷ�ʡ������֮�g���Pϵ������˼��Ϥ�����Q�����r�x�_һ��ӣ�ȥ��������һ�ˡ��r�g������Щ�L������Ђ�һ����d��
�����������Ԓ�f���p�ɣ��·������^ͻȻ�g��Ѫ�������݂��L����ɽ��ˮ��
����������W���f���@�������������ĘO���ˡ�
�����c����һ���ɔ࣬�쵶�y��Ě��Ǐā����������ܓ��С���ֻ��ϣ������һ�Εr�g�������܉���_���܉����o���úõ�ȥ˼��һ��δ����
��������������ʼ�K�Ǵ��ڵģ����dž
����������W����ϵ����ǣ�����ķ����O�˵ļ��ҡ�
����Ԓ���x�e�r������ٿȻĘɫ��׃�������W�q���F���O���ľG�⣬��һ��קס����W���½ݺݵ�����������ʲô��˼������˦����ô����
���������@ôһ�ƣ�����W���ڽY�࣬һ�r�����ܲ�����
���������B֧�ᶼ�����������o�����@���������ࡣ
���������R�������^������Ц�˔����G�_����W����Ȼ������ץ��ˮ����������������ƴ��һ���������Ǹ��X�����κ���ʹ����������rѪ����ӿ�����䵽���^�������Ԓ����������W�����ƽ���
��������W��ȫ���@�������������ɵ�ˣ��������ؿ���������ˮ��������ץ�Ԓ����һ��һ��Ѫ�۵����೯���ƽ���
����Ȼ����جج֮�У�һ�ж��������挍�ġ�
�����������x�_��Ԣ�ĕr�����Գ�Ҫ��������K��ס����W���p�֣������̶��ڴ��ϣ��oՓ����W��ô����l�IJ����x�_���o�����¡�
��������Ҳ�����̫��ďUԒ����ֻ������W�f�����㲻 �ҵģ��Ҿ�ȥ������
��������W���@�ӵľ������ǟo���κΣ����o�ˣ����Ǹ��õس�ȫ������ķǷ��O��������Ǜ�����˕��l�F��ͻȻʧۙ�ˡ�
���������f�^�Ҳ������ˣ����B�@�c���ζ����Ͻo�҆������WҊ�����ƺ��o���ٌ���������������Ц����
��������Ū���˿����������N�Ϻ���W��Ę�a�����Ƶı�������W���ɵ�飧�����۾���
�������� �����������Z�ƵĆ����������W�����W���ǂ������С���ǽo�����ʲô�Իꜫ�����Ȼ����Ҫ�x�_���ˣ����V�ң����o����ʲô��̎����
����������С�������W�Ļش�ɴ����䡣
���������p�@���u�^�����Ǿ��V�����ʲô���@�����㣬�x�_�ң���
�������қ���С���
��������W�f���@Ԓ�r�����X�����ﶼ�ܷ���������
������������Ԓ��
����Ȼ����������Ȼ�Dz��ŵģ�����Ц�����ĺ���W��Ę������������͟��������_�����ҵġ����V�ҡ��㡭���ǐ������ˣ���
��������W��������һֱ��Ĭ������ŗ���������������֓������������ţ��˕r ���@Ԓ�����Ȼһ�@��̧�^ֱҕ�����࣬�������Զ��������ˣ����࣬�Ҳ����ٮ���ċ����ˡ���
����ͻ������Ĵ�����һ㶣���ͣ���������l��һ��_�ĵĴ�Ц��Ц���Ϛⲻ����r����������W���_�ڵ��������W���㌍��̫����Ц�ˣ���
����Ц�����ۜI���۾����W�^һ�zꎻޣ��@������б�����W����������Ϣ�o�⣬���X����Ŀ�����һ�N���衣
������Ҋ������Ц�ÝL���ڴ�������W��Ȼ���������~���T߅��
���������ք��������T�ѣ������Ц���̟�����ɢ��ȡ����֮���DZ���عǵ���ã��������W���Ҹ����f�^��Ҫ���x�_��Ԓ�����ӣ��@�����㲻����ô����
��������W�s���֣�����߅���Ŀ�Ц������֪��֪��ʲô���������ǣ���
������������������ң����㣬��Ҳ�ǽ^���������֡����W���������ģ��㲻�����ҵ���ȥـ���δ��������������
���������Ц�����r�g����ط·�ͯ��
��������W�ش�߅������ҕ�����࣬�n���ѷe�ɵĺ��ƌӌӉ��ϸ���ijlj������u�˓u�^��ԇ�D���Ó��һ�c��w�������࣬�㵽��߀Ҫ�ҵ�ʲô�����܉��������ȡ��������@���¡����찡���Ҿ����Z߶�˶��ٴν���ú���һ�ݹ������@�����˵Ľ�ɫô����߀������㋌������
������Ŭ���Լ����Z�ⲻ������ɽ���o�Ա��l��
����Ȼ��ƽ�o����еõ��ؑ���
�������౾��ЪϢ��Цƽ����푣���ʹЦ�����p��߀�䏈�ش������壬���岻��Ű����������푡�
��������W��������˿ښ⣬���ѽ��o��룧�����ס�^��������������࣬��������ࡣ
����������һ���A �Ķ����cһ���˽���c����Ҳ�S�����ܽo���㌍�H�Ď������s��������һ�����c��ů���@�������϶�����
�����������������ˣ����Ǟ�ʲô�������s������ʹ��ĸ�Դ�أ�
���������������e�ˣ����������l�e�ˣ�
���������������������ˣ���ʲô��Ȼ�����Ϻúõء���ƽ��͵� ���fһ�fԒ�أ�
�����@�ӵĐ���֮�У��������˴˵��˽⾹Ȼ�������O�Կ���ı�����
�����q�牋��تz��ʹ�࣬����W߀�ǟo���κΡ�
�������࿂�㾏�^�Ł���ץס����W����������һ�������˷��L���˴��ϡ�
�������촽���N����Ķ��䣬����W�����������M�������Đۓᣬ �����Ԏ�������գ�Ц����ι�����f��ĸ���g�Dz���Ҳ�����@�N�£���
��������W�����컨�壬ϣ�����܉�oҕ���еĴ�
��������֮�������sֻ�����@�����ϣ��œ��А����c����ô��
����������ĺ������^����У���
���� �������@ô��������WͶ�ԅ�����Ŀ�⡣
����������֪������ǰȥ����ŭҪ�������飬Ҳ��֪�����ڴ˕r�˿̣��������е�ŭ������w�أ����Դ��˵����⣬�����@�����飬��������������Ҳ������ʯ��١�
�����F�ڣ�����W�����wֻ��Ռ��ط���������������������������ϣ�Ĭ�����ѷ�ͬһ�㡣
�������w���p��һ�𣬸��顢��������������܉�E�����P���e�����o�ķ��_��
������ϲ�DZ�������W��������ڏصؿv��ǰһ˲�����뵽���ǣ�����
����51~52
����51��
�������ż��ˣ��ðְ���ŭÿ���糿����Ů������ȻҲ�������ڡ�
�������Ը���µ����Ҫ����࣬��������ܳ��������������dzϻ̳Ͽֵؾܾ��ˡ�
�������˵����ϲ��������������һ�����������������Ľ�ͨ����ôҲ�������Ŀ����٣�������ŭ��˽��������ζ���������λ��������Ƶ��ǹ����Ȳ��ϵġ�
���������˾���ϸ�����࣬��ŭ֪����Ȱ��ȥҲû�н����ֻ�����ա�
��������֮�ң��Լ�һֻ�������һ���չ˺��ӵİ��̵����������������졣
�����糿�����ǹδ��������ʱ�䣬���������빷��ͬ���š�
������ŭ���������С����ʿ������Ѽ��ܲ������������Ǹ��Ȱ����ܵ����ˣ�ֻ�Ƕ��κ��¾������Ķ������᱾�ܵؾ��ľ���
�������������ǹ���
����������ŭ�����ֱ�Թ���İ����õú�Ц���
�������ӳ���̽��ͷȥ��������ŭ��Ѽ����ܵ���Ӱ������һ�����������������ӿ������
��������û�ж���ŭ˵�������ж�ôϲ���������Ϸ�ܲ�����ŭ�����������������͵���ŭ��
�������������ŵ���ŭ��
������ʿ����С������С��ס��������ͬ�Ĺ���ϵͳվ�㡣
���������һ�����������˳�����ʱ�������Ѿ��������ǹ⣬�������ʱ�ij˿ͽϴ�ǰ���Լ����ˡ�
����������˰�������Ȼ̾�˿�������һ�귢���������治�٣����ȿֺ���ˮ��ÿ�¶������������Ū��Ϊ�֡�
��������������ѧ�����ɴӿ��´����ͳ��ֻ�������������ѧ�ĺ��룬������ȥ��
���������������䣬�ǻ�е����ʾ�Է��ѹػ����������㹻������
�����⼸�������Դ���ŭ��������Ƭ����֮�����ͼ�ֲ�и�ز������ѧ�ĵ绰��ȴʼ���ǹػ���
������ŭ���ܲ�û�н�����������У�����Ҳ�����࣬ϣ������Ҫ�������ѧ���˽�����
������ȻҲ���е����ġ�
������ŭ˵������������Ǹ����Ѻ����ģ�������ȴ˽�����ij���������Ƭ���Ǹ������������ʲô���������˲�ֵ�����Ρ���
������ಢû�������ѧ���ͣ���ֻ���Լ��ĵ״���һ�����š�
�����������ţ���һ������ѧð��ǰ�����ȴ������������ôһ�֡�
����������ˣ�����ѧ���Ļ�֮������ݼ�֮��տ���ж�֮���ܣ�ίʵ���˺��¡�
�����������Ϊ��²Ⲣ����ʵ��
�����͵����Ǹ��ɾ�ҩ���ֹ������߰ɣ�����Ϊ������Ŀ���������β�������Ҳ������������ŭ��ӵ��һĻ��
����������ʵ�����྿����Σ���������ֻҪ����ѧ�ڷ��ϣ��������ŵ��ס�
��������ѧ��ʵ��̫�����ˡ�
����Ȼ�������֣�����ѧʧ���ˡ������Ҳ����ˣ����統�����ܿ���·��˼�������
����ǧ���˿ڵĴ���У�ãã�˺�����ͷ��Ӭһ���Ҹ��ˣ�̸�����ף�
������������У�Ψ����һ˿����Ӱ��
���������Щ�㷲�������������ǵ��ĺ���ѧ�İ�ȫ��
�������ų���Ĵ��⣬Ҳ�����ಢ�����˺�����ѧ��
��������ٴη����Լ�������Ϊ����
����Ŀ������������Ұ�����˦��˦ͷ����ʱ�����˵�˼������һ�ߡ�
������������Ҫ����������Ҳ����ǰ���ѵ��ⷬ��ƽ����
������Ȼû�и��ѵķ��������ٲ�Ҫ������Ϊ����˼�������Ը���
������ʼһ��Ĺ���֮ǰ��������������������Լ���Ҫʧ����
�������챾���Ǹ�ƽ�͵����ӣ�����������˼���µĹ�����ͼ��ͻȻ�ӵ��չ����ҵı�ķ�������������ĵ绰��
������ķ�����ɢ�ظ�����࣬���Ҳ����ˡ�
������ྪ��һ���亹����ͷ�Է��£����ò�ƴ������Լ�ǧ���


![��б���[ȫϢ]����](http://www.8btxt.com/cover/41/417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