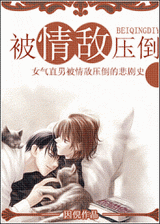头号情敌-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赫连小声道:“我懂。你快回来。明天圣诞,我不管你跟哪个病人,廖启望也好,别人也好,我们必须启程回去,明不明白?”
我胡乱答应。又呆呆坐在客厅,怀里搂着那个丑到灵魂的卡通抱枕。蔡仲勋突然要求增多,我默不作声一一执行,但不跟他讲半句。
廖启望在清晨时分出现。身上全是冰凌,大衣撕破好几处,浑身上下挟裹着冰冷的寒气,比昨天还要狼狈。我从沙发上爬起来,睡得懵懵懂懂:“你回来啦?”
我揉着眼,穿着毛拖鞋跟在他身后,“冷不冷?饿不饿?要不要吃饭?”
他脱下外套,忽然站住,低下头仔细看我,轻轻将我拥在怀里。
☆、第十七章
我是真正清醒了。
我感到他的毛衫都已冷透:“没事的没事的。他很好。”
他呼吸沉重,手臂上强悍肌肉绷紧。张嘴欲说些什么。
我双手轻轻放在他手臂以示安抚。
电话响,我们同时各自退开一步。
是赫连,声音懒洋洋:“哎——呀。你电话响好长时间。我摁断,它反而响得更执着。”
我心里蓦地一动,手忙脚乱穿衣服,边跟廖启望汇报工作:“他很好,睡的很香。我熬了稀饭在锅里。你喝一点暖和一下。我现在有事马上回酒店。”
我越过他身侧,手握门钮没有回头:“再见。”
门外大雪仍在继续,冷风灌得我睁不开眼。小区门口堆了两个大雪人,圆滚滚身躯插两把大扫帚,憨态可掬。
我顶风踉跄前行。
街旁两侧鳞次栉比,商店未开门,然而七彩霓虹灯与松树已经装扮妥当,大大小小的红色圣诞老人与白雪相映成趣。
我打蔡邵雍电话,没有人接。
我只好一直打一直打。又一次次响到那个机械的女声提醒:“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我心中焦急,快跑起来。
路上摔了几个大跟头,头顶一层白雪,转过路灯街角,酒店门前行人寂寥,有一辆黑色车停在门口。
身形高大的男人静静伫立在清晨白雪中,黑色薄呢大衣肩头堆了薄薄的积雪。
簌簌雪花落在他身上,迅速消融。
氤氲白汽散开在他脸前。
冷空气浸透鼻腔,急促呼吸的酸涩刺冷,简直要让我落泪。我连忙跑到他面前。
他转首看见我,眼光高傲冷漠。
我笑:“你来了。来了。”
我伸手想给他掸掉身上的雪,他轻轻退后一步。
我讪讪缩手,又问:“等了,等了很久么?”
长久沉默。
他微微低头,微皱着眉头,仿佛是在问自己:“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
他退去温和内敛的惯常姿态,声音如同冬雪覆盖下冷硬的岩石:
“你从哪里来?”
“你跟廖启望,很熟吗?”
他果然知道我去了哪里。
我抬头直视他冰冷双眼:“他家里有病人,要回去拿药,让我陪伴两天。”
我想了想,又说:“我与他不是很熟。我走得太匆忙,把手机落在酒店。”
我将手套摘下,试探着握一握他冰冷左手。
“赫连煮了咖啡。要不要上去喝一杯,暖暖身子。”
他面部仍很僵硬,只是眼光温和下来。
他跟在我身后,轻轻说:“只有这一次,下不为例。”
房间堆着一地的行李,大大小小的箱子散开,满满的衣服散乱摊在床上和椅子。
熏然的暖气让人意态放松。
我倒了热咖啡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水杯,端给他。
我尴尬笑:“刚换新房间,有三分之二是赫连的。”
他坐在床边,环顾四周:“公司不舍得给你们订两个房间?”
我换衣服,将箱子阖上:“赫连有幽闭空间恐惧症,不敢自己睡。”
赫连穿得十分骚情,高昂着头推开房门:“哈,哈,你都猜不到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他看见蔡邵雍沉默坐着,十分困惑,说:“唉?蔡——你好。来啦?”
蔡邵雍点头。仍沉默。
我将他推出房门:“你到楼下咖啡馆坐一会。”
他探头探脑:“这奇怪了,他不应该在这里啊。”
又说:“航空与高速还是不行,都在滞留。只好走铁路,助理买到了高铁,下午三点的票。”
我心不在焉点头:“好好。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
他兴奋,说:“周锦聚打电话,约我吃饭。”
“……”
我想说问的不是这个。
我转身关门。
蔡邵雍躺倒在床上,闭眼假寐。
他拍着床侧:“过来陪我坐一会,我马上要走。我很累,睡一会。”
我坐在床侧,拍松枕头,半躺下去,笑着说:“好像每一次见面,你都在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睡觉。”
他呼吸渐渐悠长:“嗯,昨晚开了一晚车,精神太紧张。”
我给他盖好被子,小声道:“你回云城吗?是的话咱俩顺路。不如我跟你开车回去怎么样?”
过了好长一会,长到我以为他已经熟睡。他微微一笑并未拒绝。
他睡得很沉,我轻轻关门出房间。
赫连独坐咖啡厅吃蛋糕,神情悠闲。吧台侍应生趁大堂经理转身,掏出手机咔嚓。
过一会又咔嚓。
赫连呆呆拿着小银勺:“……”
我吃不惯牛排西餐,捧着自带的咖啡喝着香甜:“我定了包间,待会一起吃个饭吧。”
他疑问:“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以为只有那一次见面。”
我推诿:“后来又有几次,只是普通朋友。”
赫连不信,但他很有分寸不再追问:“你小心,他还有别人,不在一个阶层,咱们都招惹不起。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你一向比我更清楚。你不是马上合约到期吗?”
我点头,心乱如麻。薛霭明曾笑言若是有一日她有时间,我有金钱,沿着世界地图画出的线路,环球走上一圈,然后定居英国乡下,买一片牧场,读大学哲学系,相守终老。
人虽然风流云散,但该走的路我还是要走。况且这几年钱也赚得差不多,加上父母留给我的商铺,只要不奢侈,做个安稳的中产阶级绝对足够。
赫连向往加拿大,要沿着密西西比河垂钓。说不定还可以时常聚会,一起回忆过往的辉煌。
我捧着咖啡杯低声道:“不过是一时兴起,你知道他们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得到了不过图个新鲜,很快就会转移目标。”
这个职业,原本也算是奢侈消费品。
城中富豪步步紧跟欧美风潮,说穿只为一张皮相,不论男女。他们迷上黑发黑眸的东方神秘女郎,这边立刻转向睿智头脑,诸如律师等高智商女子,不光有外表还要讲内涵;后来又一窝蜂喜欢运动员,很快便会搭上政府高层子女,一日三变,最擅长自己推翻自己。
赫连笑:“周锦聚竟然要挖我跳槽,去他家下属公司,开出的报酬很丰厚。哇,真动心。”
他在圈中凭借自身实力,再加上贵人相助,料定会走得比我远,我想了想:“你看着办,事情未成之前不要乱说话。”
他笑,目光里有真正的向往:“我弟弟明年毕业,我可以松一口气。到时咱俩携手开拓欧美市场,而且在国外,我俩还充满异域风情。”
我讥笑他:“是,你不知道金发碧眼老外有多喜欢东方男人。你这类型向来比我受欢迎。我看好你哟亲。”
☆、第十八章
回程路上美妮姐电话不断:“今晚大场合,公司老板都出席,不是拼盘演唱会也不是个人独奏,是慈善基金,多少名媛亮相,你要打起精神,好好招呼,明不明白?”
又想起来,说:“你要是走了,我床边空虚,找谁代替你好?赫连行不行?”
接着絮叨:“礼服在方如晦那里,你俩一起。注意跟紧他。”
我反问:“难道他又要再婚?”
美妮姐冷笑:“当然,你什么时候见男人忍得住寂寞?这样好机会,早就按捺不住了。这次我们好说好散,帐算清楚了,谁也别再欠谁。”
方如晦一向神思诡谲,天价违约案吵得震天响,看来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将他卖个好价钱。
高速雪途艰难,橙色车辆刺耳鸣笛不断来回穿梭。
我关了手机,车内顿时静谧。
蔡邵雍微笑:“你也很忙。而且很八卦。”
我舒服倚着椅背,“那我应该正好借着你在的大好时机,问一问传说中最终极的大新闻。”
他竟然立刻想到我指的是谁:“蔡仲勋是我堂弟。他父母姨表近亲结婚,所以他有精神分裂。”
我哦一声,奸笑:“不,我指的不是他。”
我把吸管插到咖啡杯,他咬着慢慢喝。
我偏头看:“你们看起来还挺像。”
他说:“但我比他好看?”
我笑了起来:“不,都不好相处。”
他看着前方,问:“他有没有为难你?”
我摇头,转换话题:“其实我想问,某大老板儿子娶得是帝都高干,是不是真的?”
他含笑,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咂舌:“哇。他那么有钱。也要走政治联姻道路。”
蔡邵雍看我一眼,说:“云城只是小地方。内地有钱人一抓一大把,他算不了什么。政治面前,我们都算不了什么。他的生意口恰好归属亲家管辖,自然想要如虎添翼。为完成这桩婚姻,去年一年白了半边头发。”
他示意要咖啡:“今晚慈善基金拍卖不少物品,你更喜欢什么?”
我笑:“其实我也有份参与,许心暖给我留的字画我请人代卖,所得款项我会亲自带着去盖希望小学。”
蔡邵雍:“你信不过他们?”
我反问:“你信得过他们?”
他赞赏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听说你是钻石人物,大把名媛要将你抢回家。”
他也笑,问:“那你要不要去抢?”
我啜着吸管咪咪笑:“我手段毒辣,一般不用抢的,都用偷的。”
车流暂时停顿,据说有货车横亘路面,装载的羊群获得自由,四处漫步。
我趴在车窗户看远方大雪茫茫覆盖田野。
他轻拍我肩膀。
我回头,迅即被紧紧吻住。
这个吻泛起内心深处最深的疼痛,我呼吸窒息手脚僵硬,眼中泪水几乎要流出来。
少顷唇分,他额头抵住我额头:“早就偷走了。”
有奇妙的暖意和辛酸。
身体反应最真实。我骗不了自己,苦着脸落下窗户,任凭寒冷风气呼啸灌进小小车厢。
他启动汽车,温和说道:“要是感冒发烧,晚上就不能见到薛霭明了。”
这个小心眼的家伙。
我关窗闭眼:“我睡一觉。有情况你叫我。”
赶到云城已是晚上七点。厚重圣诞气氛在这座殖民老城弥漫渗透,到处都有人喜气洋洋,商家拼命促销,卖场人满为患,下雪天又堵车,紧赶慢赶到酒店已经人头攒动。
我敲开方如晦房门,看到熙熙攘攘的男女老幼均是正装,人人挤在镜前窃窃私语,气氛十分喧腾。
身着宝蓝紧身细腰礼服裙的美妮姐一把将我抓过去,说:“化妆!造型!就等你了!”
我伸着手臂抬着脸面对冲上来的化妆师和造型:“好像我家就是云城,但我竟然有一个月都没进过家门!”
方如晦身姿挺拔站在旁边,不忘给我脑筋急转弯:“四位顶级大牌同时出现现场,只有两间化妆间,怎么办?谁该第一个谁该最后一个?”
我张口结舌。他得意回答:“全都关掉。”
我怒目注视他。
他颔首微笑:“不错,今晚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才挤成一团。
慈善会场陆续有嘉宾到来,主办方别出心裁随意配对,有一位女士出场便会招呼一位男士相陪,结果赫连昏头昏脑扎错对,司仪叫他名字已是笑的颤音:“女士嘉宾,赫连名扬。好的,现在出场的是凌博仁。”
立刻又有人吹了口哨,我俩严肃握手,对了对拳头。他将手臂放在我臂弯,还不忘四处含笑致意:“今晚落实咱俩的奸情,待会我会请你跳舞。然后共度云雨如何?”
我禁不住老脸微红,在闪烁的灯光中保持微笑,红地毯长的一眼望不到头:“为何我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都要干这些无聊的事情。”
他笑:“这就是你的工作啊。”
赫连与我走进金碧辉煌偌大会场,绅士淑女们各自站立,灵活的waiter在其中穿梭,远处舞台上主持人在调音,嗡嗡嗡的声浪不绝于耳。
我立刻就失去了前面方如晦的身影。
赫连托住我肩膀,“哎哎小心。”我诧异看他,他摸一把自己的胸:“刚才是何美娜。上周刚去瑞士回来。唉,她,唉。”
我忍俊不禁,他递给我红酒:“下周元旦我有访谈,约你当采访嘉宾,你给我好好背稿子。”
我四处乱看,见到有熟悉面庞就举杯示意。他又说:“公司想我口味太重,决定要我扶持新组合。”
我笑:“七八个小姑娘你都下得了手?大叔。”
他说:“也就是两个吧。你帮我一



![情敌变夫夫[全息]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41/417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