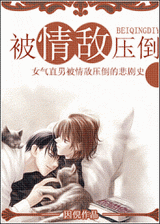头号情敌-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忠心耿耿。”
赫连坐在椅子上,腰胯耸动,慢慢做波浪起伏状,“忠——心——耿——耿——”
门开了,周锦聚脸色平静走进来。
赫连吓的笑容都僵硬,不敢回头。
三个人都立刻转移话题,谈论当地天气。
他缓步上楼。
赫连看他平常如昔,抚着胸口说:“吓了我一跳!以后这样事情不能再说。”
蔡仲勋将杯子在圆桌上打圈,目光灼灼盯着我看。
脚步声响起。是周锦聚。
蔡仲勋含笑抬头看了一眼。
周锦聚仍是脸色平和,嘴角甚至有些笑意。
长筒军靴一级一级踩过木头台阶。声音不疾不徐。
黑黝黝的猎枪逐渐露出,握在他右手。
我看见蔡仲勋神色巨变,诧异回头。
与此同时,周锦聚右臂倏然上扬,清脆响过咔嚓一声,子弹上了膛。
蔡仲勋猛虎扑食般向我扑来,连连撞到好几把餐椅。他拖着我胳膊,不管不顾向门外跑去。
我愣怔,与他连滚带爬窜出门外——不,是我自己连滚带爬,蔡仲勋躬身紧紧抓住我衣领,勒的我几乎不能呼吸。
我俩狼狈逃出门外,我瑟瑟发抖,紧紧拥抱他,两个人站在草坪中间。
房门关闭,少顷,劈啪!咔嚓!轰隆!各种家具坍塌巨响连成一片,震得房顶都在微微摇晃。
沉重的撞击声响起,像是椅子砸到什么物体。
这是刀具,这是玻璃破碎,这是——不知道是什么,是混合音响。
除了玻璃铁器木头之类物品的碎裂声,他两人没有半点声音。
我吓得不住颤抖:“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蔡仲勋轻拍我的背。
我说:“怎么都不出声?”
蔡仲勋回答:“家丑不可外扬。”
我听着屋中剧烈震响:“万一他火气太大,真的开枪怎么办?”
蔡仲勋事不关己,轻轻摇头。
我握住他胳膊:“加拿大是法制社会!”
蔡仲勋无所谓的表情,又说:“是我就会开枪。先崩了你再自杀。”
我惊恐扭转眼,见沙皮多莱仕三条腿站立,在他家枫树下姿势猥琐。
蔡仲勋拉着我向越野车走去:“不如我带你逛逛冰雪之城?现在没有下雪,但有几家好餐馆。我估计主人已经没有心情做晚餐,我们自己动手打包好了。”
我与蔡仲勋逛完小镇,几乎连城镇大超市都全盘观摩,带着琳琅满目的战利品回他家,果然仍是冷锅冷灶。
厨房中物品都已更换,焕然一新。下午我喝橙汁,十分喜欢的德式日耳曼水晶杯也不见了踪影。
好效率,好速度。
赫连鼻青脸肿坐在餐桌旁边喝咖啡,心平气和。
他起身帮我摆放盘碟,一条腿一瘸一拐。
我看他神态自若,只好低声问:“你们——没什么事情吧?”
他自嘲:“哪有夫夫不吵架。”
我狐疑打量他,“要是怕冷战,我们也可以带你去市区酒店,凑合一晚再道歉也好。”
他仍是一脸坦然:“打死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放心。”
周锦聚面色平静坐在桌前,慢慢擦拭银餐具。
赫连将专用咖啡杯端到他面前。
他见我一脸纳罕,笑着说:“他在这儿,我能去哪?”
我想起很遥远的过去,一些早已模糊的事情,有人也对我说过,心在哪,人就在哪儿。
四个人坐下来吃晚餐,气氛倒也安谧。
我试图打开话题:“车库旁边纸箱子中有项圈,是你们准备养狗么?”
周锦聚喝咖啡,回答:“就是给狗带的。”
赫连冷嘲:“狗带着干的你。”
周锦聚沉默一会,才说:“我愿意让狗干,是因为我爱那条狗。”
蔡仲勋一刀划出碟子,声音刺耳难听。
我:“噗……”
赫连说:“我就是狗,打死也会守在门口。”
我:“……”
电话响起,我几乎眼含热泪接起,是蔡邵雍的助理。
我勉强维持笑意听完,扣掉电话。
赫连注意到我的慌乱。
我说,“蔡邵雍病了。”
蔡仲勋将盘中的胡萝卜偷偷扔到我盘中。
我看他,说,“你到底跟他胡说了些什么?”
作者有话要说:明天即将终结。稍后过几天会写古风耽美文。请各位继续捧场O(∩_∩)O~
☆、第五十四章 ? 结局
蔡邵雍于出差途中突然倒下。
仿若很久以前,他曾感慨:“我有好友昨天取得某品牌的东亚代理权,晚上聚餐还跟我讨论工作安排,今天凌晨突然去世,竟然是肾癌。”
他也笑我:“懒人才有懒福,比如你。”
我不得不中断行程,提前回城。
常年疲惫工作,压力巨大,遍布的勾心斗角组成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倾诉也无处倾诉的负面情绪积累,早已使他超负荷运转,疲惫不堪。
医生说这是身体预警,迫使他自我保护的人体机制。要求他卧床休息,停止一切工作。
有一日蔡仲勋去看他,发表噩耗:“他死了。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生的车祸,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有,碾碎在车轮底下,还有一些可能被来往旅人捡走。他们通过车牌号找出租车人。”
蔡邵雍静静听完,只说了一句话:“你终于满意了。”
他们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我不能让新闻报纸宣称我客死异乡,我有父母朋友都在云城,更不能让蔡邵雍雪上加霜。
可恨的蔡仲勋,我明明第一时间拼凑手机,给他打求救电话,他联系薛霭明,派人才将我接回。
蔡邵雍回檀城修养生息,我求他带我去,竟然被无情拒绝,还被无中生有安上许多罪名,指责我朝秦暮楚朝三暮四。
我就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便是加上薛霭明和蔡邵雍,他蔡家小少爷也不是那“楚”和“四”啊。
去往别墅的路途太过遥远,我一个人起初散步,心态自然,后来走到心头火起,打电话骂蔡仲勋忘恩负义,再后来他犯了少爷脾气,悍然关闭手机。我只好一个人认命般,忍辱负重走在路上。
彼时天气阴沉,海边风气夹杂水汽扑面而来,道路两旁不知名野花甚多,我摘了许多,捆成一束。
我终于跋涉到别墅外郁郁葱葱的花坛。
他名下产业众多,这栋别墅却是唯一一座在山林之中,四周古木参天,平日少有人来,取退隐之意。
他在树下草坪躺着,闭目养神,身上盖着薄毛毯。
我走到旁边仔细看他,一眉一眼,一笑一怒,刚直唇线,英俊面庞,都与我记忆中宛若一致。
他睁开眼,眼神平静,有些欣喜。
也许时间最大的可怕,在于它让人渐渐变得习惯,习惯了分别,习惯了软弱,习惯了漫长,习惯了没有彼此心灰意冷的时日。
也许那些压抑,软弱,逃避,那句如果分手,你会怎么办所表达的深刻落寞,和一些注定落空的希望,已经失望的希望,将离别后冷淡的人生摧毁的面目全非,到最后我们回头看,始终一无所获。
也许相见便注定在劫难逃,纵然伤痛一生,也无法确认这一场没有未来的爱情,是否是人生的不虚此行。
也许再见我仍然双手空空,一贫如洗。但我曾经将最丰裕的爱意都堆积在你脚下,以献祭的姿态,那样没有任何保留的爱过你。
我躺倒他身旁,把花放在他肩侧。
许久之后,他才慢慢搂住我。
“你回来了。”他说,“蔡仲勋打过电话。”
虽然病态支离,但已经恢复元气。
我在他胳膊上蹭了蹭,舒坦的长叹一口气。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的生意,相互倾轧的下属,兄弟睨于墙,我的旅途见闻,生活糗事,土著风情,遇到过的致命危险,还有心愿达成的心满意足。
聊起很多人,有他的三个孩子,还有蔡仲勋。
那时我曾不敢面对慌张逃离,而现在,我已能够平静倾听所有一切。
……
我在别墅的海边漫步,蔡仲勋站在礁石上眺望大海。
湿凉海风吹皱他衣衫。
他转脸看我。夕阳下颇有些睥睨万物,眼神妖娆:“我可等到你了。”
我站在沙滩,仰首看他。
他手上有我的nassu戒指,我腕上带着他的手表。
他满脸嫌弃的摊开掌心:“那天仪式被打断,今天要在这完成。”
那时赫连打过惊天动地一架,我竟然忘记这件事情。后来时过境迁,他屡发无名怒火我才想起。我要求补救,以身体作为交换条约,才换来小少爷高傲点头。
我笑:“为何选择这个地方?”
他拧眉:“不放心。蛊惑人心的本事,蔡邵雍敢认第一,我家里无人敢认第二第三。”
他拉着脸伸出左手,让我给他戴上。
故事的结局竟然回到最初,像当初我曾经去退戒指,经理满脸遗憾的说抱歉,一脸同情地看我。
那时我胡子拉碴满面沧桑,身体语言透露出不堪的打击。
后来我终于走出伤痛,去问能否再买,却被告知早已有人买走时,又重新经历第二次深刻打击。
他的手表是廖启望赠我的车马费。我将它压到箱子底,早已遗忘。要去旅行前翻了出来,并且觉得如果遇到困难,还可以换些必要费用。
我朝他晃晃腕上的手表:“限量版哟亲!全球只有八只哟亲!”
他看着自己手指上的戒指,再看看我。吐一口滚烫的气:“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插。你了。”
我:“……”
☆、番外*幻想小剧场
蔡仲勋等我回家。唧唧歪歪不满意:“鱼都不新鲜!西红柿炒鸡蛋很难吃!”
我大怒,踹他腿:“你昨晚骗我,说什么我做菜水平大涨!”
他吼:“因为要骗你上床!”
我大喊:“你这个骗子!你骗我要去英国,结果我现在还在云城!你藏我护照,我想跑都跑不了!”
他声音比我还大:“你左手一个戒指右手戴一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你心里还有蔡邵雍,你就想逃避!”
我说:“是!谢谢你提醒我!他做饭比你好吃,时间也比你长,你嫉妒!”
他气坏了,扑上来撕我衬衣:“我让你看看谁时间长!我让你到处勾引人!我让你淫。荡!”
手机响,我头朝下,躬着身子从沙发上捞起:“喂——喂,你好。”
我想站起身,腿有些发软。
臀被掰开,清凉的润滑剂挤到内部,被摁在沙发靠背上,就这样缓缓贯穿。
十指紧紧扣入臀肉,不断揉捏。
我窒息,失神了一会。
电话那端:“是我。我来云城开会,想看看你,你在家么。”
是蔡邵雍。
背后的动作也是一滞。
我反手握住他绷紧的手臂。
他将丝帕塞入我口中,用领带勒紧,在我脑后打了一个结。
我只能仰着头无声流泪。
他接过电话,□缓缓研磨:“哥,他不方便。”
蔡邵雍疑惑:“你怎么……”
他反应过来:“……你!!!”
蔡仲勋说:“要不要开扩音器?让你听听他的声音?”
我无声的挣扎。
蔡邵雍沉默一会,声音疲惫:“我离婚了。”
蔡仲勋张张口,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挂了电话。
*****************幻想小剧场*****************
柔软的跳蛋在后。庭反复不停地蹂躏那一处。
性。器笔直修长,阴。囊紧紧贴在根部。光滑漂亮,被剃得干干净净,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哥,送你的离婚礼物。”他恶意地说:“里面洗的很干净,他很懂得保养的。”
蔡邵雍坐在沙发,双手抱胸,目光深邃。
“爬过去。”他说,“自己摘下口里的那一根。”
我爬到他身侧,仰起头,目光慌乱地看他,我抽出唇里的仿真阴。茎,太深太长,几乎卡到喉咙。
电流加大,我瞬间瘫软在他腿上。
蔡邵雍深深呼一口气,冷冷道:“拉开。”
我羞耻的动手,解开他腰带,握着他粗长的阳。具,吞到喉咙。
他微微闭眼,手放在我后脑勺。
“我受不了了。”蔡仲勋说,“来一起干吧。”
跳蛋被抽出,我猛的窒息,嘴唇都在震颤,蔡邵雍立刻粗重的喘息。
后。庭失守,迅猛的撞击快感迸发。
我将手挪到□,凌乱的自己亵渎。
他猛地抽出,跳蛋被重新塞入。
我被翻过身,两腿大开,仰躺在地毯上。
嘴里深嵌一根,几乎到喉咙。
□被含住,令人战栗的炙热。
他在喝热水,吐出,然后将我包裹。
那种炙热和湿润,将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刺激到底。敏感的细筋被左右擦拭,这种快感,凌驾于所有精神和思维之上。
那朵蝴蝶结时隐时现。
我双腿伸到半空,一动不



![情敌变夫夫[全息]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41/417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