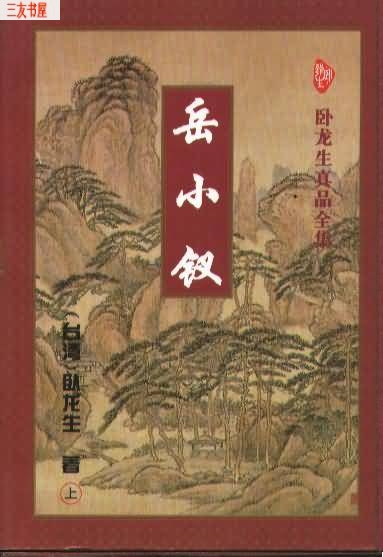金陵十三钗-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窑姐们回到她们的栖身处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孟书娟都闷头闷脑坐在那里。她气得浑身虚弱,一百句羞辱这群女人的话在她心胸里憋着。她恨自己没用,为什么当场没想出那么精彩的杀伤性语言,及时把它们发射出去。
所有同学回到阁楼上去了,书娟还在那里想不开。她坐到黄昏都进入了室内,坐到自己腹内剧痛起来。没人有告诉过她,这样可怕的疼痛会发生;这本应该是母亲的事,而母亲现在缺席。隔着地板,她能听见地下室的声音:打麻将、弹琵琶、打情骂俏。是的,惯于打情骂俏的女人在没有男人的时候就跟女人打情骂俏。
坐在昏暗中的孟书娟听着外面枪响不断。短命的日本人把仗打到南京,把外婆外公打得消息全无,把父母和妹妹打得不敢回国,把一帮短命窑姐打到英格曼神父“最后一片绿洲”上来了,书娟实在太疼痛太仇恨了,咬碎细牙,恨这个恨那个,恨着恨着恨起了自己。她恨自己是因为自己居然也有地下室窑姐们的身子和内脏,以及这紧一阵慢一阵的腹痛和滚滚而来的肮脏热血。
下午英格曼神父也出去了一趟。陈乔治开车载着他往城内走了一两公里,就退了回来。他们不认识这个南京了;倒塌的楼房和遍地的横尸使陈乔治几次迷路。在接近中华门的一条小街上,他们看见日本兵押解着五六百个中国士兵向雨花台方向走,便停下车。英格曼神父奓起胆子,客气地向带队的日本军官打听,要把战俘们押到哪里去。随行的翻译把他的意思转达过去后,军官告诉他:让他们开荒种地去。他脸上的表情却告诉你:他才不指望你相信他的鬼话。英格曼回到教堂,晚餐也没有吃,独自在大厅里坐了一小时,然后把所有的女学生们召集到他面前,把下午他看到的如实告诉了她们,他温厚地看看法比,说自己早晨的判断太乐观,看来法比是正确的,在找到新粮源水源之前,保证这三十多人不饿死渴死,是他最大的抱负。他叫陈乔治再搜一遍仓库,看看还能找到什么,过期的、发臭的、长毛的都算数。
神父没有说完,侧门口冒出几个窑姐。她们挤在那里,看看大厅里有什么好事,有了好事是否有她们的份。一看女生们个个沉脸垂头,都不想有份了,一个个掉头出去。但法比叫住了她们。
“以后你们就躲在自己的地方,不要上来。特别是不要到这里来。”法比说。
“这里是哪里?”一个窑姐还是没正经。
“这里就是有学生的地方。”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突然说:“大概是永嘉肥皂厂着火了。肥皂厂存的油脂多,火才这么大。”
跟着他的目光,所有人看见刚才已经暗下去的黄昏,现在大亮。书娟和同学们跑到院子里,火光照亮了教堂主楼上幸存下来的玻璃窗,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圣母圣婴像在米字形纸条下闪动如珠宝。女孩们呆子一样看着如此瑰丽的恐怖。
火光给了人们极好的却诡异的能见度。被照得通明的地面和景物在这样的能见度中沉浮。
阿顾和陈乔治判断火光的来源,认为起火的只能是五条街外的永嘉肥皂厂,法比让女孩们立刻回阁楼上去。这是个随时会爆发危机的黄昏。
女孩们离开后,叫红菱的窑姐们叼着烟卷在圣经工场门口打转。
“你这是要去哪里?”法比大声说。
红菱低头弯腰寻觅什么,被法比吓了一跳,烟头掉在地上。她撅起滚圆的屁股,把烟头捡起来。
“东西丢了,不让找啊?”她笑嘻嘻的。
“回你自己地方去!”法比切断他们间对话的可能性:“不守规矩,我马上请你出去!”
“你叫扬州法比吧?”红菱还是嬉皮笑脸。“老顾告诉我们的。”
“听见没有,请你回去!”法比指指厨房方向。
“那你帮我来找嘛,找到我就回去。看看你是个洋老爷,一开口是地道江北泥巴腿。”她笑起来全身动,身子由上到下起一道浪。
书娟和女同学们现在都在阁楼上了,三个窗口挤着十六张脸。十五张脸上都是诧然,只有书娟以恶毒的目光看着这个下九流女人如何装痴作憨,简直就是一块怎么切怎么滚的肉。
“法比也不问问人家找什么。”红菱一嘟嘴唇。
“找什么?”法比没好气地问。
“麻将牌。刚才掉了一副牌在这里,蹦得到处都是你还记得吧?捡回去一数,就缺五张牌!”
“国都亡了,你们还有心思玩?”
“又不是我们玩亡的。”她说:“再说我们在这里不玩干什么?闷死啊?”
红菱知道女孩子们都在看她唱戏,身段念白都不放松,也早不是来时的狼狈了,一个头就狠花了心思梳理过,还束了一根宝蓝色缎发带。
窑姐中的某人把赵玉墨叫来了。五星级窑姐远远就对红菱光火:“你死那儿干什么?人家给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回来!”她说话用这样的音量显得吃力,一听就不是个习惯破口叫骂的人。
“你们叫我来找的!说缺牌玩不起来!”红菱抱屈地说。
“回来!”玉墨又喊,同时上手了,揪着红菱一条胳膊往回走。
红菱突然抬起头,对窗口趴着的女孩们说:“你们趁早还出来!”
没人理她。
“你们拿五个子玩不起来,我们缺五张牌也玩不起来。”红菱跟女孩们拉扯起生意来了。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一个胆大的学她的江北话:“……也玩不起来……”一声哄笑。
法比呵斥她们:“谁拿了她的东西,还给她!”
女孩们七嘴八舌:“哪个要她的东西?还怕生大疮害脏病呢!”
红菱给这话气着了,对她们喊:“对了,姑娘我一身的杨梅大疮,脓水都流到那些骨牌上,哪个偷我的牌就过给哪个!”
女孩们发出一声作呕的呻吟。有两个从窗口吐出唾沫来,是瞄准红菱吐的,但没有中靶。
玉墨戗着红菱往厨房去。红菱上半身和两条腿拧着劲,脚往前走,上身还留在后面和女孩们叫阵:“晓得了吧?那几个麻将牌是姑娘我专门下的饵子,专门过大疮给那些手欠的,捡了东西昧起来的!……”她嘎嘎地笑起来,突然哎哟一声,身体从玉墨的捉拿下挣脱,指着玉墨对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陈乔治说:“她掐我们哎!”似乎陈乔治会护着她,因此她这样娇滴滴地告状。
女学生们恋战,不顾法比的禁令,朝眼看要撤退的窑姐们喊道:“过来吧!还东西给你!”
红菱果然跑回来。阁楼窗口上一模一样的童花头下面,是大同小异的少女脸蛋,她朝那些脸蛋仰起头,伸出手掌:“还给我啊!”
叫徐小愚的女学生说:“等着啊!”
赵玉墨看出了女学生居心不良,又叫起来:“红菱你长点志气好不好?”她叫迟了一步,从三个窗口同时扔下玩游戏的猪拐骨头,假如她们的心再狠一点,手再准一点,红菱头上会起四五个包,或者鼻梁都被砸断。
法比对女孩们吼道:“谁干的!……徐小愚,你是其中一个!”
但孟书娟此刻推开其他同学,说:“不是小愚,是我。我干的。”
玉墨仔细看了书娟一眼,看得书娟脊梁骨一冷。假如被鬼或者蛇对上眼,大概就是这感觉。
红菱不依不饶,一定要法比惩办小凶手。
玉墨对她说:“算了,走吧。”
红菱说:“凭什么算了?!”
红菱露出她的家乡话。原来她是北方人,来自淮北一带。
玉墨说:“就凭人家赏你个老鼠洞呆着。就凭人家要忍受我们这样的人,就凭我们不识相不知趣给脸不要脸。就凭我们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
女孩们愣了。法比一脸糊涂,他虽然是扬州法比,虽然可以用扬州话想问题,但玉墨的话他用扬州思维也翻译不好。多年后书娟意识到玉墨骂人骂得真好,她骂了女孩,骂了法比,也骂了世人,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的低贱。
第三章
晚上,火光更亮了,亮得女孩们都无法入睡,书娟旁边是徐小愚的铺,徐小愚的父亲是江南最大富翁之一。他的买卖做到澳门、香港、新加坡、日本。南京抵抗日货的时候,她父亲把日本货全部换了商标,按国货出售,一点都没有折本。他跟葡萄牙做酒生意,成吨的红白葡萄酒都是他用廉价收购的生丝换的。威尔逊福音堂做弥撒用的红酒,也都是他捐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天夜晚,藏在地下室仓库里的秦淮河女人们喝的,正是徐小愚父亲捐的红酒。
对徐小愚父亲徐智仁的研究,我比我姨妈要做得彻底,因为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里,他将要跑个龙套。现在还不是他出场地的时候。徐小愚和孟书娟的关系很微妙,今天两人是至好,明天又谁也不认识谁。徐小愚是个漂亮女孩,好像不明白漂亮女孩容易伤害人,最容易伤害的是欣赏她、羡慕她、渴望她友谊的女孩。我姨妈书娟就是这么个女孩。书娟易受小愚的伤害,还因为她暗暗不服小愚,因为她功课拔尖,长相也算秀美,但有了小愚就永无书娟的出头之日,这样的一对女孩,往往有着被虐和施虐的关系,并且被虐一方和施虐一方常常互换位置。
小愚把一条胳膊搭在书娟腰上,试探她是否睡着了,书娟觉得马上反应不够自尊,因为小愚昨天是苏菲的密友,今天傍晚小愚用猪拐骨砸那个叫红菱的窑姐,书娟存心替她担当了罪责,就是要小愚为自己的变心而自责。果然,书娟一举把小愚的心征服了。小愚在自己的胳膊上增加压力,书娟动了一下。
“你醒了?”小愚耳语。
“干什么?”书娟假装刚醒。
小愚趴在书娟耳朵上说:“你说哪一个最好看?”
书娟稍微愣了一下,明白小愚指的是妓女们,她其实谁也没看清;不屑于看清,除了叫玉墨的那个女人的脊梁。但她不想扫小愚的兴;刚刚弥合的友情最是甜蜜娇嫩。“你看呢?”她反问,同时翻身把脸对着小愚。
“那我们再去看看。”小愚说。
原来女孩们都一样,对花船上来的下九流女人既嫌弃又着魔,她们一想到她们靠两腿间那绝密部位谋生,女孩们就脸红地“啊哟!”一声,藏起她们莫名的体内骚动。罪过原来是有魅力的,她们不敢想不能干的罪过事物似乎可以让这些做替身的去干。
书娟和小愚悄悄来到了院子里,火光把院子里照得金黄透明。草坪中央苍老的美国山核桃树顶着巨大树冠,光秃秃的枝桠抓向天空,如同倒植的树向金黄夜晚扎根,一股奇怪的焦臭在气流里浮动。
两个女孩站在院子里,忘了偷跑出来要干什么。好像单为了看看英格曼神父的红砖小楼是否还在那儿。又好像单为了看看法比的卧室窗口是否还亮着烛光。然而,琵琶弹奏的音符敲醒了她们。
地下仓库的天花板高度正达书娟的大腿。沿着厨房往后走,就会看见仓库的透气孔。一共三个透气孔,上面罩的铁网生了很厚的锈。透气孔现在就是书娟和小愚的窥视口。
琵琶弹奏是从豆蔻手指下发出的。豆蔻生得小巧玲珑,桃子形的脸,遮去她下半个脸来看,她整天都眉开眼笑,遮去她上半个脸,她整天都在赌气,人家借她米还她稻似的。不管怎样,豆蔻是个美人,若不是这副贱命,足以颠倒众生。两个女孩通过窥口进行的选美,初选结果已决出。
仓库已经不是仓库了,是一条地下花船,到处铺着她们的红绿被褥,狐皮貂皮,原先挂香肠火腿的钩子空了,上面包上了香烟盒的锡纸,挂上了五彩缤纷的绿中、纱巾、|乳罩、肚兜……四个女人围着一个酒桶站着,上面放着一块厨房的大案板,稀里哗啦地搓麻将。看来缺五张牌并没有败她们的玩兴。每人面前还搁着一个碗,装的是红酒。
“呢喃!你让我打一圈吧?”豆蔻说。
呢喃用塗蔻丹的手指扒拉一下右眼的下眼皮。这个哑语女孩们都懂;少妄想吧;你眼巴巴看着吧。
“哎哟,闷死了!”豆蔻说。拿起呢喃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
“那你去洋和尚那里讨两本经书来念念。”玉墨逗她地一笑。
“我跑到洋庙的二层楼上,偷偷看了一下上面有什么。”红菱说:“都是书!扬州法比住在那间大书房隔壁。”
“我也看到了。能拿书去砌城墙了!”黑皮女人说。
“玉笙跟我一块上去看的。”红菱说。
两个女孩对看一眼,又看看叫玉笙的女人:那么个黑皮还“玉”呢!
“那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姐妹们就进修道院吧。”红菱说着,推倒一副牌,她和了。
小钞、角子都让她扒拉到自己面前。
“去修道院蛮好的,管饭。”玉墨说。
“玉笙,你那大肚汉,去当姑子吃舍饭划得来。”呢喃说。
“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洋和尚陪,才美呢。”红菱笑嘻嘻地说。
()好看的txt电子书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玉墨?”
“叫什么都一样,都是吃素饭,睡素觉。”玉墨说。
“吃素饭也罢了,素觉难睡哟,玉笙!”
说着大家哄起一声大笑。玉笙抓起一把骨牌向红菱打去。大家笑得更野,说红菱今天为麻将挨了第二次打,以后非死在麻将下面。玉笙和红菱在到处磕绊绊的仓库里追杀。玉笙说:“红菱你别急,明晚上就让你尝洋荤,姐姐我去给那个扬州洋和尚扯个皮条,你明晚就不用睡素觉了!”
红菱做了一个手势,两个女孩不懂,但马上明白那个很下流的手势,因为窑姐们笑翻了,玉笙笑得直揉圆滚滚的肚子。
玉墨心不在焉地看她们闹,自己独自坐在一个卧倒的木酒桶上,一手烟一手酒。
两个女孩看久了,对刚才初步评选的第一美人改了看法。赵玉墨在她们眼里每分钟都更好看一点;她不是艳丽佳人,但非常耐看,非常容易进入人的记忆。她头发特别厚实,松散开来显得太重,把那张脸压小了。脸盘说不上方,也不说上圆,小小的,短短的,下巴前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