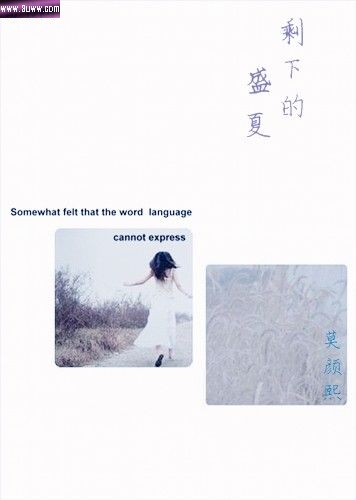盛夏的果实小薇子-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听都没听说过,所以他想都别想!
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单纯认为是面子的问题,那就实在大错特错了。
这种时候,这种理智没进入头脑的时候,面子,还没上升到被考虑进去的地位。
支持人类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判断的,是本能,是既有习惯,是既定思维。比如你听见蚊子嗡嗡,第一时间便是伸出手去,要么赶走要么拍死,至于考虑这蚊子是公是母,是叮人的还是吃草的,那是你有时间有空闲之后的事了。
张小芬远没到有时间有空闲的地步,她的一切行动,依然还在受她的既有思维方式支配。
她伸手了,没赶走,所以她只有拍死了。
张小芬脾气急,但她再急的脾气她依然想到了这事儿不能告诉程玉军,只要不告诉程玉军,一切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了,就上升为阶级矛盾,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现在,她没辙了,她管不了了,她没有办法,她只有告诉程玉军。
儿子是他们俩的。
程玉军是第二天早上知道的,因为一早上起来张小芬的脸就耷拉着,说什么话都带着气,做什么事都挑刺,于是程玉军嘻皮笑脸的问:“哟,二小姐,这又是怎么了?谁又惹着你了?”
二小姐又骂了一阵,终于抵不住那一阵关心的温暖,所有的委屈往外一涌,说了。
程玉军知道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拧了拧程知著房间的钥匙,一脚踹开门,捡起地上的棍子,举起来,没轻没重地往下挥。
张小芬自己打起儿子来也不分轻重,可是从旁观的角度看别人这样打,却是另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于是程玉军打,张小芬就在背后哭喊着拦,嘴里叫着:“你要打死他呀这是?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打死他,我后半辈子怎么过呀?”
程玉军一抬胳膊挥开她:“你起来!我今天非得打死他不可!你不是一直嘟嚷我不管他吗?我今天就管一个给你看看!我楔不死他!我叫你现眼!我叫你现眼!”
程知著抱着头蜷在地上,像卷成一团的烂纸团。
一个家庭中,相克的关系必须形成闭环,才能保持和谐稳定。比如说,如果儿子怕爸爸,爸爸怕妈妈,那么妈妈就应该怕儿子,这样儿子在这个家庭中才有活路和话语权,这样的家庭才算得上是民主的家庭。
在程家,这个环路圆环套圆环,极其错综复杂,也许今天你怕我我怕他他又怕你,但到明天可能就完全反过来了。
但总体来说,对于程玉军,这家里的终极大BOSS是他老娘,如果张二小姐从表面上似乎可以掌控他的话,那么他娘则是从本质上掌有实权的人物。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程知著那天之所以于乱棍之下讨得一线生机,完全归功于他奶奶的一声暴喝:“你先打死我吧!我也不活了!”
至此,这场家庭闹剧终于凑足了一切要素,红红火火热闹三俗地开张了,你想得到的一切情节,它将一点儿不落地发生,你见到过的一切桥段,它将一星儿不少地展示,所以,外国友人有一句话拿来形容我国再恰当不过:热闹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热闹的家庭各有各的不热闹。
第 28 章 不热闹的家庭
小时候听说书,老听见一句话,觉得很有文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为什么要各表一枝呢?让我们把外国友人的那句话托马斯全旋一下:不热闹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热闹的家庭各有各的热闹。
张慨言家的热闹和程知著家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家的热闹,热闹得非常之不热闹。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电视剧里一定要有几个小白级人物,三十好几了依然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不?那是因为不这样不热闹,不热闹没人看。
张慨言家就比较没人看,因为他们家就没那种长到三十好几依然不长脑子的人。
基本上张慨言在他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即使在其年少顽劣的时候,也没受到过程知著那样的待遇。
总体来说,赵彩凤的脾气属于温和型的,张新昌属于放纵型的,所以,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时,他们对于张慨言一向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对于这种教育方式的作用,他们认为很明显:全村有哪个孩子比得上他家张慨言的?
自打小学二年级之后,张慨言就没犯过原则性错误,别说原则性,就一般性错误他都没犯过。以他当时的社会身份,学习好就是硬道理,有了这个硬道理,其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张慨言家,张慨言是有一定话语权的,甚至某些时候,他的话是可以被奉为圣旨的。
但不是现在。
赵彩凤坐在沙发上,张慨言低头坐在她对面儿,俩人就那么坐着,干巴巴地已经过了有半个小时了。
“你们俩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没什么程度,豆豆的脾气你也知道,我不敢惹他。”
“是吗?你还挺有定力的,都住一块儿了,还没什么程度呐?”
“妈,我是喜欢豆豆可是我也不是……那个……吧,豆豆根本不知道我对他什么意思。”
“张慨言,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恶心呀?豆豆是谁?是你哥们儿!你最好的朋友!你天天看着人家脑子想着那么脏的事儿你有脸吗你?豆豆知道了怎么想!你让我怎么跟你小芬婶儿解释?是,你说走上学走了,我还得天天留在家里和人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你给人家儿子发这种短信,说这种话,叫我以后见着人家怎么抬起头来?!人家是大小伙子!不是小闺女儿!他们家要是生一闺女你爱怎么发怎么发我管都不管你,说不定我还支持你,咱两家怎么说也是知根知底的,我巴不得你们俩好。可是人家不是!人家跟你一样!你们小时候……,你……,我……,我怎么就没想到呀!我怎么就以为你们是小孩儿没长大闹着玩儿!我这心里还说豆豆反应也太大了,我还巴巴儿地跑人家家去求着人家原谅你,我早知道你是蓄谋的,打死我也没脸做这样的事!”
“妈你也别生气了,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以后不发了,赶明儿等我婶儿气消了我再跟她解释就说是我跟豆豆闹着玩儿的,学校里好多人拿这事儿开玩笑,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学校里哪个人没玩儿过国王游戏?国王让做什么就得做什么,豆豆也玩儿过,其他人做得比这过份的多得是……”
“张慨言。”
张慨言看了看他妈的眼神,停了嘴。
“你要是想不承认,那你就从一开始就别承认,现在人家已经知道真相了,你再去骗,你当人家别人都傻子吗?是,人家没你念的书多,没你会撒谎,可你也别忘了,年纪在那儿摆着呢,凭你,过两年再出来骗人吧。”
张慨言低着头,不说话了。
“行了,豆豆的事儿先不说了,反正只是两条短信,豆豆也不知情,大不了我再看人家几天脸色赔几天不是,张慨言,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着吧。”
“……”
“说话呀,你想怎么着?”
“我不想怎么着,不是刚才都说过了,我会去跟我婶儿解释清楚的。”
“张慨言!你别跟我装傻!”
“妈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不提这事儿了,就当没有过,我跟豆豆还是哥们儿,还和从前一样,还不行吗?”
“张慨言你甭跟我打太极,我现在在说你!你别扯上豆豆!锁你送给人家了,我也没脸往回要了,这事儿就算了,回了学校你就把你那房子退了吧,要不就让豆豆一个人住,你回你们学校去,毕业之前,给我领回个小姑娘来,张慨言,你领得回来,咱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你还是我儿子,领不回来,我也不在乎养你一辈子,你就准备准备收拾行礼回家吧,别在北京呆了。”
“妈……”
“行了,就这么定了,这事儿我也不跟你爸说了,我给你俩月时间,我看你怎么解决吧。”
晚上张慨言基本没怎么睡,不是因为他们家的事儿,他们家,他自信他应付得过来,他怕的是豆豆。
看小芬婶儿昨天的样子,肯定还没问过豆豆这事儿。自己倒是先担下来了,可她回家肯定是要问豆豆的,他现在不怕别的,只怕豆豆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
豆豆这人傻,一股子愣劲儿,你让他死容易,让他陷害别人,他绝对不屑于做。搁古时候,他就是个当大侠的料,搁现在,却实在让张慨言提心吊胆。
这事儿张慨言以前不止一次跟豆豆提过,俩人在一块儿,难保哪一天不被发现,张慨言当初千叮咛万嘱咐,让豆豆全推到他身上,只要全推到他身上,一切都好解决。但凡豆豆那股子愣劲儿上来,断不肯承认自己没份儿,那什么都难办了。
解决自己家,张慨言有百分百的信心,加上豆豆家,张慨言也并不太怵得慌,可是再加上一个豆豆,他就真没辙了。
现在这种时候,能怎么办?只能骗,骗得了一天算一天,骗得了一时算一时,他搭了台勾了脸上了装亮了相,这戏就算开了,那观的看的再怎么难对付,他自然有信心震得住他们,他十几年的功夫,他谁也不怕。
他只怕跟他搭戏的人。一个应该是个傻子的角儿,一个应该是个哑巴的戏,你在台上走两步儿,动几下儿,其余看他的就行,只要这么简单地一应付,下来的戏他都好唱。怕只怕,那傻子非要心疼他跟头翻得累,那哑巴非要怕他调门儿拔得高,自作聪明地要承点儿担点儿逗台下各位爷开心的任务,于是也张了嘴要唱,可不知道,他这一张嘴,这出戏,就算是砸了。
任他张慨言三头六臂,也救不回来了。
张慨言心里一直盼着豆豆他妈回家之后没跟豆豆提这事儿,可想来想去觉得不可能;接着他就盼小芬婶儿跟豆豆提的时候说的话不至于太激烈,以免激起豆豆那股随时都能泛滥的“正义感”;如果实在没可能,他希望即便小芬婶儿说得再让豆豆气愤,豆豆都可以记住他以前叮咛了一百万遍的话:迂回迂回再迂回,必要时,就往他身上推。
那一整个晚上张慨言一直翻来覆去地祈祷豆豆千万别犯傻,可越祈祷心里越不踏实,他的手机被他妈拿走了,他看了好几次电话,但最终也没打出去。
没用,他知道,豆豆的手机也被他妈给拿了,就算手机还了他,也是审问或教育完他之后的事儿了。
大意了大意了,怪只怪他吃饭前没想到他妈已经发现了;怪只怪他一味地鸵鸟把什么事都往好了想;怪只怪他一直心存侥幸不敢直面现实,怪不得豆豆。
他们俩当中,豆豆一直都只是个小兵而已,他才是主帅,自己手下的兵什么样儿他是知道的,只怪他自己的战略性失误,如果他早做打算,现在又何必这样提心吊胆?
睡到半夜,到底踏不下心来,看看表,指到十二点半了,张慨言又犹豫了一会儿,翻身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得先去看看。豆豆家的墙他翻过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小时候他们家没人豆豆又忘了带钥匙的时候哪回他俩不是翻进去的。只要进去见着豆豆,甭管他认没认,好歹问清楚了,也便于他制定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总比现在这样猜来猜去的强。他现在,连下一步该怎么办都想不出来,满脑子净剩下担心了。
刚一开门儿,客厅的灯就亮了,他妈坐在沙发上,平静地看着他。
“还没睡呐?明天中午还有事儿呢,赶紧睡吧。”
“妈你一直在这儿坐着来着?”
“对,一直坐着来着。”
张慨言低头想了想,说:“妈,我就去看看豆豆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因为我让我婶儿打了他,我……”
“你怎么样?你心疼?你心疼就少往人家家跑,你去了,只会让人家更生气,人家肯定不能打你,有气又要撒出来,少不得又是豆豆挨了,你说你是去帮人家去呀还是害人家去?”
张慨言看了看他妈,那脸色冷得像三九天的河面,话是一句比一句在理,温温和和的,可口气却夹针带刺,冷得能结一层霜。
张慨言也不说话了,转身回自己的房间。
“回去就睡吧,我也不能老在这儿坐着,明天一早还得去市里呢,你就早点儿睡吧,别一起床顶俩黑眼圈影响了效果。”
张慨言停下了:“什么效果?”
“你姨有一同事的女儿,也在北京上学,今年也该毕业了,跟你一般大,说人长得挺漂亮,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一直没回话,即然现在有空,趁着你们俩都在家,就见一面吧,成不成的,见了再说。”
张慨言转回身,坐了下来。
“妈,你这是干嘛?”
一句话,他妈彻底爆发了,“噌”一下站起来,瞪着他的俩眼布满了血丝,牙咬得太用力以至于连张慨言都听到了声音,俩手都攥成了拳头,一个劲儿地发着抖,“你,你”了两声,眼一翻,倒在了沙发上,嘴唇发着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却一直闭着,两行眼泪流了下来。
张慨言一步蹿过去,用力抚着他妈的心脏帮她顺着气,小声地叫着:“妈,妈你别着急,我去,我没说不去,你别这样儿。”
半天,他妈才长出了一口气,脸色恢复正常了,睁开眼,抬手挥开他,冷冷地说了句:“你随便吧。”回房间了。
张慨言自己在客厅愣愣地坐了好几分钟,也不知道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好像什么都想了可又好像什么也没记住,最后站起来,轻手轻脚关了灯,回房间了。
第二天天快亮张慨言才睡着了,睡前把所有的事想了一遍,自己对自己说,不管了,就当豆豆已经被发现了,做最坏的准备吧。
睡了三四个小时就醒了,起床出来,看见他妈已经在做饭了,手里拿着块湿毛巾,不时地捂一下眼睛。
到吃饭俩人谁也没说话,他爸觉得奇怪,问了声今儿这是怎么了,俩人也不抬头,都说了句“没事儿”就低着头吃饭去了。
吃完饭,收拾完,看看表,快十点了,他妈说了声:“走吧。”俩人就出门了。
到了门外张慨言扭头看了看豆豆家的大门,还没开,侧耳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