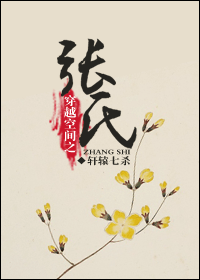水云间之言默-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默想说什么?”谷玉农放慢脚步,侧过头,看向汪子默问道。这两日汪子默已不是第一次这般欲言又止了。
汪子默对上谷玉农的眼,略移开视线,琢磨着该怎么开口,抿了抿唇,刚要开口,就被身后传来的嘈杂声打断。汪子默回过头,就看见有两个拿着相机的青年横冲直撞地跑来,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汪子默还未反应过来,就感觉到一只手穿过自己的后背揽住自己的手臂将自己向一旁拉去。汪子默回头一看,正是谷玉农。
那两人从身边跑过后,谷玉农并没有立即放开,而是抓住汪子默的手腕,迅速将他又向后拉了几步。刚站定,又有十几个穿着黑衣的人跑来,想来是追着之前那两个青年来的,场面一时有些混乱。汪子默比谷玉农要矮半个头,他略略抬起头,正能看见谷玉农的侧脸。他的头发剪得短而显得十分清爽,此时眉头微皱却并不显得急躁,相反地显出十分沉稳的模样,在周围人惊慌的神态中显得更加卓尔不同。
待那群人跑过了,谷玉农忙转过身,问道,“子默,你没事吧?”
“我没事,他们并没有撞到我。”汪子默摇了摇头道,却瞥见一旁一位被方才那群人撞倒了的老太太,忙上前帮忙。二人同其他一些好心人将老太太送去了医院,刚到医院,老人就醒了过来,口中却喊着要回家,总之是不愿就医。老人的亲属还未到,旁人见状也无可奈何,不知该如何处理。谷玉农叫过一旁的护士,将医药费垫付了,谷玉农却不再多留,拉着汪子默便离开了。经此一事,回程的路上,两人都有些沉默。
待到道别的时候,谷玉农才想起了什么似的,唤了汪子默一身。汪子默回过头,谷玉农的上半身已掩在夜色中看不真切了,谷玉农向前走了几步,待离得近了,才开口道,“汪子璇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不要多虑。”说话声虽不大却清晰地传进了汪子默的耳中。汪子默愣了一下,心知自己这两日的不对劲已被对方尽收眼底,却不想他竟看出了自己所忧之事,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些什么。谷玉农笑着拍了拍汪子默的肩,“回去吧。”汪子默点了点头,又看了谷玉农一眼,方才转身离开。
谷玉农回到住处后,受到英国来的传真,接下来的日子,一直忙于公事。因此提前打发了人去支会了汪子默一声后,两人好几日都没再见。
这日,谷玉农好不容易忙完了事,走到窗前,闷热的风吹来,竟觉几分烦躁。无事可做的时候,反而更觉难耐。谷玉农扯了扯衣领,想起今日汪子默没课,回身拿起椅背上的外套便走了出去。
谷玉农来到汪子默下榻的旅店,向柜台上的侍者点了点头,径自上楼去了。那侍者之前见过谷玉农与汪子默在一起,对着谷玉农憨憨地笑了笑,也没拦他。旅馆已有些老旧了,但胜在干净,踩在木质的楼梯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到了汪子默房间门前,谷玉农敲了敲门,片刻后,门从里面被打开,汪子默从门后露出脸来。看见是谷玉农,汪子默眼神一亮,惊喜地说道,“玉农,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谷玉农进去后打量了下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其他地方东西摆放地整洁有序,只靠窗的一张被汪子默当做书桌的桌子上一些纸张、书本有些散乱地放着。屋内没有多余的椅子,谷玉农脱了外套随意地放在床尾,在床边坐下,接过汪子默递过来的一杯清水。
“今天怎么来了?”
“事情忙完了,闲着无事便过来了。”谷玉农随口答道。
“原来竟是把我这当消遣处了……”二人如今已很是熟稔,故汪子默也不吝惜和谷玉农开开玩笑。只是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本不是善于言辞的人,说完,汪子默自己倒先笑了。谷玉农见了他的笑,只觉之前的郁结烦热都消散了。
“午饭吃了没有?”谷玉农知道汪子默平时把自己关在屋里看看书、画会儿画,很容易就会忘了时间,并且吩咐了旁人不得随意打扰,故而开口问道。
“咦,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了吗?”
“都已经过了饭点了。走吧,出去吃饭去。”
并不拒绝谷玉农的提议,汪子默点了点头,换了双鞋,从衣柜中拿出一件外套来,便和谷玉农出门了。汪子默的教师工作说到底是兼职,平日接触的大都是些从事艺术绘画的人,鲜少或者说从未接触过谷玉农这般的人,而他的心性敏感,很容易对谷玉农这般看似内敛实则强势的人产生些依赖,即便平日里他自己没有察觉到,表现得也不明显,但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却体现了出来。而另一方面,谷玉农表面上看来沉稳有度,实际上骨子里是个十分霸道、不容一丝差错的人,他又是个工作狂,平日里接触的又都是商业上的尔虞我诈,戒备已经成为本能。但汪子默心性淡薄,在他面前,谷玉农很容易放下戒心,心情也要舒畅许多。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两人是很互补的。
闲话且不说。谷玉农与汪子默吃完饭后,仍是回到旅店中。上了楼,就见汪子默门口站了个人,是同行的一名教员。见了汪子默,那人上前一步,说道,“我正找你呢,可巧你这就回来了。”那人这时才注意到汪子默身后的谷玉农,要说的话顿了顿。谷玉农向那人点头示意了下,自动从汪子默手中拿过钥匙,先进屋去了。关门的时候,正好听见那人说,“那人谁啊?架子真大。”“是我的一个朋友……”
几分钟后,汪子默推门进来,谷玉农正拿着书桌上一本书随意翻看着,闻言回过头来,却看见汪子默皱着眉头似有什么烦心事。
“怎么了?”
“后天就要回杭州了,今天晚上有个聚会,说是必须到场。”
“嗯,还有呢?”
“可这次聚会连赞助商也一起,地点也是由他们定的,就定在大上海,好像是因为大上海的老板秦五爷也有赞助这次艺术节的原因,真是莫名其妙,哪有让教师去那种地方的。”
谷玉农闻言也有些不悦,一是想不到现在这教育界的官僚、拜金主义就已经这么重了,二来,也是觉得汪子默着实不适合去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但听他越说越气愤,却仍是要安稳下他的情绪的。
“这又什么好气的,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去麽。”
“那怎么行?主任一定不会同意的。”汪子默这般说着,却也没自己拒绝。
谷玉农不在意地笑笑,“怎么那地方被你们主任包下了不成,只准你们去的,我就不能去?”
然而,到了晚上出发的时候,也不知谷玉农如何说的,那主任竟同意谷玉农与他们一道去了。而原本打算乘电车前往的一众人也乘着谷玉农叫来的几辆老爷车前去了。其余人都知道汪子默的家世极好,见此虽有些吃惊,倒也不为他认识这么个有钱的朋友感到奇怪。
此时夜色初降,大上海前车水马龙,却仍不算是最热闹的时段。众人下车后,门口已站了一个穿着黑色长衫的人等候,将一众人引到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桌后正坐着穿着一身黑色长袍外套有绸缎马褂、手中拄一根红木拐杖的秦五爷,端的是一幅好派头。那位主任忙上前问好,秦五爷点了点头,视线一扫,本是随意地打量一眼,忽地一顿,发出一声豪爽的笑声,站起身来道,“谷老板怎么也在这儿?莫不是谷老板还有这等才学,竟还兼职教授麽。”谷玉农笑了笑说,“秦五爷客气了,不过是陪着朋友来而已。”“哈哈,倒不知哪位朋友得谷老板这等重视,竟还怕我秦某人吃了不成。”“这是说的哪里话?”谷玉农回了句,却也没有把汪子默特地叫出来介绍。却说谷玉农在刚来上海的前几天,除了与汪子默有空时出去白相相(玩一玩),也另找了些时间,扩展扩展在上海的人脉,而这位秦五爷恰是谷玉农拜访过的人之一。
因为谷玉农到场的缘故,秦五爷也不好再如先前决定的那样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招待一番,使了个眼色派人下去打点。秦五爷笑着开口道,“我在和平饭店订了座,不知谷老板可否赏脸?”
“秦五爷既开口了,谷某恭敬不如从命。”
一行人刚上了车,谷玉农向外看了一眼,正好看到两个眼熟的人,秦五爷注意到谷玉农的视线,亦朝外看去,“怎么,谷老板认识这两个申报的记者?”
“哦?他们是记者?”
秦五爷点点头,说道,“不过是两个跑跑小新闻的记者罢了,前几天还想着要采访我。”
谷玉农笑了笑,将前几日的事情简单说了说,秦五爷意识到那在后面追的一群人应当便是自己的人,心下庆幸谷玉农对此并不清楚,然而心里却是对那两个记者的看法越发差了。而原本的聚会,也俨然成了秦五爷和谷玉农两人的饭局。
没想到,第二日,昨日一同吃饭的商人中有一人有心搭上谷玉农这条关系,竟又发帖来宴请了汪子默一众 ,谁想当晚汪子默和谷玉农皆没有到场,弄得那人只能悻悻,徒惹了个笑话。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倒是让众人返回杭州的时间又往后推迟了一天。三日后,二人同其余教员坐一班车回了杭州。
作者有话要说:这个真的只是客串,客串啊客串……主要剧情还是放在水云间里,下一章就进入了。
☆、开场
下了车,已是下午一、二时了,众人互道了个别,各自散了。汪子默的行礼要比谷玉农多得多,就由谷玉农分担些。二人出了车站,来接谷玉农的车已到了。谷玉农冲迎上来的仆人挥手做了个手势示意稍等,转过身对汪子默说道,“我送你一程吧。反正去烟雨楼也顺路。”
汪子默摇了摇头,道,“不用麻烦了。你快些回去吧,想来伯父伯母已等急了。”见谷玉农皱了下眉还要再说些什么,汪子默忙道,“我出门多日,家中定有很多事务要处理,我今日要先回趟老宅。确实是不方便麻烦你。”
闻言,谷玉农也不再多说什么,提了提右手中汪子默的那箱行礼,挑了挑眉对汪子默道,“你行礼中可有什么必需品,不若我先将些杂物带走,改日给你送去,也省得你拿多了不方便。”
汪子默笑了笑也不再推辞,将手中的画架也递到谷玉农手中,只留个小箱子,“那便麻烦你了。我过两日就回烟雨楼,平日里都呆在那里,你来前通知一声,我必空出时间、扫榻相迎。”
谷玉农点了点头,笑着回道,“我便等着子默的招待了。”那边的侍从有眼色地上前接过谷玉农手中之物,放到车上去。两人道了声再见,谷玉农转身向路边的车走去,临上车前,又回身挥了挥手,方才离去。
“谷玉农”的父亲在其记忆中是个典型的严父,父严子孝,父子之间的关系却说不上有多亲近。他的母亲也是大家出身,对这个儿子是极好的。谷玉农向来不否认自己重利,否则前世清理家族之时也不会如此不留情面,但他对原主的父母倒也存了几分孝敬的心思,这两年虽不曾回国,平日里也常会寄些东西回来。逢年过节的时候,吩咐个机灵的手下,带着谷父谷母四处转转。谷母这两年来倒是时髦了不少。而谷父,看着自己长子做出的业绩面上虽不显,心中却欣慰自豪不已,自然也乐得清闲,陪着自己夫人溜达溜达。
谷玉农一回家,谷母就立马迎了上去,看见自己儿子面色健康、体格健朗,连说了三声好,又忙着去吩咐底下准备些好的吃食去了。谷玉农说了句“不比这么麻烦”,倒叫谷母拍开搀着自己的手,嘴中说着“出去了两年,回自家倒客气起来了,这孩子真是的……”边说着,仍是面含喜色的出去了。而谷父却一眼就看出了谷玉农的变化来,通身的气派体度、内在气韵如同换了个人似的,沉稳自信,就是连自己也有几分看不透这个儿子了。但看他如此有出息,仍是心喜得多。
谷玉农正和谷父说着些这两年的见闻,就听得一阵脚步声。“爸,我听说哥哥回来啦。”从门外跑来一个穿着黑色校服的少年,长得和谷玉农有5分相似,只是眉眼多了几分稚气,气质也开朗得多。谷父见了,笑道,“多大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谷玉农笑了笑,“玉诚回来了,倒是比我出去时长高了许多。”谷玉诚是谷家二少爷,也是幺子,原主对这个弟弟颇为疼爱,兄弟俩的感情倒也亲厚。谷玉诚挠了挠头,“还是没有哥哥高。”
晚间,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却是谁也没提本该在场的谷家大少奶奶。
谷玉农一向起得早,这日起来后,想起自己回来两日了,还未去看过西湖,此处距西湖不远,徒步也就30分钟左右的路程,谷玉农心血来潮便出了门,此时的西湖与后世的西湖风姿更秀,虽只隔了百年,但其清净雅致已相差甚远。
谷玉农沿着湖堤走着,大早上的,人不多却也不少,老人几个聚在一起,寻一块空地打着太极,起得早的小孩跟着大人乘着早晨的风放起了风筝,湖上零散地行着几艘船,有的载着游人,有的向湖中的荷花群荡去。在俗世中漂泊许久的心仿佛被洗涤过了般,难得的,放下了心中承载着的或大或小的事,悠然地踱着步,在这西湖边上。
正巧刚上了苏堤,前方就有一个穿着不很整洁的男子推着辆破自行车急冲冲地前行,身后跟着一个穿着橘色衣裳并长裙的女子手中拉着一个小男孩快步跟在那男子身后。正行到下坡处,那男子却不减速,底下路虽平整,却显得冲冲撞撞地,边跑还不时偏过头向后喊着“快,快点啊……”这几声不合时宜的喊声,打破了西湖一清早原本的和谐的轻轻嘈杂声。谷玉农快速向边上靠了靠,与那人空出段安全距离,待那三人飞奔似的跑过了,谷玉农才继续方才的漫步。才行了几步,却发觉已失了一开始的兴致。心想最近怎么尽碰到些走路不看路、急冲冲的莽撞之人。弹了弹衣服,却是往回去的路上去了。
却说另一厢,梅若鸿原本牵着车,带着杜芊芊慢慢向烟雨楼而去,没走几步,心中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