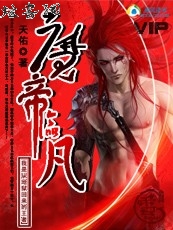梅上雪作者:匿名君(完结)-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文弱书生究竟是何人,竟能拿得到这块牌子?他与施仲嘉又是甚么关系?
且不说这块金牌的威力有多么大,只施仲嘉这个名头,他便万万惹不起,黑州隶属永兴军,施仲嘉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刘指挥面色苍白,滚鞍下马跪倒在地,大声道:“大人请恕末将无礼!请大人下令,小将莫敢不从!”
奚吾根本不敢看身后刘倍的神色,爬下马背对刘指挥道:“如前围住村子,不准任何人进出。再将周遭能弄到的药材尽数调来,你身后半里有处高坡,令人在高坡上建倾角滑道,将药材装在柳条箱中,都自那滑道送过来。另外备两百匹白布,大量石灰水,调黑州左近所有的大夫到此地待命。切记所有来人都以厚布蒙住口鼻,不要与村中任何人做肢体接触,切记!”
“此病难治,何况村中那些愚人根本不懂药,送进去也是白饶,又何必多此一举?”刘指挥颇为疑惑,轻声问道。
“他们不懂,有我,我会再入疫区为他们诊病用药,你留几个兵卒在高坡上,我有事会在滑道那边喊你,一应物事,都要及时调配,绝不能耽搁。”
刘指挥望刘倍方向瞟了一眼,招手轻声道:“大人,大人?”
奚吾不解,附耳过去,却听刘指挥压低了声音劝道:“大人恕小将冒昧,村中泰半是胡人,宋人只怕没有几个,大人何苦甘冒奇险……”
“胡人也是人!”奚吾万没料到他竟会说出这样话来,不由怒极,站直身牵了一匹马便走。
他本就不擅控马,顶多算是能勉强不掉下来,此番心中急躁,催马疾奔,便显出他一塌糊涂的骑术来。明明是平路,也走得歪歪斜斜,先前那块金牌和他的严词厉色换来的威严形象瞬间破灭,五百兵丁目瞪口呆站在原处
50、金牌 。。。
,看着这位新上司左扭右扭,一路危险万分地挣进了村子。
在村中施展平生解数,救死扶伤的奚吾并没有想到,那块一时心急抛出去的牌子,会带来怎样的惊涛骇浪。
他此时此刻的心中,只有两个字:救人。
至于这些人是甚么人,能不能救得回来,值得不值得他赌上自己的命和子文的前程去救,他却全然没有想过。
因此,当他在熟睡中被人掳走时,也并没想到睁开眼看到的不再是灾民遍地的互市街道,而是面目和蔼、言笑晏晏的六王赵和。
赵和却甚么都不逼问,不问他是甚么人,不问他是否死而复生的韦奚吾,不问他的金牌从何而来,不问他出现在黑州是否出自子文授意,不问他和子文有否还有联系。
甚么都不问。
每日里好茶好饭招待他,衣服从里到外换掉了,屋子里空空荡荡到可怕的程度,连吃完茶的木杯都会被随手收走。
逃跑不行,传信不行,诈死不行,装病不行,饮药不行,撞柱不行,投缳不行,咬舌不行,绝食不行……
所有能想得到的法子,统统被挡了回来。奚吾此生从未有过如此无力的时刻,竟全无任何可施展的余地,任人鱼肉。而在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想起那块金牌的分量。
那是子文千叮咛万嘱咐,不到万不得已,决计不可为人所知的东西,那是给他的救命之物,是子文敢于与九王抗衡的一块极重要的砝码。
他救人,错了么?
他万般无奈之下,抛出那块救命的金牌,错了么?
似乎没错,又似乎错了。
一心要做件好事,一心要救天下苍生,自身却万劫不复。
茫然中,他想起师叔祖说过的一句话:“万事,皆量力。”
人非佛陀,救得一个,救不得许多,若自身便是泥菩萨,就不要妄想渡他人一同过江。不但过不去,反一同沦陷。
活了二十余年,他韦奚吾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不肯,而是不能。
他终于懂得子文说他还不曾长大是甚么意思。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本事,不是不辨黑白对错,而是缺乏一颗懂得审时度势的心。
天真,自以为是,愚蠢。
他确实凭一己之力救了数百性命,确实博得了那些人的交口称赞,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可是代价竟然如此沉重。
六王越不动他,他越害怕,不晓得有一日这些人将他抛出去的时候,子文要付出甚么样的代价才接得住,以及,他肯不肯付出那个代价去接。
便在他已接近绝望的时候,这囚笼中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问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
“这块帕子,你从
50、金牌 。。。
哪里得来的?”
。
未几,天交九月,秋风渐凉,一纸邸报送抵京城——西北军攻克西凉城,大帅朱鹏博为国捐躯。
无论是对西夏,还是大宋,这样的战况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大宋朝廷还在为是否出兵而犹豫不决时,西夏大军已攻破沙州,号称百战百胜的雄鹰之王支河罗,竟在阿斯曼这样一个不足双十的黄口小儿面前全无还手之力,一败涂地。
支河罗一代英雄,沙州城破,他以一己之力灭夏军上百,最终长枪折,利剑断,箭囊空,力尽而死。及亡,太子亲兵领命将之团团围住,使乱军不伤其骨,战后,阿斯曼亲手敛其尸骨,送上高台,率夏军叩拜祭奠,并葬以重礼,举城上下哭声震天,支河罗余部遂降。
甘州回鹘从此亡国,部分残兵护卫王室向沙州以南退却,深入大漠,不知所踪。
短短数月,屹立西北数百年的甘州回鹘自西北版图上消失,夏太子阿斯曼横空出世,为各国所瞩目。
至此,大宋通往西域的经商通道被西夏牢牢扼住,其中以战马来源受阻最是心腹大患。
朝中上下为此大为震惊。
发问责文书于夏,却得到这样的回答:“胡里老迈,国事尽付吾子阿斯曼,恳请上国宽宥吾子,宋夏两国代代友好,不起刀兵。”
这根本就是敷衍!
官家大怒,掷书于地,立即封锁宋夏边境,封互市,停通商,断绝所有与夏的来往。
出兵!
一声令下,大军迅速集结,以枢密副使朱鹏博为正,御史中丞施仲嘉为辅,领兵二十万,自兰州入夏境,直逼西凉。
西凉城西有祁连,东接大漠,背靠长城,当中是号称“金关银锁”的古浪峡。“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乃大宋通往西域的必经之所,也是攻克西夏的第一道难关。
古浪峡鹰嘴关地处关冲要道,两侧悬崖壁立,当中一条羊肠小道,最窄处仅容两辆大车,地势险恶之极,绝不可能正面取之。
朱鹏博以重金贿赂当地猎户,请其引路,猎户指山左一条小径,言可绕到峡后,直通西凉城。朱鹏博大喜,便要领军前往,偷袭西凉,副帅施仲嘉则道,此行凶险,大帅不可亲征,宜派先锋取之。却被朱鹏博冷冰冰驳回,再劝,更被责了五十军棍,还在众军面前被批无能,贪生怕死,若再啰嗦,以致贻误战机,当立斩不赦。施仲嘉只得眼睁睁看着朱鹏博点兵五千,随那猎户沿着小路进了山。
朱鹏博本就反对出兵西夏,此次受皇命不得不出征,仗着大宋国力强盛,兵力雄厚,自拊必胜,急于速战速决,眼见得小路蜿蜒,直通古浪峡深处,一路上毫无阻碍,不
50、金牌 。。。
由得大喜过望,天色未明,至昌松口,朱鹏博登崖远望,被崖西埋伏的夏兵团团围住。
夏军早有准备,将宋军困在昌松口的山坡上,无遮无挡,几轮乱箭射过去,宋军死伤过半。欲待前冲,前方是悬崖峭壁,欲待后撤,退路狭窄,且下方亦有夏兵把守,冲下一人杀一人,无一幸免。
五千精兵被困在局促之地,转身不得,便如箭靶子一般,被夏军转眼间杀戮干净。朱鹏博右臂中箭,夏军重重围上,他力战不敌,便要跳崖殉国,幸好施仲嘉放心不下,着手下死士在后悄悄跟随,乱军之中拼死将其抢了出来,救回大营,可惜朱鹏博伤重,又羞怒交加,当晚便不治而亡。
昌松口惨败,五千宋兵全军覆没,宋军更失了领军的主将,不免士气大落,施仲嘉值此危难之际,竟领两千骑兵,深入东边大漠,一日两夜急行,在虎狼关下冒充西夏钦差,骗开关门,用腰间宝剑斩守将于关前,趁乱夺关而过,天光大亮时,他已抵达鹰嘴关背后的鹰嘴山顶,以罕见的强弓射火箭入城,火烧鹰嘴关!
鹰嘴关的地势狭窄,易守难攻,只是一旦燃起了大火,又前后有敌,便如同巨人被困窄道之中,进退两难,百年雄关,此地多少名将折戟,却被施仲嘉一举攻破,大军浩浩荡荡穿过古浪峡,与夏军对峙于西凉城下。
西凉守将自恃武力超群,骑兵精悍,出城摆阵与宋军会战,施仲嘉设长枪阵居中相抵,背靠五百长弓箭阵,左翼右翼重骑扑上,另有两千轻骑绕到夏军背后偷袭,四路大军分进合击,攻守有度,夏军空有勇悍无比的骑兵,竟没有施展的余地,被宋军不断变换的战阵突进切割,分而围之,乱阵之中被屠戮殆尽,余者尽数投降,西凉城破。
这一路过关斩将,夏军竟无人能敌,宋军如一柄尖刀,势如破竹,锐利无匹,直逼夏都银川城南不到百里的西平府。
银川告急!
夏太子得到消息,却已回援不及,万里迢迢横穿大漠来到西平府城外,却只见施仲嘉白衣飘飘,高踞城头,举杯相邀道:“太子劳顿,晚来风冷,可有兴与嘉同饮一杯否?”
作者有话要说:今日更新完毕。
快要进入西北卷了,默默替自己打气加油
51
51、认子 。。。
“这块帕子,你从哪里得来的?”
这是一块锦帕,丝线的颜色已有些黯淡,上面绣的杜鹃却依旧鲜艳夺目,握在他白皙瘦长的手中,竟意外的契合。
此人是第二次出现,中年有须,眉眼温和,跟在六王身边,二人神态间颇为默契,六王叫他——建功,他对六王又恭谨有礼,想是贴身谋士类的人物。
此人究竟为甚么特别留意阿娘留下来的这块帕子?自家已被捉到六王府,真实身份想来早已暴露,他必然不是为探听身份而来。那么,他……会不会……若是……或许……
奚吾心中瞬间转过无数念头,面上却神色如常:“这是我阿娘的遗物。”他温言道,“请你还给我。”
来人上上下下反复看了他几遍,问道:“你是哪里人氏,爹娘是谁?”
奚吾直视他双眼,缓缓答道:“小可乃成都府人氏,因爹娘早丧,只知爹爹行三,阿娘叫他三郎,至于我阿娘的闺名,却不便告诉你。”
“你今年多大?”
奚吾的心中猛地一跳,便有个荒谬的念头涌上来:“小可今年二十有七。”
来人一直沉稳的呼吸竟有些乱了,将那块帕子紧紧攥在手心,艰涩地问道:“你阿娘……几时故去的?”
“甲辰年春天,那年,小可只有十三岁。”
“甲辰年……甲辰年……”那人口中低低地重复了几遍,又问,“你家中,可有兄弟姊妹?”
奚吾低声道:“只听邻人说过我有个幼弟,不到两岁便夭折了。”
“听邻人说过?”那人有些不解,“你阿娘怎样说?”
“自我记事起,阿娘便疯癫了,甚么也不知,每日里只是枯坐庭中对着梅树哭泣。我是邻家阿婆带大的,阿婆说,阿娘生下阿弟不久,我爹爹便死了,阿娘受不住,疯了,没过多久阿弟也夭亡。只是阿娘虽然疯癫,我也舍不得,转回去同她一道住,只盼着有一日她能清醒过来,谁知……阿娘那日好容易清醒了……却……夜半投河而去……”
这番话虽半真半假,却触动了奚吾心底那一块最柔软的所在,他拼命按捺住眼泪,眼圈早红了一片。
对面那人低垂眼帘,看不出神色如何,手却微微有些颤抖,过片刻,忽然问道:“你叫什么?你阿弟叫什么?”
奚吾一怔,忽然满面慌张,急道:“小可名叫薛江,阿弟还没有名字。”
那人翻手一把扣住奚吾的腕子,盯着他双眼低声道:“不要骗我。你姓韦,叫韦奚吾。你是江宁府人氏,你阿娘小名叫阿梨,她才是成都府出生的,可对?”
奚吾用力挣出双手,一径后退拼命摇头:“不是不是,我不是韦奚吾,不是江宁府人
51、认子 。。。
,我阿娘也不叫阿梨,你找错人了!”他的神色惶恐之极,竟怕得双手发抖。
那人一个箭步冲上去,按住奚吾肩膀,眼中已含得有泪,他颤声道:“不用怕……好孩儿,不用怕……我……我是你爹爹啊!”
奚吾心中一片恍然,先前那些模糊的猜测只怕便是事实,他按捺住心跳,一脸茫然道:“爹……爹?”
那人已泪流满面,哽咽道:“你家住江宁府城东静安巷,三进三出青瓦白墙,你阿娘小名阿梨,她喜欢的那株梅树是老君梅,长在南墙边,庭院中另有两株梨树,乃我亲手所植,既犬白首不相离’之意,又暗合她的名字。我姓韦,叫韦业,自建功,乳名韦三郎,是阿梨的结发夫君。你……辛卯年,我去书院读书,考中后,便留在京里做了官……一去便是几十载,竟不晓得她已为我生了一子!你今天二十有七……正是我走后第二年出生,是我的亲生骨肉!”
韦业这番诉说固然好生悲怆,别妻离子十余载,一朝重逢,当真情深。
慢说他是否便是韦三郎,是否便是当年那个见爱妻为人所辱,毫不怜惜,多问一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