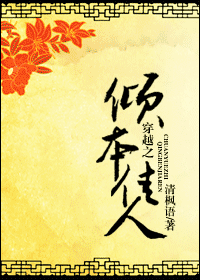梦里浮生之倾国作者:梦里浮生-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出身,一介文臣,乐太平而厌乱世,不愿意在有生之年,亲历兵火锋镝之苦。——言尽于此,王爷三思。”
豫王呆坐椅中,周身冷汗涔涔而下,这些话,他不是没想过,不是不明白,只是图谋行险道、走捷径的人,心内总有“侥幸”二字,又有“利益”一物,蒙眼障目,让人即便是知道不妥,也甘愿饮鸩止渴。因此当林凤致慷慨陈词之时,他倒不仅仅是为他这番言辞所惊所动,而是因为这番道理,原来是这么人所共知而震骇——既然这样,图谋还有成功的可能吗?
只是在这场合,无论如何,对方说得再有理,再私心暗赞,脸上也万万不可认同,还是得死撑到底:“林大人一片言辞慷慨激昂,果然是世间至理,争奈小王并没有非份之念,不轨之心,这番话未免白说了。”
林凤致也不追究到底,微笑道:“这也是,王爷忠心可昭天日,原是下官杞人之忧而已。”
他说了这么一大篇话,不免口干舌燥,盏中茶水已全部倒进了豫王的衣领里,于是便走过去倒热水。豫王望着他背影,双拳捏拳,一时恶念横生,几乎想找把刀当场将此人砍杀。只是身在大内,哪里容易找得到凶器,何况倘若真的杀了此人,就算皇兄不追究,自己也是说不出理由来,对将来更是大大不利。心里又不禁浮出一个古怪念头:“这样的人,要真杀了却也可惜!”
林凤致忽然又道:“下官听说,当年王爷尚在童稚之年,便曾向先帝进谏,不愿剥夺亲兄长的太子之位,据说这善念来自于已故刘太傅一言:‘自古以来,难有终其天年的废太子。’因为这一句话,王爷甘愿放弃先帝欲予之大位,而保今上东宫无恙,这是何等孝友天性?难道到了今日,却欲听俞汝成巧言相诱,宁可置今上于死地么?”豫王冲口道:“胡说!怎会对皇兄不利?”林凤致回头看着他,笑道:“也是,俞相的提议,说的是逼今上退居深宫,拥立王爷,没说要对皇上不利。然而,自古以来难有终其天年的废太子,难道却有安逸余生的废天子?王爷天生睿智,自是比区区所想更具明见,下官倒是多嘴了。”
豫王回想到此处,不由得叹了口气,这是不得不叹。林凤致此人,说话间阐明利害,摆开道理,已经说得九分九之妥,最后还要加上动之以情一条,委实灵巧,委实锐利。这样的人,杀掉固然可惜得很,留在皇兄那里,却也令人下半辈子,不敢放心大意。
但林凤致淡淡而笑,说道:“王爷放心,下官也不会久居朝堂。此事了结,便是下官离去之日,决不至于一直碍着王爷的眼。”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极为平淡,眼中却微露萧索凄楚之意。豫王从来只贪□,不屑情爱,这时被林凤致长篇大论分析一番,既警告又劝说,心里又惊又惧又疑又恨,一时惟剩忌惮戒备,哪有还有方才的欲念?然而在看到他这一丝奇异神情的时候,却不自禁心中一动,隐约觉得他所说的“离去”,并不仅仅是离开朝堂那么简单,一霎时间,即使是表面上大大咧咧的豫王爷,也感到对方压抑着的情绪是波涛汹涌、复杂惊人的。
于是他便问道:“你和俞相,当真就有如此深仇大恨?我听说老俞对你可是真好。”林凤致道:“国家大义,岂顾私恩。”豫王笑道:“面子话就免了!据我所知,老俞可是一直当你如珠似宝的捧着,你的功名前程,均出他手,就是上届的名花榜,都是他指示御史上书,替你禁毁掉的,不然的话,林大人的声誉,可实在不妥得紧啊!他如此相待,你却反来向皇兄告发这谋逆大罪,明摆着要灭他满门,就算你们床笫失和、情海醋波,也没这么切齿刻骨的罢?难不成竟是杀父奸母、夺妻淫女的不共戴天之仇?”
他问这些话,一半是好奇,一半是讨便宜,反正今日不论在口舌还是气势上,都输定了,不如拿对方最不想说的事情,稍稍羞辱一番,也算小小的出了一口恶气。这个问题本来没指望林凤致会回答,可是出乎意料,林凤致竟然答了,说话时仰起头,眼中微微闪着阴郁的火花,声音虽轻,却带着森森寒意,这股压抑的、隐约似含悲哀而又无比决绝的杀意,使豫王一直到回房坐定,尚自心底发冷发颤。
林凤致只是简简单单的答了一句话:“不错,是不共戴天之仇。”
豫王觉得,能让这样一个人恨到如此,绝对不是普通的事,而且,绝对是太可怕的事。
8
本朝的太后姓刘,乃是已故刘太傅的幼妹,其出身也是本朝元勋之后,母家势力极盛,因此刘氏自出嫁为太子妃做起,一路由皇后而至太后,人生一帆风顺,美满无比。现今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最心爱的小儿子豫王不能常常在身边。虽然凭着圣上宠溺,豫王至今还未出京之国,然而朝内一帮老大臣们,动不动拿这事来说话,向圣前参上一本,就好似不把太后这块心尖肉硬逼得送到河南府藩王封地去,就不肯安生。因此太后在后宫中一提到多管闲事不通人情的大臣们,就长吁短叹,咬牙切齿。
这几日太后觉得很奇怪,小儿子豫王虽然平时也常常入宫来看望母后,却是个野马性儿,在宫中留宿绝对不会超过两天,就必定闹着要回去散心。这一回却好不奇怪,自从十月十二那天豫王入宫之后,居然一连五六日,都住在花萼楼不曾回去,自然也就天天来参见母后,母子团聚得颇是欢喜。太后高兴之余,不免也生出疑心:莫非这个宝贝儿子在外头闹了什么大事,以至要回宫来躲这么多天?
豫王听母后问将起来,只是摇头:“唉,儿臣能闹什么大事!倒是皇兄,近来不知道怎么忽然喜欢跟群臣较劲起来,接二连三的惹乱子,这一阵朝堂闹得跟开水锅似的,儿臣这不是怕他们聒噪,没法子只得来躲清净么!”刘太后其实对大儿子不怎么宠爱,但是到底是皇帝儿子,也不能不关切,吃惊道:“有这等事?皇帝身子又不好,入冬正是每年的难关,有什么要紧朝政,非在这时候跟大臣们较劲?”
这时皇后刘氏与德妃时氏也正好在慈宁宫问省太后起居,刘皇后乃是太后的亲侄女,时德妃则是太后的姨甥女,与豫王都属于中表之亲,自幼见惯了的,所以也不曾避嫌,都在太后身周坐着。听太后这么一问,刘后矜持,只是淡笑一笑,时妃嘴快,立即道:“还不是皇上近来被个小编修官迷了心窍,忽然好端端的,到处黜斥起官员来。听说前儿准了兵部尚书的辞呈,昨儿又罢免了吏部的什么主事,俞相国为此跟皇上较起劲来,领着内阁一帮人闭门不出,接连三日,将所有送到阁臣府邸的公事统统退回,说是要闹什么罢朝咧!现在朝房的折子堆得比山高,皇上每夜不是在养心殿,就是去噙梅暖阁,通有四五日不曾回寝宫了罢……”刘后截着她话头道:“妹妹,朝政上的事,我等后宫女流之辈不宜枉议。”时妃忙领了皇后的教训,却低头委屈道:“臣妾只是担心皇上龙体罢了。”
太后不悦道:“俞相领着内阁闹罢朝?这算什么规矩?我看皇帝平日是太纵容他们了,居然闹得君不君臣不臣,成何体统!”时妃那一大篇话的重点本在“小编修官”,没想到太后的注意却在“俞相”,心里不禁发急,一时却又不好再提,幸好豫王十分凑趣,接着笑道:“母后有所不知,俞相也是气得跳脚了,听说他栽培的一个翰林编修,只因最近遽得皇兄宠信,得意忘形,背弃师门,颇是做了些轻狂勾当。朝臣几次参他,都被皇兄护短按下,俞相老脸上委实挂不住,这才赌气罢朝,也不过是情面上的事罢了。”
太后怒道:“居然有这等佞臣?你皇兄不明,你难道也眼睁睁看着他发昏?”豫王在母后面前随便惯了,往椅背上一倒,一个欠伸,笑道:“母后,这些朝政勾当,却不是儿臣能方便去多嘴的,儿臣只管在宫里头躲清净,大家闹定了,也就完事大吉。世上有句话呀,叫做‘隔岸观火,台下看戏’,儿臣舒舒服服的做亲王,享乐子,有什么不好,何苦出头招惹麻烦呢。”
太后气得啐道:“不长进的东西!” 又问:“那个闹得朝政不宁的佞臣,到底是什么来头?”豫王收起笑容,正色回道:“这是皇兄的事,儿臣却不敢胡说。”太后柳眉倒竖,立刻一叠连声叫人,去把贴身服侍皇帝的内官叫几个过来。眼看太后怒了,皇后德妃连忙齐声劝解,于是豫王便趁机起身告辞,脚下一滑先溜了。
他这一下春风得意,连花萼楼都不回,先顺路往暖阁去,谁知空无一人,内官禀道:“皇上起驾往慈宁宫了,林大人去了朝房。”豫王心道:“一个家务,一个公务,倒是合拍得紧!只怕今晚上姓林的便要被母后撵出大内了,倒不忙出去收拾他,先等几日。俞相的事成与不成,我反正站干岸儿,管他们怎么办呢。”
谁知等到晚上,出去打探的小六回来报讯:“林官儿还留在大内,听说皇上跟太后争了一场,又犯了喘症,却不肯回寝宫,今夜又在养心殿安歇了。”
这一下豫王震惊不小,嘴上笑道:“皇兄倒真是多情种子,破天荒头一遭听说他跟母后顶嘴,居然为那个东西!”说着话,便命下人服侍自己穿袍束带,前去养心殿探皇兄的病。
嘉平帝倒无大碍,只是这次喘势比平日更紧些,据说在慈宁宫因为说话太急,还发了一次昏,被太医急灌散剂才救醒过来,豫王去看望的时候,只见他口唇犹带紫绀,双颧火赤,需要靠坐着才觉喘息通畅,手中却兀自握着朱笔沉吟。豫王一进殿,参见之后,便连声道歉:“都是臣弟多嘴的不是,罪该万死!”嘉平帝声音虚弱,却微笑道:“有什么呢,太后向来这样听风就是雨的性子,与王弟何干。”
因为在病中,兄弟二人也说不了几句话,过一阵外面禀传通名,林凤致恭恭敬敬的进来,跪拜之后,便将几份拟好的诏书呈上定审。嘉平帝喘后眼昏,看字费力,于是赐他在御榻前坐了,一字一句的读给皇帝听。豫王一时不好便即告退,呆在室内又不便插嘴,眼见这君臣二人行迹亲密,关系默契,不禁又是好大一阵胸闷。
而且,他在旁边听林凤致读新拟的几份诏书,却是越听越惊。嘉平帝登基四年,御前所拟诏书的风格,一向是不愠不火,含蓄委婉,别说斥责大臣,连说句不是的话都少有,林凤致今日所拟的几份诏书,却是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指责内阁诸臣:“挟众要君,颇多叵测。”痛斥吏部官员:“拖延散漫,胸无定策。”又将兵部大骂一顿:“交讦争权,缓急不分,虚资糜饷,尸位素餐!”看来嘉平帝是铁心不再让步,要将群臣罢朝的风波给打压下去了。
林凤致一一读完之后,嘉平帝迟疑道:“卿的笔力好是好,只是……怕不是太过锋芒?”林凤致道:“那么微臣再重新草拟便是。”嘉平帝叹道:“也罢,就这样算了。反正拟来拟去,也是这些意思,卿也累得紧了……这一发下,明朝还有得闹腾,唉。”说着神情不胜萧索。
豫王见皇兄脸色灰败,显然这几日颇是身心交瘁,忽然心底有点酸楚,轻声道:“皇兄,臣弟告辞。”嘉平帝仿佛没听见,过了许久才疲惫一笑,道:“王弟缓步……今晚太忙,倒是冷落王弟了。”
豫王连称不敢,躬身退出去,将到屏风之外,林凤致忽然道:“皇上,不若今晚便将圣旨颁发到朝房,微臣此刻亲自跑一趟便是。”豫王没听见皇兄答应,想是点了点头,接着林凤致便也躬身退了出来,到门口向他微微一笑,道:“正巧和王爷同路,下官恭送王爷一程。”
9
去朝房和去花萼楼,其实方向不同,出养心殿不远便得分路,林凤致这么说,豫王也明知是借口。两人心照不宣,走到回廊时便放慢了脚步,提灯小监远远在前,随从侍卫知机落后,长廊一片昏暗,静夜中橐橐靴声显得分外清晰,豫王忽然有一种荒唐的错觉,觉得此刻恭谨地落在自己身后半步、端着公事架子的编修官,是个如影随形摆脱不掉的存在,而这从未有过的光景,却似乎有几分诡异的熟悉感,明明陌生不惯,却又似乎习以为常。
豫王在林凤致面前吃过几回口舌上的亏了,这次便拿定主意后发制人,打死也不先开口,谁知林凤致却只是沉默着走了一段路,直到离回廊尽头还有几步,他才悠然叹道:“王爷若要置身事外,又何苦搅这混水?” 豫王只推不懂,道:“什么事外,什么混水?林大人说话,莫要打哑谜,小王是极愚钝的。”林凤致便不作声,到了回廊尽头,他在后面一躬身,道:“王爷慢行,下官就此分道扬镳——望王爷记得多来问候皇上龙体。”行毕了礼,由一个提灯小监伴着,便向南去了。
明明是他主动要送豫王一程,显然是有话要说,没想到却只是这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豫王准备好的应付招数没有使出来,大是纳闷,看着林凤致抱着文书匣匆匆而去,一盏宫灯照得他背影分外清瘦伶仃。豫王忽然回味起来,今日对方说话的语气中隐约有一丝怅然,比起前几日泼自己一盏冷茶后侃侃而谈的那股逼人架势,仿佛少了锐利,却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和伤感的味道,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变得柔和了许多,这种变化煞是古怪,豫王寻思之下,不免意马心猿:“他干吗叮嘱我多去问候皇兄?莫非到底看上了本王英俊风流,拿这个做借口,以后好多见本王几面?”
林凤致当然不知道豫王的自猜自想的意淫,他心中有事,匆匆到朝房交付了诏书,再回到养心殿向皇帝缴回书符玺信,已经是三更时分,嘉平帝靠在榻间,围着锦被,已经昏昏睡着,地下只余几个小内侍在照管火盆,料理茶水,也是东一个西一个在打盹。林凤致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