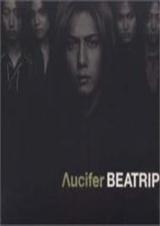第三十九年夏至-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千涟替我接了段四爷府上送来的请帖。
问题还不在这儿,要是送给我的请帖,无论我多不喜欢也还是要去唱的,但在那封请帖之前还有一份请帖,是专给千涟的。
段老爷喜欢《桃花扇》是众所周知的事,以前下过的请柬也都是点的《桃花扇》而不是《长生殿》,这回请柬下来照旧是《桃花扇》,千涟却不像以前赶紧收拾东西过去,反而是慢吞吞地回信说他最近脚受了伤,唱不了,倒是我唱《长生殿》的功夫又进步了。于是段四爷点点头,说那就换成《长生殿》吧。
然后就又送来封请柬,给我的。
千涟看着我笑了笑,说,你不是要替我唱吗?你去吧。
我瞅了眼他那分明已经能跑能跳的脚,也笑了,说,那你好好养养。
那双消了肿还不能走场子的脚吧,要是一不小心好不了,我可要替你唱一辈子。
师哥也无奈,拿着请柬看了又看,最后把帖子往妆台上一扔,怒道:“我要好好骂骂他!”
我拉住师哥,说:“你训他的还少?”又把请柬捡在手里,看了看,“也不过多唱一场戏,不碍事。”
我虽然这么说了,但师哥的怒气还是没有消下去,反而埋怨起我来了,“就是你这个样子才让他得寸进尺!”
我默默叹了口气,很无奈地给师哥泡了一杯菊花茶让他一个人消消火,然后了茶楼。
茶楼里我和蒋沐说起这件事,蒋沐挑眉:“你不喜欢给那些人唱戏?”
我道:“也没有,戏到哪里不是唱?都一样地唱。”
蒋沐笑道:“那就好,我还想哪天请柳老板到我府邸去唱一出呢。”
其实我是不喜欢去那些官僚富人府上唱戏的,不是我看不起他们的腐败和剥削,而且他们请唱戏大多只是撑场面,真心听的没几个,比起这些来,我更喜欢在戏楼唱,愿意坐进里面听戏的才是真心听戏的,喜欢戏的。
蒋沐又道:“你说的段四爷是不是叫段仁义?”
我说:“是。”
然后听到一旁的肖与凡说道:“那是段秘书的父亲。”
蒋沐点点头,看着我,“那正好,我和段秘书挺熟的,我到时也去段府。”
我轻笑,“您不是军统的吗?中统的人您也熟识。”
蒋沐不以为然,说道:“我都说我是蛀虫了。虽然军统和中统之间多少有对立,但像我这样只知道的荒废事业的人,能一起玩的人自然都凑一块儿了。”
我看你是能两面俱混吧?
第二日,段府。
《长生殿》,夜怨。
“宠极难拚轻舍,欢浓分外生怜。”
“比目游双,鸳鸯眼并,半思移情变。”
“唉,江采苹,江采苹,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是我容得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
“只落得徘徊伫立,思思想想,画栏凭遍。”
我哀哀怨怨地唱,而蒋沐果然坐在台下,旁边坐着的就是段秘书,蒋沐看戏中途偶尔回同段秘书说上几句话,而段四爷坐在最前排的中央,听得入神。
戏完了,退了场,我草草卸了装,趁师哥同其他人收拾东西的时候去了西廊。
段府是典型的园林构造建筑。东西左右长廊,临水幽静,镶嵌其中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花草格局合适,围墙圆门断隔环环相扣,依水则顺水之,依山则顺山之,尽万物之体态,出风景之雅韵。
我过了一道门,隔着那丛美人蕉,正好看见水阁里的蒋沐。
我走过去,蒋沐回头看我,“我就知道你会过来。”
我笑他道:“您坐台下给我那个向西瞟的眼神,算是我见过的最明显的暗号了,怕是段秘书都看见了。”
蒋沐哈哈笑了两声,说:“我有那么逊?”
我笑而不答,左右看看,水阁中间的桌子上只摆了个果盘,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不禁问道:“我们过来做什么?”
“过来游后园啊。”
“那让段秘书带您不就好了么?何必要偷偷地?”
“这样才有意思嘛,让段子程带我看就只是一路走马观花,不能细看。”
我看着眼前这个说话眉飞色舞的男人,与他相处的这段日子愈发觉得我当初有些事多想了,他依旧有霸道的气场,丝毫未减,却有多了一份痞气,让人觉得好笑又无奈。
一只让你猜不透的蛀虫。
蒋沐走到栏杆前,双手撑着栏杆,四周看看,道:“我挺喜欢园林的建筑的,威廉。查布斯说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外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一样尽量吸收他的光辉……什么时候也去买一栋这样的宅子住住。”
我也走过去,刚走进又听他说道:“看,下面还有鲤鱼呢。”
我低头去看,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我和蒋沐的影子,在鲤鱼尾巴打起的水波中晃晃荡荡,水波把两人的表情荡得模模糊糊,都看不清明。
“是有几只,那只大红的好看。”
“可以没有饵料逗它们,”蒋沐突然转过头看着我,“不如把柳老板你扔下去吧。”
我顿时错愕。
蒋沐噗地一笑,嘴角一勾,说道:“说着笑的,哪能啊,柳老板要是被鱼吃了谁带我去秦淮河呢。”
但事实上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却还是牵强地笑了两声。两声笑还未过,蒋沐的脸却在理我越来越近,慢慢地,一寸一寸地靠近。
他低下头,彼时已经在我耳边,声音不同以往,分外轻柔:“柳老板身上有种好闻的味道。”
我脊背一僵,不自觉地说道:“大概是脂粉的味道吧。”
蒋沐若有所思,“哦?是吗?不是体香?”
自己心跳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耳膜里放在了几十倍,种种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镇定道:“师哥大概收拾好了行头,我要回去了。”
蒋沐直起身,点头道:“好,那柳老板回去吧,我还要自己在周围转转,就不送你了。”
我应道:“抬爱了,告辞。”
回去的路上我问师哥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味儿,师哥说没有,我说真没有?师哥就扯过我闻了几下,说你早上又没吃我给你买的葱油饼是不是?一股大葱味都没有。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地数落我吃饭吃得少什么的。
我心里只在想蒋沐是不是嗅觉出问题了。
傍晚,我开门进了屋,刚坐下,手指才碰到茶壶饼,就听见外面吵嚷了两声,然后就听见房门被敲得砰砰直响,我微微皱眉,起来一开门,就听见站在门口的警察讯问道:“是不是柳青瓷?”
我点头:“是。”
话落下的瞬间,只觉手腕一凉,警察吼道:“段府告你涉嫌谋杀段家二小姐,带走!”
不明所以,却啷铛入狱。警察局里,一个脸大耳肥的警官把一朵绒花往我面前一扔,“你就给我老实说了吧!”
我却不知从何说起,更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审讯了半个时辰我才大致有整个事情的轮廓。段四爷有个女儿,眼看成婚在即,却突然在后园水阁落水溺死,而我的鬓花却在水阁被找到。
“你说还是不说?!当天可只有你们戏班子去过段府!”
我淡淡道:“我是去过后园水阁,但没有谋杀段小姐。”
“你去过水阁还说没有谋杀?”
“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的鬓花怎么会落在那里的,即使落在了那里也没有什么希奇,但那在他们眼里却成了我杀人的铁证。我皱了皱眉,突然说道:“我有人证,军政处的蒋少尉。”
那审问我的胖子突然就住了嘴,同周围的警员面面相觑了一阵,摆摆手说:“先收监。”
事情一下子变得说好办也好办,说不好办也不好办。好办在于只要去找蒋沐就可以证明我是否清白,不好办在于蒋沐那样的人物,这么一件小事,请不请得动他,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过来作证。
我有些忐忑,不知道警察局会做怎么的打算,更不知道蒋沐会做怎么打算。段秘书和蒋沐有些交情,如果蒋沐为我作证必定得罪段府的人,蒋沐他……是我的话,一定不愿意去做这个对己有害而无利的证。
等待似乎是没有止境的。入夜后牢房里的寒气开始从四周聚拢,走廊的灯昏黄暗淡,我坐在硬邦邦的床上没有入睡的打算,因为我看见一只蟑螂从薄薄的被絮里爬了出来,我皱眉,而后又往边上坐了坐。
不知道师哥怎么样了,应该急死了吧?
想着想着思维开始有些模糊,头慢慢地就靠在了墙壁上,睡去了。
夜里下了雨,但我全然不知。一夜绵绵细雨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我竟然对蒋沐说你不管我。蒋沐笑了笑,回答我说我为什么要管你呢?我一时无言,师哥却突然出现,拉着我的手说走!青瓷别听他的!别理他!一群势力小人!
师哥拽着我的手托我走,我却不由地要回头看,但似乎真的有人在和我说话……
“师哥。”我轻嗫嚅了一声,细细地听真的有人再叫我,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脑袋里像注了铅一样重,背心发凉,感觉自己靠墙的那一面身体湿淋淋的,是顺着墙壁流下来的雨水浸的?
什么时辰了?还在下雨?我听不见雨声,我只听见:
“少尉,喊不醒啦。”
“开门,我要带他走。”
“可上面的赦令还没有下来。”
“出了事直接找我。”
接着就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随后身子一轻,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抱在了怀里。我心里紧紧了,喊了声:“蒋沐。”
却因为喉咙干哑,细若蚊足,连我自己都没有听到。
作者有话要说:
☆、第七章 枪声惊破霓裳曲
回了戏园子大家舒了口气,吓得众人汗涔涔的背终于干了干。
师哥是吓得最不轻的,急得到处找人帮忙都没有空去训千涟。千涟也没想到自己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我回来后识趣地站得远远的不说话。
而我,因牢里的一夜雨染了风寒。幸好还是回来了,估计吃几服药就好了。
那天蒋沐送我回来后就走了,师哥替我道的谢。我醒来后问师哥蒋沐有没有留什么话,师哥说他让我多多休息,我哦了一声,心中多少有些失望。
但第二天蒋沐又来了。
蒋沐来的时候千涟正在没好气地递给我药,我刚接过就看见蒋沐出现在千涟身后,叫了声:“蒋少尉。”
千涟一回头,看着身后军装束身的男人吓了一跳,赶忙端起盘子出门去,却突然一头撞在了进屋的肖与凡身上,他们相互看了对方一眼,千涟匆忙走掉,肖与凡一脸疑惑地回头又看一了眼。
蒋沐开口,“今天怎么样了?好了没有?”
我笑,“谢少尉关心,今天好多了。”
蒋沐自径走到床前,在床边坐下,“嗓子还痛不痛?”
“还好。”
蒋沐招招手,肖与凡走过来,把手里的一个小盒子递给蒋沐,蒋沐接过打开,里面是几个塑料瓶,蒋沐说:“这是我让与凡去医院开的药,吃西药好的要快些。”
“谢谢。”此时我不知道我除了说谢谢我还能说什么。我话像一块海绵,水在里面,却没有勇气去挤。
蒋沐笑了笑,自然地说道:“柳老板你早些好,我还等着听你的戏呢。”
我说:“您听也听了许多了。”
他嘴角勾得更为厉害,叹了口气,说:“戏有意思着呢……人更有意思。”
我突然觉得脸有些烫。幸好还没有等它烧成燎原之势蒋沐就告辞了。
蒋沐刚走,师哥就进来了。师哥坐在床边,看了看我手里的药,又看看我,试探地说道:“那个蒋少尉似乎对你很好。”
我说:“还好。”
师哥顿了顿,才说出了心里话,“青瓷,我看你都不像你了,你以前可不喜欢和他们那样的人来往。”
我顿时也不知道怎么说,当初认识蒋沐是蒋沐的原因,那后来呢,我们熟识也是蒋沐一个人的原因?一个巴掌拍不响,同我拍得响的人,却又是我以往讨厌的人。是我变了?还是他的不一样?我犹豫了一下,说:“他喜欢戏。”
师哥一愣,叹了口气,“青瓷,戏是戏,人是人,戏唱不了一辈子,人却能害你一辈子。我们这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该交,什么样的人不该交你是清楚的,不用我多说,以后掂量着点。”
我看了看手里的药,轻轻嗯了一声。
那些药直到风寒好了我也没有碰,我把它们装在匣子里然后上了锁。
蒋沐依旧来看戏。
这日,来看戏的不只是蒋沐,还有别的军统的人。但显然他们没有和蒋沐相约,一群坐在楼上一个坐在楼下。蒋沐在坐池子里同他们招了招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继续看着台下的我。
“呀!时当仲夏,为何这般寒凉?”
我在台上踩着碎碎细步,又惊又喜地左右观赏,如真到了月宫,见其所没见,惊其所希奇。
头上凤冠珠串晃晃,凤冠下一双水灵的眼目光哀哀婉婉。蒋沐暗暗地对我竖了竖大拇指。
我心里浅笑,听着台旁师傅们奏出的乐声,此曲音律飘逸,飘飘然如纤云,柔柔然如流水,闻之赏心,品之怡情。离情别绪被这欢快的曲子冲得荡然无存。
·我长袖一挥:“你看这一群仙女,素衣红裳,从桂树下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