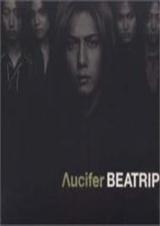第三十九年夏至-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手无力地垂下,我真是没用。
我对蒋沐,到底还是动了真心。记忆里,我进戏园子的那一刻,我回头,看见厚重的大门慢慢锁上,我的人生也就被禁锢在那里,在我眼里挨打受骂算什么,成角儿才是出路,我曾经暗暗地给师哥说如果以后我成不了角儿,我就学千涟他娘,跳河算了。师哥当时没说话,他没骂我傻,他看着戏园子里四角的天空,良久,他说,小柿子你说得对。
小时候总觉得成角就有了那时没有的一切,当成了角,才发现自己除了戏一切都没有。偏偏蒋沐出现了,他为什么要出现,他要情报,他可以找戏班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为什么他偏偏要找上我?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却有毫不解释地收回。我最初在意他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人,我最后恨他,也是因为没有见过他那样的人。蒋沐,你既不是真心,就不要来骗我的真心。
我颓然地坐着,我想这个夜应该会无比的漫长。
“肖副官,您慢着,这里暗,看不太清。”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越来越近,我把怀表放进袖子里,再抹了抹脸,往铁门在一看,正对上肖与凡的眼。
肖与凡看着我,淡淡的目光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采,他手里端着梨木盘,里面盛着一壶茶,怎么?他还要同我夜饮不成?
他亦淡淡地说道:“柳老板。”
我站起身来,笑了笑:“肖副官这是来干什么?要同我喝茶?”
“我可没有这么好的性质。茶是少尉让送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送来而已。”
我不说话,看着肖与凡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如同我不知道蒋沐的心到底怎么想。
“你明天就可以出去了。”他突然说道。
我以为我听错了,我亦不信,道:“你不用戏弄我,我都被关在这儿了,还不够可怜?”
看守摸出钥匙把牢门打开,然后接过肖与凡手里的茶,端进来放到床头后又出去了。我看了看茶,冷笑了一声,翻过一只茶杯倒了半杯茶,闻了闻:“竟然是上好的碧螺春。”又缓缓喝了几口,清香的茶水滑过喉咙,竟然异常苦涩,我转头对肖与凡笑道:“少尉不觉得可惜了么?给我这样的人喝。”
肖与凡不理会,他只说道:“你不会有事,叶西不会有事,戏班子也不会有事。”
我不能再骗自己是听错了,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他欠你的,他拿这些还你。”
欠我的?还我?呵,果然是连半分感情也没有。蒋沐,你真真把冷血二字诠释到完美!
霎时,觉得喉咙里的茶味更是苦涩,我一口饮尽杯里的茶,把茶杯狠狠往地上一摔,茶杯“啪”地一声四分五裂。
“你可以走了。”我突然说道。
肖与凡倒也不恼,平静地说道:“少尉说柳老板以前喜欢喝碧螺春,如今送一杯茶水就算是饯别——少尉已经离开南京了。”
“离开又怎么?那对我不是正好吗?”我哼笑。
然而我心却如刀割,他真的弃我而去。其实我有一句话想问肖与凡,但我怕那一句话会吧我的所有倔强都用光。
我想问肖与凡——蒋沐他,还回来吗?
最终还是不肯去问。我不愿意把那些软弱展示给肖与凡看。肖与凡走的时候我低声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骗子。”
肖与凡的脚步一顿,也没有转头,只是听见他没有什么感情的声音:“柳老板可否帮我一个忙?帮我告诉千涟,就说别等我。”
嚯,原来还有一个真心的。原来连肖与凡都能有情意,而蒋沐就是没有。我没有回答肖与凡,他也没有为了我的回答而停留,他的背影融入黑暗,最终消失了。我又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我突然想起唐明皇曾经在长生殿同杨玉环的密誓与定情,我才想起蒋沐从来没说过喜欢我或者要同我过一辈子的话,唐明皇说过尚且弃玉环而走,况且我们没有说过呢。再看着那茶,人走茶凉。
不能去想明天,更不能去想以后,还不如闭上眼,浅浅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喉咙里如一团火在烧灼,呼吸都开始不顺畅,难受地睁开眼,伸手捂住脖子,痛,喉咙很痛,如同在用砂纸摩擦。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明白,只觉得额头的汗不停地往外冒,如同被火烤的难受。
此时此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喝水。我困难地睁大了些眼睛,四周昏暗,但依旧可以看看床头的那壶茶,它瞬间勾住了我的目光,急切地伸手却被放在旁边的板凳绊了一下。
“啊。”我吃痛地低声叫了一声。
却在下一刻全身的血液开始逆流。只是一个“啊”字,可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我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哪怕只是低声都如此沙哑,如同蒙了一层纱,模糊不清,这,这是我的声音吗?
我伸手一把捂住喉咙,那里烧灼难耐,被烧灼的不只是我的声音,还是我的思维。
我的一切,我的所有。
我慢慢抬头看向摆在床头的那壶茶,我进牢之前除了它滴水未进……我瞬间有些明白了。我的梦也就这么醒了。
南柯旧梦,浮生未歇。
南柯新梦,浮生尽歇。
“蒋沐……”我的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唤他一声名字,嘶哑难耐,如同我的心,悲恨难当。
“蒋沐,你就是这么还我的,你说你欠我的,拿这些还我,你即是要还我,为什么还要收回去,你这个人……真的不愿意心软一回。”
监狱的灯下,飞娥还在绕着电灯泡飞舞,时不时地撞在上面,它追求的光热,永远都隔着一层玻璃。飞娥翅膀扇动的阴影在墙壁上左右摇晃,我坐着的地板冰凉,我低着头,这么一低,就是整个夜晚。
这个夜晚,夜色都凝成了霜,泪水都结成了冰。可惜,蒋沐,你都没有看到,你也不想看到。
“ 青瓷!”
有人在叫我。但我依旧没有抬头。我知道现在已经是第二日了,我已经在地上坐了整整一夜。
牢门被打开了,我听到看守讲:“快点!把他带走!别磨蹭!”
而冲进牢房来接我出去的竟然是叶先生。肖与凡说的是真的。
叶先生单膝跪在我身边,扶着我的肩,我的视野里只看得到他深色的西裤。
“青瓷,青瓷,你怎么了?抬头看看我。”
叶先生急促地询问我,我渐渐抬起头,眼里的氤氲一看便知。叶先生大概也疲乏到不行,脸色憔悴,眼睛有些红肿。叶先生被我的脸色吓了一跳:“这,怎么了?”。但我没有张口说话。
腿早就麻了,叶先生也不再问我,一个打横抱起我,安慰我道:“没关系,我们这就出去,这就出去……戏班子很好,大家都在,云楚和千涟都好……”
我就是这样被叶先生带回戏园子的,被抱着坐着黄包车,一路我都在叶先生的臂弯里闭着眼,我只听到耳边的风声和嘲杂的人声。街上似乎还是一样的乱。
“到戏园子了青瓷。”叶先生小声说。
我不开口,同叶先生进了戏园子。戏园子整个班子的人都在,戏楼被封了,暂时他们只能在这里等。练功的众人见我我回来,都慢慢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看向我沉默。我缩在叶先生的怀里,我来不及抬头,只感觉到一阵风从人群里蹿了出来,然后听到“啪!”地一声。
有人抽了口冷气。可我连声都没有吭——即使那一巴掌是打在我脸上的。
师哥的手有些颤抖,他大口大口喘着气,在一巴掌之后最终什么都说不出来,转身离开。他什么也没说,正是心痛,痛到什么都不能说。
我以前想,如果有这么一天,一定是千涟给师哥说了什么,不然师哥不会知道我和蒋沐的事。而如今,我觉得我是活该。
我猛地抬起头,冲着师哥的背影大喊了一声:“师哥!”
两字一出,无人不愣。
师哥猛地转过头来看着我,叶先生亦吃惊地望着我,大家各种神色,而我只是眼里呛着泪。
叶先生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把拉起我的手往大门口去。
一戏班子的人都还在发呆,叶先生已经叫了黄包车。
“去西和医院!”
去了,就能有用吗?
黄包车上叶先生紧紧地搂住我,他声音有些嘶哑,他下巴低着我的头顶,不停地说:“放心吧青瓷,一定没事的一定没事的……”他终于明白了我从始至终不说话的缘由。但我总感觉一切都是定局,这都是蒋沐设好的局,困住我一身的局。
“这嗓子怎么搞成这样了?估计看不好了。”那个中年的医生这样说。
叶先生几乎是疯掉般的说道:“怎么可能?!他可是唱戏的,医生您再看看!”
“唱戏?”写些病历单子的医生抬头,“这嗓子,那还能唱戏,就是看好了也不能唱了。”
从医院出来,叶先生紧皱着眉,他也许不敢去相信这是真的,我却并没有多大反应,我想,这可能就是命吧。
叶先生说:“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青瓷。”
我只是看着街道,街上还有学生在游行,他们举着的旗子一起举起又一起放下,周围的人群拥拥挤挤,风吹得有些凉,把地上五颜六色的传单吹得乱蹿。
人群中突然蹿出个小报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卖报卖报!”
“八号暗杀案!”
“德川酒店突变!”
“卖报!卖报卖报!”
我鼻子突然有这些算了,我抬头,南京城的天空阴沉,像极了我最初进戏班子时候的天空。
而耳畔,是那些学生的怒吼。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民主!”
“反内战!”
“反内战!”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还我民主!”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十九章 病树床前万木春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南京,大年初一。
南京城的冬天突然冷了起来。南方的暖流迟迟不到,寒风倒还吹着,让人走在街上觉得微微的冷。天空也灰蒙蒙的,就是除夕那天也没见着太阳,幸而晚上有还烟花染了个色,终于有了丝生气。
听说夫子庙在年关那天给人踩烂了门槛。观里头也到处都是人,都是烧香拜佛求好兆头———现在这形势,外面那么乱,要是说好兆头,保个一家周全也就算是好兆头了。这一下子就冷落了秦淮河。听闻那十里秦淮的风光,纵是红灯高挂,碧水如玉,游湖的船也都停在水边,偶尔有船夫把船划过桥洞,走个两里就又回来了。这人都忙着在家过年呢,谁往那儿跑?
人都到街上去了。有钱人家吃喝玩乐必定一个不差,过了年关就都出来遛,百货商场,电影院,茶楼,都是热闹的地方,山西路那边就更是不得了了。没闲着的,恐怕也就拉黄包车的了。没办法,过年关不挣钱什么时候挣?
“黄包车。”
刚下了客人的黄包车就急急跑来,虽然是冬天车夫也穿着面粉口袋做成的背心,已经被洗得发白,脖子上还搭了条毛巾,把额头上的汗一抹———“您去哪儿啊?”
我说:“洪明戏楼。”
今天是初一,师哥说让我去戏楼找他,然后大家伙儿一起出去吃顿饭,也就算是过个年了———过年那天得从早唱到晚,哪能算是过年。
我把脖子上的围巾扯了扯,让它遮住我的鼻子和嘴,把自己的半张脸藏在里面,免得寒风刮得脸发痛。
这一年来我变得怕冷了,上台唱戏的时候非得在云裳里多穿两件衣服,不然觉得冷得牙齿都打颤,唱不了。
师哥说是体寒,买了着阳气的药来补,汤水喝了不少,却没见什么作用,有时风轻轻一吹,脸就紫得跟洋葱似的。最后也就算了,多穿两件衣服就好,喝那些药才折磨人。
黄包车一路直到洪明戏楼,我从后面进去,后台人不少,初一要过来看戏的人都携家带口的估计,戏份自然就多了。
“哟!青瓷!你怎么过来了?”经理看见我吃惊地说道,接着又笑道:“不会是过来唱戏的吧?巧了,前几天宋老爷子还提过你呢……”
“我是过来找师哥的。”我把围巾松了松,好歹这里没风了不是那么冷。
经理一下子不说话了,我把披风解下,兀自到自己的厢位上去,扫了一眼桌子,妆奁,胭脂,笔墨,头面,十多天没过来了,这桌子的东西一个没少,也一件没动,原原本本的模样。我伸手要去摸桌子,经理连忙说道:“擦过啦!云楚天天都擦!”
“其他人不擦么?”
“云楚抢着做的事谁干去做?”
我微微笑了笑,在妆台前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是长袍短发,只是看着脸色有些发白,不知道是不是周围的灯泡打的光太亮反出来的颜色。我的脸印在镜子里,没有珠钗头面,没有胭脂水粉,我仔细看看,想虽然如此但看起来依旧有些光彩。
立刻有想到,自欺欺人。
我把脸一侧,不去看镜子。什么光彩,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脸上有明显的憔悴,就是强挤出笑意来也掩盖不了。我不喜欢看这样的自己。记起以前,每次上台前化妆我都是最慢的,师哥经理老催我,但我依旧是慢。
妆这种东西,